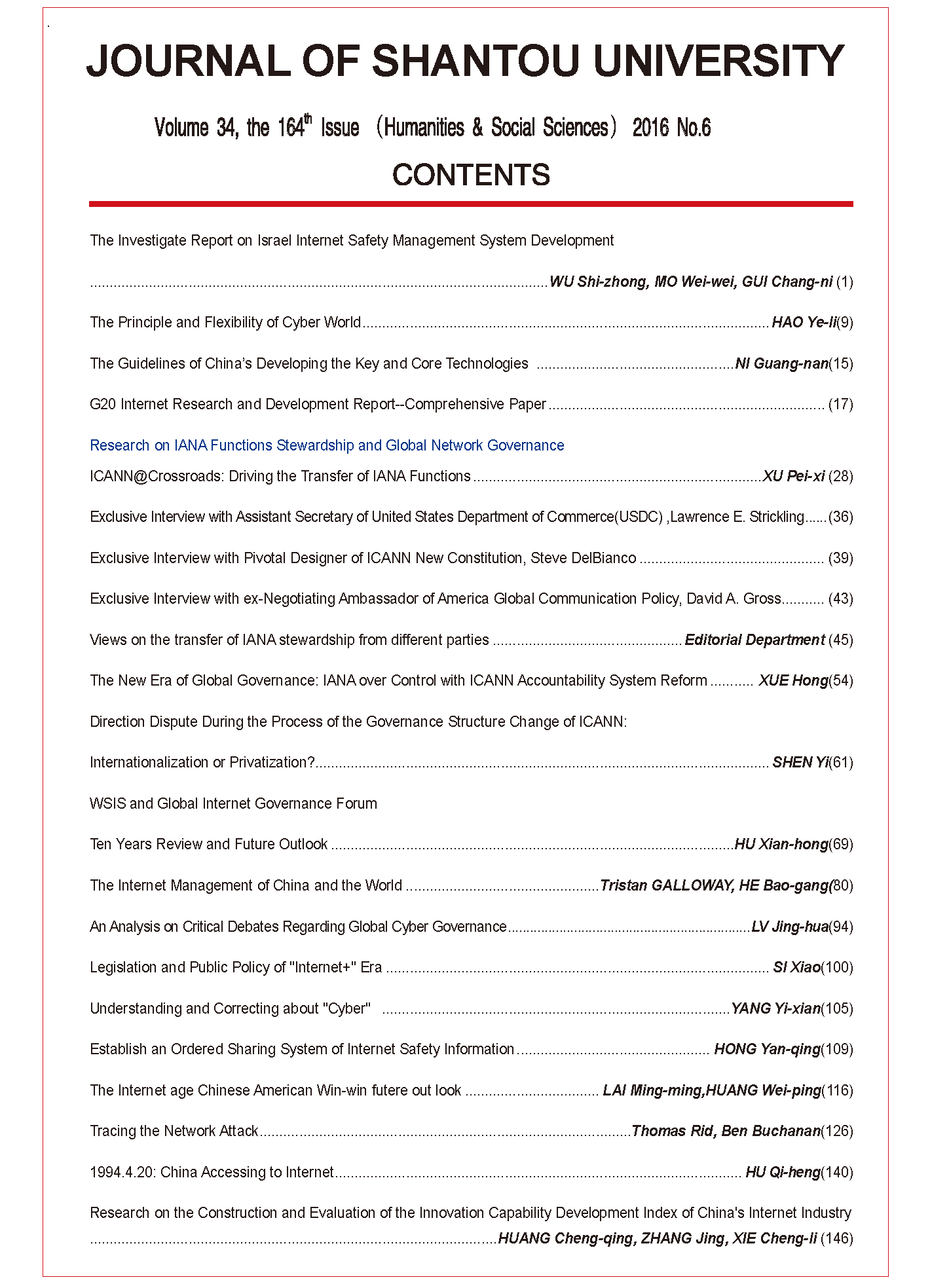ICANN@十字路口:驾驭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1]
2012年和2013年发生的两大事件具有分水岭的性质,煮沸了互联网治理和网络安全这锅水,成为NTIA移交决策的催化剂:国际电信世界大会构成了美国单边主义网络政策的倾覆点,斯诺登泄密事件则激化了美国产业部门和安全部门的利益矛盾。
加之美国政府本来就有私有化IANA的初衷,2014年3月14日,NTIA最终宣布将放弃互联网关键职能的管理权,准备将其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社群”。NTIA要求ICANN定移交计划,并且设定了众所周知的四个移交条件。NTIA尤其强调,移交计划要强化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不能以政府间组织或政府领导的组织取代当前NTIA扮演的角色。[2]
NTIA宣布的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广受讨论,以至于在中国社群中,“3•14决定”成为耳熟能详的名词。2016年3月17日,ICANN向NTIA提交了移交计划。移交计划由两部分组成:《IANA管理权移交方案》和《加强ICANN问责制的建议》。前者由“IANA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起草,后者由“加强ICANN问责制跨社群工作小组”起草。
2016年6月9日,NTIA公布审核意见,表示ICANN提交的移交计划满足了此前设定的条件,表示如果贯彻并完成移交,有助于确保私有部门在跟互联网技术结构有关的决策中继续保持领导地位,避免一些外国政府以美国政府的特殊地位为借口主张应该由政府控制互联网域名系统。[3]
2016年8月16日,NTIA宣布不再延期现有合同。在写给ICANN新任总裁兼CEO马跃然(Göran Marby)的信中,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NTIA局长施特里克林(Lawrence Strickling)表示:“如果不出现重大阻碍,NTIA将允许IANA职能合同在2016年10月1日到期后自动失效。”[4]重大阻碍暗指美国国会休会期结束之后有可能采取阻挠移交的新举动。
果然,2016年9月8日,从总统竞选中失意退出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腾出手来,宣布将升级他此前的抵制行为,全力阻碍这次移交。在美国内部,分别以施特里克林为代表的主移交派和以克鲁兹为代表的阻碍移交派之间的突日益激化。主张移交派包括奥巴马政府、美产业界及其行业组织,阻碍移交派主要包括传统基金会等保守智库、国会保守势力。
2016年9月14日,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两人为代表的主张移交派和阻碍移交派彻底摊牌,NTIA局长施特里克林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之间的冲突无以复加,克鲁兹当场表示按照联邦法律可以将施特里克林送进监狱,施特里克林也忍无可忍再不必忍,表示对克鲁兹指控的莫须有的罪名感到“义愤填庸”。[5]
2016年9月16日,克鲁兹为首的11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民主党参议员加入他们,阻挠10月1日即将发生的移交。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三位负责信息和网络事务的高官联合发表文章,支持马上移交。此刻,距离移交仅剩两周的时间,一切迫在眉睫。
克鲁兹在国会的游说并未成功,他发动的最后一击发生在9月29日,德克萨斯州等美国四个州的总检察长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列举了这次移交将导致美国资产流失等一系列罪状,并要求法院发出临时禁令阻止移交。但是,请求在最后一刻被驳回,美国政府跟ICANN签订的IANA职能合同如期失效。参议员克鲁兹穷尽了所有手段施加阻挠,在最后一刻仍然败下阵来。
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交不交?何时交?立即移交?延迟移交?稍微延迟?长期延迟?这些悬念一直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占据着公众的注意力。整个过程具有高度的仪式感,宛如一场好莱坞电影。作为核心观众,ICANN社群成员身在其中,感同身受,持续观看了两年半的时间,在9月30日合同到期日,终于等来期盼已久的消息:美国放弃IANA职能的管理权。
交给谁:国际电信联盟Vs.全球多利益相关方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电信联盟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主张由其接管ICANN,那么美国为什么极力反对国际电信联盟(ITU)接管ICANN?而是主张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社群?
广泛而言,美国政府移交管理权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实现ICANN的私有化(去政府化),维护产业界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避免全球互联网在斯诺登泄密事件之后走向分裂,避免一些国家联合起来重新建立一个跟ICANN平行的组织,遏制各国实施数据本土化政策的潮流。美国尤其竭力避免联合国或者其下属ITU等政府间组织接管互联网或者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四个移交条件中,强化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是条件之一,同时,NTIA还专门强调,不交给政府间或政府领导的组织。相较而言,在各种讨论中,这个条件被提及的次数最多。
受访人施特里克林表示在过去十年里,关于互联网治理的主要辩论焦点就是仅仅由政府来监管,还是由多利益相关方来监管。美国政府一贯支持由多利益相关方来监管。但是,施特里克林也表示在美国也有人出于政治上跟奥巴马政府作对的动机反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奥巴马的这些政敌认为,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之后,实行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会导致威权政府接管互联网。施特里克林则认为,这些人的看法没有事实依据。有趣的是,不管是诸如克鲁兹等反对移交的人,还是诸如施特里克林等做出移交决策的人,都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或多或少地将中国作为假想敌。2016年9月14日,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克鲁兹连续多次炮轰ICANN新任总裁兼CEO马跃然,要求他表态是否赞成中国是互联网的敌人。不管是马跃然,还是施特里克林,都不赞同克鲁斯的说法,指出中国有6亿互联网用户,但是也都表示,如果这次移交失败,美国将严重失信,对多方的支持会减少,中国的主张会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受访人戴尔比安科主要担心ITU的投票原则,他认为ITU奉行一国一票原则,以这种方式通过的规则或条约会极大地威胁美国利益,伤害美国产业界的利益。他表示:“根据这种投票模式,ITU的任何成员国,不管多小,都拥有一票。而商业力量、民间团体、技术社群,这些互联网的缔造者,却在ITU没有任何投票权利。所以,毫无疑问,我所在NetChoice组织的所有成员公司,都极力反对将ICANN纳入联合国体系。”
受访人格罗斯担心则担心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可能出于宗教因素、政治因素或公共道德等原因,来限制信息自由流通。二是由国际政府间组织接管全球互联网治理可能会限制创新的发展。他认为许多国家无法适应技术的飞快发展,试图减缓这一过程,或者设置一些阻碍。三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可能会加大获取信息的难度。
从2014年3月14日到2016年3月10日,针对如何满足NTIA的条件,全球各方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辩论,最终向NTIA提交了由“IANA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或“IANA-管理权”(ICG-Stewardship)起草的《IANA管理权移交方案》和由“加强ICANN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或“CCWG-问责制”(CCWG-Accountability)起草的《加强ICANN问责制的建议》。
对于“ICG-管理权”这个协调小组来说,这个为期两年的流程至少涉及到“NTIA-ICANN-ICG-OC”(美国商务部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ANA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运营社群)这四道分包流程。
首先,NTIA要求ICANN召集全球各个利益相关方提出移交计划。然而,为了满足NTIA的移交条件,ICANN协调13个社群的30名代表成立“IANA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中国CNNIC主任李晓东为30名代表之一)。接着IANA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动员三大运营社群献计献策:“域名社群”(ICANN的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SO和AC)、“号码资源社群”(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RIR)以及“协议参数社群”(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
然后,各个社群根据各自职能通过自身流程响应ICG的要求,编制提案。在三大社群各自编制提案的过程中,又重新复制这个征询意见的流程。例如,“域名社群”设立了跟域名有关的跨社群工作组,提议成立一个新的独立法律实体——“移交后IANA”(Post-Transition IANA),作为ICANN旗下的附属机构,跟ICANN订立合同,负责跟域名有关的运营。
“CCWG-问责制”这个工作组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流程。2014年12月,“CCWG-问责制”工作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到了2016年3月,工作组已经开过209次会议,打过404小时电话,写过12430封邮件。在最后的建议中,工作组也提议成立新的法律实体——“赋权社群”(EC)。根据加州法律,赋权社群将拥有任免ICANN董事会成员或重组董事会的权力。
“赋权社群”由ICANN五个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组成:地址支持组织(ASO)、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ALAC)、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ccNSO)、通用名称支持组织(GNSO)以及政府咨询委员会(GAC)。ICANN的章程被修改,使赋权社群具有以下权力:(1)拒绝ICANN董事会提出的运营计划、战略计划以及预算方案;(2)批准对基本章程的修改;(3)拒绝对标准章程的修改;(4)启动具有约束力的独立审核程序;(5)拒绝董事会关于IANA功能审核的决策。[6]
此外,“CCWG-问责制”工作组还进一步限定了ICANN的自身使命,在最大程度上避开意识形态、内容管理等最具争议的话题。美国担心ICANN在脱离美国政府的直接监管之后会擅自改变自身作为一个技术组织的定位,防止ICANN扩大自己的责任范围。工作组明确界定ICANN的使命,表示ICANN的使命是保证互联网的独特标识符系统的稳定和安全运行,并且必须严格按此执行,不能管制使用这些独特标识符的服务和内容。
在核心价值观部分,ICANN依靠市场机制来促进和维护域名系统市场的健康竞争环境。在关于ICANN价值观的陈述中,第5条将民间组织、技术社群、学界、用户跟企业一起归入到私有部门当中。ICANN核心价值观第5条:“ICANN植根于私有部门,包括企业利益相关方、民间团体、技术社群、学界以及用户,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政府和公共机构负责公共政策,适当考虑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公共政策建议。”[7]
在通向2016年3月ICANN第55届马拉喀什会议的过程中,关于政府咨询委员会(GAC)权力的辩论非常激烈。此前,ICANN旧章程第11条第2节第J款这样论述政府咨询委员会和ICANN董事会的关系:在政策的制定和采纳期间,应该适当考虑政府咨询委员会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建议。如果ICANN董事会想要采取行动的事项跟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存在冲突,那么ICANN董事会应该告知政府咨询委员会和相关政府不采纳建议的原因。此后,政府咨询委员会和ICANN董事会应该开展及时有效的沟通,寻求双方皆可接受的办法。[8]在ICANN新章程中,政府咨询委员会的权力被严格限制。“CCWG-问责制”工作组为了争取美国政府移交监管权,所提出的建议不仅符合NTIA设定的框架,即不能以政府领导的组织或政府间组织取代当前NTIA扮演的角色,而且还完全吻合美国参议院提出的细节要求。
2014年7月31日,美国桑恩(John Thune)和卢比奥(Marco Rubio)两位参议员曾给ICANN董事会主席克罗克(Steven Crocker)写过一封信。信件从三个方面具体指出如何限制政府在ICANN的权力:(1)不允许拥有投票权利的政府代表进入ICANN董事会;(2)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咨询委员会落实,限定为咨询层面;(3)修改ICANN章程,只有在政府咨询委员会获得全体共识的情况下,才可向ICANN董事会提建议。[9]
“CCWG-问责制”工作组的建议激起不少政府代表的激烈反弹。在通向ICANN马拉喀什会议过程中,涌现出来一个由零散的16个国家组成的准联盟来对抗这个会削弱政府权力的条款。这些国家包括法国及其带领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贝宁、几内亚、马里、刚果)与巴西/阿根廷率领的南美、拉美、加勒比国家(智利、多米尼加、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俄罗斯加入这个立场毫不让人惊讶。俄罗斯指责ICANN改革并无新意和诚意,仍是一个西方的组织。中国大致采取了战略模糊的方法,并没有加入这个阵营,而是保持作壁上观的态度。16国松散阵线指责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对各国政府的敌视态度,认为政府在当前ICANN治理结构中所起到的作用太小,主要列举了四点让他们非常不满的内容:
第一,政府通过政府咨询委员会在ICANN只能扮演咨询的角色,而其他实体则可以通过起草政策建议扮演决策角色。第二,政府无法参加ICANN提名委员会(NomCom)来决定ICANN董事会、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ccNSO)、通用域名支持组织(GNSO)、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ALAC)的领导职位,而ICANN内部的其他咨询委员会(AC)和支持组织(SO)却可以这样做。第三,政府不能进入ICANN董事会,而所有其他咨询委员会(AO)和支持组织(SO)可以直接或通过提名委员会的方式选举董事会成员。政府咨询委员会仅能做到在ICANN董事会任命一个不具有投票权利的联系人。第四,ICANN董事会可以轻易地抵制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董事会内部60%的多数票即可抵制政府咨询委员会达成全体共识的建议),相较而言,通用域名支持组织(GNSO)仅以66%多数票通过的决策建议(PDP)需要在董事会获得高达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方能抵制。[10]
由此可见,各国政府和政府咨询委员会的权力在ICANN缩水的程度有多高。法国政府代表对此表达了巨大失望和不满,认为这将导致政府在ICANN被彻底边缘化,从而为“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美国产业利益集团让路。[11]法国与ICANN之间的矛盾积攒已久,法国认为自己在“wine”或“vin”(酒)等顶级域名上拥有巨大产业利益,而ICANN在落实这些域名时拒绝认可它们的地域性。为了抗议ICANN的这种做法,法国甚至升级到抵制欧美《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高度。[12]
如上所述,2014年3月14日,NTIA宣布要将IANA职能的管理权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并设定了四个条件。受访人施特里克林是设定条件的人。NTIA要求ICANN根据这些条件制定移交计划。美国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独立制定移交计划的两个工作组?美国如何确保ICANN在既定轨道上运行?如何确保ICANN在未来不会出现伤害美国利益的重大变动?
美国政府相信美国产业界在ICANN的影响力。美国产业界在ICANN的代表所做的事情甚至超过了NTIA所能料想的范畴。美国互联网行业组织NetChoice执行总裁戴尔比安科不仅仅求确保ICANN所提出的建议满足NTIA的四条件,甚至从社群的整体利益出发设定了问责流程,限制ICANN董事会的权力,避免ICAN失控。设定问责制流程既非NTIA的初衷,更曾经遭到ICANN董事会的抵制。
在连续六个任期中,戴尔比安科一直任ICANN“商业利益相关方社群”(Busin Stakeholders Constituency)的政策主席。早在美国政府宣布移交之后的首次ICANN会议上(ICANN49,新加坡,2014年3月23-27日),他就提出了一整套“压力测试”机制。
压力测试(Stress Test)这个词是个软件工程专用词汇,用来测试系统潜在的弱点和风险,程序员出身的戴尔比安科突发奇想,将这个方法应用于ICANN的制度设计当中。他本人提出了这个“创意”,经过社群的讨论叠加,竟然发展成36个压力测试类别和规模,成为问责制工作组的关键思想基础,连NTIA和ICANN董事会也忍不住提出了自身版本的压力测试。
如上所述,在ICANN旧章程中,如果政府咨询委员会(GAC)要向ICANN提建议,只需在政府咨询委员会内部达成“大多数共识”(Majority Consensus),ICANN董事会必须对这种建议做出回应。在修改之后的ICANN新章程中,在政府咨询委员会内部,不管要向ICANN董事会提出任何建议,都需要事先在委员会内部达成“全体共识”(Full Consensus),而ICANN董事会只需要达到60%的票数就能抵制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本来,将这个写入章程,看似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戴尔比安科更进一步为下列情况未雨绸缪,如何确保规则的稳定性?如何应对ICANN董事会或者他人未来重新改写这些规则?压力测试用来检测各种可能性,要么封堵漏洞,要么当
常事情发生时做出恰当的反应。戴尔比安科设了“压力测试18”(Stress Test #18),应对府咨询委员会“复辟”的可能性,一旦政府咨委员会未来咸鱼翻身,在ICANN重新扩大权力,可以激活一些程序进行应对。戴尔比安科提出的预防机制包括独立审核政策和法庭仲裁。这里最为关键的内容是将这套机制镶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的框架之内,如果背离了既定的规则和章程,那么社群可以激活加州法律关于非盈利公司的规定来确保贯彻。
针对这个压力测试的讨论结果,既进一步重申限制政府咨询委员会在ICANN中的权力,还能保障未来出现异常情况时做出明确的应对。“压力测试18”因此演变成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最深恶痛绝的内容。在访谈中,戴尔比安科虽然拒绝承认政府在ICANN的权力缩水了;但在其他场合,他曾经宣布:“毫无疑问,政府或政府咨询委员会,在移交过程中失去了权力。”
既然交出监管权能够更好地保护美国产业界的利益,既然苹果、微软、谷歌、因特尔等美国跨国科技企业都支持移交,既然几百家名不见经传的、但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美国中小微互联网企业都支持移交,NetChoice、i2Coalition、ITI、互联网治理联盟等美国科技领域产业组织也都支持移交,都认为这样能够保护互联网的完整性和兼容性,有利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避免世界其他国家政府过多染指全球互联网治理,那么为什么这次移交仍然在美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争议?为什么美国参众两院、强硬派智库仍有人极力反对移交或主张长期搁置移交?
这里的背景是“网络军工复合体”在美国的崛起,并且跟美国产业界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这个崭新的利益集团涉及美国情报承包商、强硬派智库、传统军工承包商、以及国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是美国传统军工复合体所确立的新的增长点,是美国军工版本的“互联网+”,地位之高,堪比一些中国的国企。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产能严重过剩,亟需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后来将建立在冲突的基础上的盈利模式延伸到网络空间,属于意料之中的事情。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等强硬智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等老牌军火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等政府情报业务承包商、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政府部门以及急于保护并制造新的就业岗位的国会议员们,相互扶持,联手行动,试图在网络安全领域开掘出新的矿脉。
这个利益集团的组织方式主要建立在政府——军工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当人们在思考互联网治理问题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这个产业的存在。提起美国产业界,人们更容易想起来谷歌、亚马逊、脸书等企业,但并不熟悉美国军工部门和情报服务提供商。
跟美国产业界所经历的巨大技术变革相似,美国情报界在奥巴马任期也经历了一场信息革命。美国国安局的“2012年-2016年通讯情报战略”指出,通讯情报收集方式正在经历颠覆性的变革,从传统时代的任务式途径转换为符合信息时代特征的系统式路径。该战略指出当下正处于“通讯情报的黄金时代”,追求“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从任何人”那里收集通讯情报的能力。
美英情报部门在情报收集领域早已完成范式转变。仅美英联合实施的“监听现代化项目”就获得了为期三年、高达10亿多英镑的资助。博思艾伦公司是斯诺登曾经效力的公司,该公司剥离了利薄的商业咨询业务,成为一家纯粹的政府业务承包商。早在2013年财年,博思艾伦公布营收就已经达到57.6亿美元,其中50多亿源自政府合同,13亿美元直接来自美国几大情报机构。
对于军工界来说,网络安全产业,以及未来的网络空间战备产业,盈利前景无限,拥有百亿甚至千亿的规模,跟美国产业界的相关成分相比,并不逊色多少。在影响美国国会方面,这个利益集团拥有跟美国产业界平分秋色、甚至更高的地位。在世界上树立中国作为网络空间的假想敌,也主要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所作所为,并构成了它们存在的理论基础。
斯诺登泄密事件源自这个利益集团的内部,严重损害了美国信息产业界的世界声誉,造成了产业界巨大利润损失以及更多的无法计算的隐形损失,造成了美国产业界和安全部门之间较为深刻的裂痕。在这个背景下,美国产业界均支持美国政府交出IANA职能的管理权,可以理解为一种撇开嫌疑的自保自救行为。两大利益集团在美国国内所进行的博弈甚为激烈,世界各国与美国之间的网络安全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美国内矛盾的一种外溢效应。( 责任编辑:李晓晖)
ICANN@ Crossroads: Driving the Transfer of IANA Functions
XU Pei-xi
Abstract:The Internet governance debates take many routes and happen in many forums. The most salient thread in recent years involves a process from the March 2014 NTIA announcement about the transfer of IANA functions stewardship from U.S. government to global multi-stakeholder community, to the March 2016 proposals at ICANN55, and then to the final successful transfer on September 30, 2016. The article answers mainly three questions: 1) Who are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makers on the way from 2014 to 2016? 2) How to make sense of the new ICANN bylaws? 3) Why have there been so many political disputes over the handover of IANA stewardship in the U.S.? Three leading figures most closely involved in the transfer of IANA functions were interviewed: The Honorable Lawrence E. Strickling, Mr. Steve DelBianco, and Ambassador David A. Gross.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iews constitute a timely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ICANN processes and the relevant debates in China.
Keywords: ICANN; IANA Functions Stewardship; Transfer; Key Figures
作者简介
徐培喜: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芬兰坦佩雷大学副博士。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互联网政策、网络安全等。
参考文献
[1]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成果,项目号YETP0619
[2] http://www.ntia.doc.gov/press-release/2014/ntia-announces-intent-transition-key-internet-domain-name-functions
[3] http://www.ntia.doc.gov/press-release/2016/iana-stewardship-transition-proposal-meets-criteria-complete-privatization
[4] http://www.ntia.doc.gov/files/ntia/publications/20160816marby.pdf
[5]http://www.judiciary.senate.gov/meetings/protecting-internet-freedom-implications-of-ending-us-oversight-of-the-internet
[6] http://docs.house.gov/meetings/IF/IF16/20160317/104682/HHRG-114-IF16-20160317-SD003.pdf
[7]第 30 页,Core Values, The CCWG-Accountability’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2016 年 3 月 10 日
[8]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governance/bylaws-en#XI
[9]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iles/correspondence/thune-rubio-to-crocker-31jul14-en.pdf
[10]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cctcrosscomm/Minority+Statements?preview=/58726353/58727370/Olga- MinorityStatement-Revised%2025Feb.pdf
[11]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16/03/24/france_slams_us_govt_internet_transition/
[12] http://www.ft.com/cms/s/0/828ad97c-f94a-11e3-bb9d-00144feab7de.html
继斯诺登泄密事件之后,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问题进一步延伸了全球互联网政策大辩论。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下,深入解读移交背景和过程、ICANN机制和流程以及政策和产业影响,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就此,本文作者采访了三位关键人物,就IANA管理权移交问题进行讨论。他们是: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美国商务部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局长施特里克林(Lawrence Strickling)、美国互联网行业协会NetChoice执行总裁、ICANN“商业利益相关方社群”(Business
Stakeholders Constituency)政策主席戴尔比安科(Steve DelBianco)、以及美国全球传播政策前谈判大使、美国互联网治理联盟(Internet Governance Coalition)领袖格罗斯(David A.
Gross)。
时间:2016年6月28、29、30日
地点:芬兰赫尔辛基ICANN56
IANA管理权移交的三个背景材料
1998年:ICANN私有化本来就是美国的初衷
联网数字分配机构)职能,从1998年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成立之初已经可见端倪。1998年以来,NTIA一直以协议方式授权ICANN管理IANA职能。ICANN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就将自身作用定义为一个临时客串的角色,因而2014年宣布将尊重初衷,放弃管理,具有合理的理由。ICANN成立之前,域名系统的管理主要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科学家帕斯特(Jon Postel)一人承担。
帕斯特是互联网创始人之一,在此领域广受尊敬。1998年去世之前,帕斯特建议成立ICANN这个非盈利机构承担他担当的责任。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以协议形式将IANA职能交由ICANN管理。而在美国商务部1998年6月10日发表的政策陈述中,承诺将最终放弃协议,移交管理权,让私有部门在域名系统管理中承担领导作用。私有部门主导、大市场小政府本来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更是克林顿时代的经典药方。
2012年:国际电信世界大会构成了美国单边主义网络政策的倾覆点
随着互联网渗透到各国人民生活的每个细节,世界各国日益关注全球互联网治理,也日益不满美国在此方面的垄断地位。及至2012年12月,国际电信世界大会(WCIT)在阿联酋召开,世界各国开始公开挑战美国,因为互联网治理议题,各国分裂为冷战对峙以来的两大阵营。WCIT会议讨论缔结新版《国际电信条约》,各国核心分歧是加强还是弱化政府/政府间组织在全球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作用。多数发展中国家主张加强政府的作用,而多数西方国家主张削弱政府的作用,由市场力量主宰网络空间。俄罗斯在这次会议上递交提案,要求在新版国际电信规则中全面增加关于互联网治理的核心内容。如果按照这个提案缔结新条约,那么国际电信联盟的确会架空ICANN在互联网治理上的作用。
新版《国际电信条约》的14个正式条款丝毫没有体现俄罗斯提案,只字未提“互联网”这个美国认为的禁忌词。但作为一个妥协方案,WCIT会议起草了“培育有利环境,实现互联网更大发展”的决议草案,要求各成员国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多种不同论坛,阐明其在国际电联职权内的与国际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发展和公共政策问题上的立场。该决议草案仅仅是邀请国际电信联盟在互联网治理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并无不同寻常之处,但正是针对这个决议草案的表决过程分裂了大会。美国及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铁杆盟友风声鹤唳,强烈要求删除该决议草案,针对该草案的去留,出现了中国等89个国家签署新条约,而美国等55个国家拒绝签署的对峙与分裂局面。这次会议构成了美国单边主义互联网政策的倾覆点,要求美国改变此前的单边主义的做法,安抚各国各方、尤其是中间的摇摆国家。
2013年:斯诺登泄密事件激化了美国产业部门和安全部门的利益矛盾
2013年6月以来,斯诺登泄密事件持续发酵,加深了美国和美国盟友、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国产业界之间的裂痕,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它们之间的互信与默契,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进行肆无忌惮的监控,严重损害了美国产业界的利益,引爆了美国产业部门和安全部门的矛盾。产业界要求美国政府全面整顿监控体系,并且“率先垂范”,限制政府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带动其他国家政府做出类似的举动。
美国产业界对美国情报部门的“棱镜”项目大都知情,但是并不熟悉美国国安局竟然还通过“上游”项目从海底光缆和基础设施上直接截取情报,因而广受震撼。2013年12月9日,美国在线、苹果、Dropbox、Facebook、谷歌、LinkedIn、微软、Twitter以及雅虎九家科技公司签署给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表示政府监控行为远超所需,亟待改革,敦促美国政府率先进行改革。此后爆发的“苹果Vs.FBI案”虽然看起来是像做秀,但实则可放在这个背景下进行考察。美国虽然并非通过ICANN来控制网络空间,从斯诺登泄露的内容即可看到这一点,但是ICANN却一直以来就是各国政府抱怨美国的着眼点和发力点。
采访时间:2016年6月30日 采访地点:芬兰赫尔辛基ICANN56
施特里克林(Lawrence E. Strickling)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美国商务部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局长,做出移交的主要决策者,2009年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当选入职,在美国商务部负责互联网政策、宽带、域名问题,是美国政府对口ICANN的主要负责人,因为移交问题,在美国政界处于风口浪尖。
徐培喜:您在2014年3月14日做出重要决定,将IANA职能的监管权(oversight)从美国商务部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
施特里克林:更正一下,我们不用“监管权”(oversight)这个词。我们用“管理权”(stewardship)。对于我们来说,这两个词有巨大差别。但是,许多人仍然使用监管权这个词。
徐培喜:差别在哪里?
施特里克林:我们并不对ICANN的活动进行任何形式的日常运营监管。1998年,我们被赋予管理权,致力于私有化域名系统。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被赋予域名系统的管理职责。监管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日常管理的含义,这从来不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徐培喜:这两个词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施特里克林:在我们看来,是的。
徐培喜:好的,关于这次管理权的移交,有人说这是一个一直以来就持续的过程,不可避免。但也有人说,这件事具有突发性,是因为斯诺登泄密事件造成的。
施特里克林:前者说的对。这是一件一直以来就计划进行的事情。如果我们追溯1997年到1998年的文件,美国政府那个时候就已经做出决定,打算将域名系统(DNS)交给商业利益主体。1998年,我所在的部门NTIA,就已经受时任美国总统所托,开展私有化工作。所以,早在1998年,就有明文表示要进行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关键问题在于,移交前要完成两件事情。一是ICANN作为一个机构要走向成熟,可以脱离美国政府独立管理域名系统。二是国际社会要理解并接受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当我们2014年宣布计划进行这次移交的时候,这表明这两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认为,ICANN机制已经足够成熟,美国政府的这个特殊角色不有必要。我们还认为,国际社会对多利益相关治理机制的支持也日益扩大。这些便是所有的素,都发生在1998年到2014年,是一个持续年的过程。
徐培喜:您设定了四个移交条件。其中您尤其强调,不能以政府间组织或政府领导的组织取代当前NTIA扮演的角色。为什么最后附加的这个条款后来被如此多地讨论和强调?
施特里克林:至少在过去十年里,关于互联网治理的主要辩论焦点就是由政府说了算,还是由多利益相关方社群说了算。美国政府一贯强烈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次IANA职能移交破坏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我们清楚地表态,社群提交的移交计划必须保证,不能由政府间组织或某个政府取代这个过程。我们尤其需要让美国政府和国会里的人明白,这次移交不会导致政府接管互联网。
徐培喜:现在,很多东西都被写入ICANN的新章程。您有没有觉得政府在ICANN机制里的权力被边缘化了?
施特里克林:不是这样,政府在ICANN的权力基本上保持原样。发生的事情是:章程具体规定了政府如何向ICANN董事会提建议,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董事会必须考虑政府的建议。所以,当下的操作是,如果各国政府在政府咨询委员会(GAC)就某个建议达成全体共识,董事会就必须考虑、回应政府的建议。这些动作如今都在章程中得到了明确规定。眼下,就是如此。未来,政府有可能寻求在ICANN扩大自己的权力,美国国会不希望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要回应国会的关切。
徐培喜:在摩洛哥召开的ICANN第55届会议上,针对政府咨询委员会在ICANN的权力受到限制,法国政府为什么表达了巨大的不满?
施特里克林:我觉得你得去问法国。
徐培喜:是跟.wine这个顶级名的争议有关系吗?
施特里克林:你得去问他们。个人不想猜测。
徐培喜:俄罗斯对ICANN的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表示不满。ICANN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将总设在加州有什么含义?
施特里克林:ICANN总部总得在一个地方。事实上,问责制流程建立在加州法律的基础之上。 如果将 ICANN 从加州挪走,就失去了问责制方面的所有保护。所以,在ICANN 新章程中加入总部必须位于加州这个条 款,能够落实社群在问责制方面的期许。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方面的争议没有实质的意义。管辖权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如果你不是美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哪国法律适用管辖你跟ICANN的争议,应该去哪个法庭解决争议。在这些问题上,都是属于可以跟ICANN单独约定的问题,不受ICANN总部在加州这个事实的影响。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想要跟ICANN订立合同,完全可以约定利用中国法律和法庭管辖纠纷,跟ICANN总部设在加州不矛盾。当人们在提及管辖权争议的时候,主要的争议点是哪国法律和法庭适用。人们担心会被迫在加州法庭依据加州法律打官司。但事实上,情况并非他们想的那样。这里有三个不同的问题。公司位于哪里?适用什么法律管辖公司和别人之间的纠纷?去哪个法院保护你的权利?这些问题必须区分对待。最后两个问题是当下ICANN工作流程二当中正在讨论的问题,社群希望加强对ICANN的监督问责。
徐培喜:我还以为必须依据加州法律解决争议。
施特里克林:并非必须这样做。这取决于ICANN和其他人之间的合同约定。
徐培喜:您觉得这次移交会顺利发生,还是会出现延迟?
施特里克林:现在,合同会在9月30日过期。华盛顿内部的政治讨论正在关注这个问题。有些国会议员不希望看到移交。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建议通过立法阻止移交。我们会看到他能否成功通过立法。这会影响时间安排。同时,ICANN必须完成一些事项,例如,签完跟IANA职能客户之间的合同。在合同失效之前,还需要完成其他一些事情。但是,几周前,6月9日,我们已经完成了对移交计划的审核,并认为符合移交条件。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徐培喜:为什么这次移交出现了这么多争议?您动身来赫尔辛基参加ICANN第56次会议之前,就在6月25日,克鲁兹参议员给您写了公开信,指责您领导的NTIA违反联邦法律,使用联邦资金处理放弃监管权问题——他使用的是监管权这个词——如何理解他的这种指控?
施特里克林:这是在玩政治。这是错误的。我已经回复了这封信,告诉他错在何处。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仅没有违反联邦法律,而且,是国会指示我们对移交计划进行评估。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扭曲事实。这就是政治。这些指控毫无事实依据。
徐培喜:在几次听证会上,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政策分析人员在这个问题也表达了跟您完全不同的想法,您如何看待?
施特里克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扭曲事实。你必须亲自问他们。
徐培喜:美国是不是有不少人,根本不理解或者反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式?
施特里克林:坦率地讲,我不理解这些人反对这件事的动机。只要他们觉得是奥巴马政府的建议,就一定要反对。但是,这些反对移交的人根本没有依据事实进行认真的分析。这些人所抛出的言论,无非是说威权国家会利用这个机会控制域名系统。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也有可能他们知道自己是错误的,但仍然坚持这样认为。我无法猜测他们的动机,但是他们的指控没有事实依据。
徐培喜:为什么NTIA要选在NETmundial会议之前宣布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的计划?
施特里克林:时机成熟了。同时,我认为,如果在那个时候宣布,会对会议有所帮助,人们有了一件可以展开讨论的事情,最后证明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这促进了在巴西发生的讨论。不过,抛开这一点不说,移交的时机已经成熟。
采访时间:2016年6月29日 采访地点:芬兰赫尔辛基ICANN56
戴尔比安科(Steve DelBianco):美国互联网行业协会NetChoice执行总裁,拥有19家会员公司。他代表美国产业界,先后21次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在ICANN召开的56次会议中他参加了32次,在针对移交问题所设的管理权和问责制工作组中,他代表商业力量具体设计ICANN的新章程,维护产业界的利益,并获得显著成效。程序员出身,技术专家,熟知互联网治理。ICANN压力测试机制的缔造者和新章程的关键设计者。
徐培喜:您曾经写道各国政府日益痛恨美国政府在IANA职能管理权方面扮演的特殊角色,并且认为斯诺登泄密事件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戴尔比安科:我的确说过这些。但是,相信我,斯诺登泄密事件跟域名系统(DNS)没有任何关系。很多国家都干监听监控的事儿,都跟域名系统没有关系。监控是通过截取通信来实现的。域名系统与此无关。些事儿被人为地炒作起来,这样,那些痛恨美国政府特殊角色的政府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关于IANA职能管理权的去留问题,本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政府并不怎么在意,但是巴西把斯诺登泄密事件拎了出来,宣称这是他们的关切,这件事情才引起大家的注意。斯诺登泄密事件还为一些国家实施数据本土化提供了动机。对于NetChoice的成员公司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头疼的问题。在这个语境下,有一种观点认为,早点儿放弃IANA职能的管理权或许会软化一些要求数据本土化的立场,还可避免联合国接管美国政府的特殊角色。放弃美国对IANA职能的管理权,便具有吸引力。但是这个特殊角色并不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社群。
徐培喜:美国政府放弃对IANA职能的监管,这是一个一直以来就持续的过程,还是说具有很大的突发性?
戴尔比安科:这是一个加速了的变化过程。本来,IANA职能合同在2018年会自然到期。按照这个逻辑,我可以想象,ICANN和美国政府那时会自问: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安排?我们是否应该移交给别人?斯诺登泄密事件影响的只是移交的时机,没有斯诺登,这件事情最终也会被提起来。
徐培喜:那么,为什么诸如巴西、南非、印度、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倾向于将其移交给联合国体系?
戴尔比安科:他们喜欢联合国及其旗下的国际电信联盟(ITU),是因为他们适应了这个体系。在联合国体系下,国家不论大小,都有一票。一些根本不关注某个ITU问题的国家有时会被说服选择某种投票立场,用来换取好处或在本国的投资。这种政治交易让产业界非常担忧。按照ITU的投票模式,产业界、民间团体、技术社群,这些互联网所有相关内容架构的缔造者,却在ITU没有任何投票权利。所以,毫无疑问,NetChoice所有成员公司,都极力反对将ICANN纳入联合国或其下属的ITU体系。
徐培喜:所以,不能让政府间组织接管IANA职能,成为NTIA制订的所有移交条件中的中心思想。
戴尔比安科:不完全是这样。NTIA的确说,不能由政府间组织接管IANA的三项职能。NTIA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IANA职能的移交。我们这些社群成员却说,等一下,我们不仅仅要移交IANA职能,我们还要关注如何监督问责ICANN机构本身。一旦美国放弃监管IANA职能,美国政府就失去了对ICANN的控制。我们需要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美国政府,这种别的东西不能是一家政府间机构,但同时又必须是一个实体。NTIA起初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它没有设计问责制流程。问责制流程是我们这些社群成员创立的。坦率地讲,ICANN董事会起初抵制这个流程,抵制设立一个独立的问责制流程。
在伦敦会议上,我们这些社群成员不顾ICANN董事会的反对,创造了问责制流程。NTIA支持我们这样做,国会也支持我们这样做,表示不能只移交这些职能,却不考虑加强问责机制。原先,美国政府有能力将IANA职能从ICANN机制中剥离出来,美国政府可以利用这种能力约束ICANN。一旦美国政府和ICANN之间的合同不再存在,便意味着没有人能够约束ICANN,因为ICANN跟行业协会不同,ICANN不是一家成员制机构,在成员制机构里,成员可以解雇领导,我所在的NetChoice成员就可以解雇我,但是在ICANN机制中,ICANN成员无法挑战ICANN董事会的决定或解雇董事会。ICANN成立之时,成员就不拥有这种权力。于是,我们所做的,就是将这项权力加进ICANN机制中去,这样可以确保ICANN机构服务于社群。后来,虽然我们并没有成功地使用成员制来改造ICANN,但我们找到了加州法律中的另外一种机制安排,叫做指定者模式(designator model),通过这种方式,拿回了不少权力。我们本来想要推动成员制模式(membership model),但是ICANN董事会强烈反对。2015年10月,曾经进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僵局。要么,问责制工作组(CCWG)强推成员制模式,同时明知ICANN董事会将抵制,要么,我们转变思路。后来,我们转变了思路,选择了指定者模式,既保住了成员制模式下的不少权力,也解决了ICANN董事会的一些担忧,他们曾经担心我们的个别成员具备突然发起法律行动的权力。
徐培喜:说到这里,我想重复一下您过去使用的那个特别生动的比喻,您利用汽车和司机的关系来比喻域名系统。您说我们可以通过汽车和司机的关系来理解这次移交。域名系统是一辆车,九十年代在美国设计和建造,汽车牌照上写着IANA。1998年,ICANN得以创立,作为指定的司机。车钥匙被交给了ICANN
戴尔比安科:他们拿到了车钥匙,但是他们没有拿到车的所有权文件。通过IANA合同,美国政府持有所有权文件,文件包括名称、号码以及协议参数核心职能。18年以后,这辆车的司机展示出了足够的成熟度和能力。是时候让他们拥有这辆他们一直在开的车了。这就是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所涉及的问题,就是交出所有权文件。在美国,我们管这些文件叫做title。当然,所有权并没有交给ICANN这家公司。由于在责制流程上所做的工作,所有权落到了社群,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具体名字叫做赋权社群(Empowered Community)。他们是这辆车的所有者,就像是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成员是行业协会的所有者。赋权社群是ICANN的所有者。
徐培喜:往前追溯您提交给国会听证会的本本,您在2014年4月听证会上提交的文件,是不是就是您提出了那些场景和压力测试(Stress Test)?
戴尔比安科:是的。在2014年新加坡会议上,我提出了压力测试这种想法。我是一个程序员,在我编写的软件中,我经常使用压力测试,来检测异常使用状况。一般而言,你编写软件的时候,都是针对目标使用状况。但是,你必须针对异常的使用状况进行测试,用户可能绕过你设定的路径,不按照正常路数出牌,你要预期,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应该如何处置?极端使用状况是符合情理的,也是可能发生的。在软件上,需要应对这些情理之中的场景。在ICANN层面,我想使用同样的方法论。我创建了符合情理但不一定必然发生的场景,并测试新ICANN和旧ICANN会如何应对这些压力,当ICANN针对这些压力做出反应时,测试社群如何才能具备监督问责ICANN的能力,测试社群能否挑战ICANN的决定。这里,请注意,我设计这些压力测试,并不是为了防止压力本身的发生,而是为了保障当ICANN在针对这些压力做出反应时,对他所服务的社群负责任。有些人对这些压力测试存在误解,认为压力测试以及针对压力测试做出的反应,是为了防止压力的发生。
其实不能这样。压力就像一场金融危机一样,是会发生的。所以,要花心思思考ICANN会如何做出反应。比如,发生针对ICANN的黑客攻击,你的个人数据被披露。这类事情都是可以假定发生的,这里要做的,倒不是努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而是思考ICANN会做出何种反应?这种反应是否负责任?所有这些压力测试尝试评估两件事情。今天的ICANN和明天配备了我们新的问责机制的ICANN如何对自身的行动负责任?跟当下的机制相比,新的机制是一样好还是更好?
的机制能否确保社群有能力问责ICANN?并战ICANN对场景的反应方式?
徐培喜:整个压力测试机制都是您的主意?在听证会上,您为什么把自己设计的“压力试18”(Stress Test #18)单独挑出来说?并玩笑称之为“臭名昭著的压力测试18”?
戴尔比安科:答案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我出了压力测试的概念,并且写了最初的几个压力测试,先向国会提交了建议,然后又提交给ICANN。接下来,CCWG-问责制工作组流程启动了,许多其他人提出了新的压力测试建议。最终,我们得到大约40个。其中,有几个是NTIA建议的,有几个是ICANN董事会建议的。GNSO被内部人士独占怎么办?ccNSO排斥一些人加入怎么办?所以,压力测试的名单越来越长。通过这些压力测试,我们想要检测我们设计的那些跟问责有关的机制,比如,抵制某条章程条款的能力,批准根本章程的能力,挑战ICANN预算的能力,获取社群支持挑战ICANN决策的能力,解散某个ICANN董事会成员或整个董事会的能力。因此,我们研究了这些机制,也考察了已有的问责机制。我们对这些机制进行压力测试,来检验它们是否赋予了社群足够的可以挑战ICANN决策的能力。
“臭名昭著”是因为各国政府的抵制,他们不愿意做这个压力测试。我觉得这具有讽刺意味。你不能蒙上眼睛,假装压力测试并不存在。我早就注意到政府咨询委员会(GAC)具有修改决策规则的能力,如果绝大多数政府投票修改,就可以实现这一点。所以,他们有能力将全体共识原则,改为大多数共识原则,或者绝大多数共识原则。这意味着政府能够扩大自身对ICANN决策的影响力。所以,我就设计了压力测试18,应对政府改变决策方式的可能性。起初政府说,我们不会改的。但是,压力测试可不管这些,压力测试只考虑情理中这件事情是否会发生。政府无法否认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我并没有宣称这件事情必然发生,我甚至没有说政府有这样做的动机。但是,这件事得到了讨论。政府咨询委员会对更改决策方法进行了讨论,一些政府试图拥抱绝大多数或大多数投票模式,因为他们觉得政府咨询委员会内部很难产生全部共识通过的建议。
徐培喜:全体共识已经被写入章程。分离政策(Carve-out Policy)是什么意思?
戴尔比安科:让我们转向赋权社群,CCWG-问责制工作组认为,政府是互联网社群的一部分。政府拥有自己的网站,使用互联网沟通商业和公民主体,同时为公民提供公共政策保护。所以,政府自然应该成为赋权社群多利益相关方的一部分,我们热烈欢迎政府加入我们,我们也邀请其他咨询和支持组织加入我们。这件事跟政府咨询委员会(GAC)针对董事会的咨询角色没有关系。赋权社群是一个新的群体,既然GAC是其中的一员,那么他们当然会参与那里的决策。GAC拥有通过全体共识向董事会提建议的权力,这本来跟赋权社群里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让我们假设一个场景,ICANN收到GAC关于某个政策的建议,董事会决定接纳这条建议,赋权社群可以挑战董事会,要求他不执行GAC的建议,如果赋权社群这样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GAC作为赋权社群的成员,就不能阻挠赋权社群行使自己的权力。所以,分离政策就是考虑到了GAC建议被董事会采纳时,GAC不能同时在赋权社群阻挠其他社群成员展开针对这条建议的行动。
徐培喜:在摩洛哥召开的ICANN第55届会议上,针对GAC在ICANN的权力受到限制,法国政府为什么表达了巨大的不满?
戴尔比安科:让法国人生气的原因不仅仅只有分离政策这件事。我觉得跟压力测试18和分离政策都有关系。
我在众议院委员会的证词中引述了法国人说的话,是因为一些参议员认为这次移交给了政府太多的权力。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所以我在证词中用整个第五部分解释为什么我们并没有给予政府更多的权力。我们创建了赋权社群,政府是赋权社群的一部分,但是,不仅政府如此,所有咨询组织(AC)和支持组织(SO)都是赋权社群的一部分。我们削弱了政府提出建议的能力,如果赋权社群内部要对GAC向ICANN董事会提出并被接纳的建议采取行动,GAC不能从内部进行阻挠。所以,我们在赋权社群中给了GAC相对应的地位,但同时削弱了GAC提建议的权力。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限制了而非提高了政府的权力。
徐培喜:我个人觉得政府在ICANN机制里的权力应该是被边缘化了。
戴尔比安科: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我们并没有边缘化政府的权力。我们只是限制了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权力并没有被减少,也没有被增加,只是被限制得很紧。他们是多利益相关方社群中的平等成员。但是,在向董事会提建议这个特殊角色上,我们确实要求政府不能鱼和熊掌兼得,如果他们要降低共识原则的门槛,那就不能同时拥有这种特殊权力。
补充说一下管辖权问题。ICANN位于哪里,管辖权在哪里,这两个问题是相互独立的。管辖权是一种当ICANN的行为影响到别人时所产生的问题。例如,ICANN要求注册商在WHOIS系统上呈现完整信息。但是,诸如爱尔兰等国家的隐私法较为严格。爱尔兰便拥有针对跟ICANN签合同的这些注册商的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法律凌驾于ICANN合同之上。如果一个国家觉得本国公民或自身利益受到了影响,便可以确立自身的管辖权,ICANN受此约束。
徐培喜:您认为这次移交会顺利进行,还是说会出现延迟?
戴尔比安科:现在章程已经就位了,我觉得在执行层面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工作。眼下,美国处于一个政治上比较敏感的时刻。美国总统候选人和国会表达了新的关切。在我证词的第五部分,我回应了这些关切。但是,考虑到当下的政治现实,延迟几个月也有可能,放在大选以后、下一任总统上任之前。如果出现这种延迟,那并不会伤害这次移交,同时还可以避免一些政治上的炒作,能够降低政治温度。
如果短期暂缓移交的话,也不会带来问题。短期暂缓移交最多是延期三个月。这不会危害这次移交计划,反而会保护其免受一些政治辐射。当然,我不是决策者,我只是当别人问起的时候捎带解释一下。这个方案可以承受吗?当然可以,不仅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可以承受,美国政府和ICANN皆可承受。
徐培喜:那些希望长期搁置移交的人包括统基金会的研究人员。
戴尔比安科:是的。不过,称他们为研究员可能不够准确,他们是政策分析人员。他们希望延迟两年移交,我完全不赞成。如果国会或者美国政府做出延期两年的决定,会向世界传达不好的信号,说明美国不信任多利益相关方社群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说明美国并没有放弃IANA合同的意图。这会唤醒联合国和ITU的兴趣,迈进美国政府穿的鞋子里(指接替美国政府当前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我建议美国应该赶紧甩掉这双鞋,将IANA职能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合同没了,联合国也就没有了任何抓手。记住,这三个层面:名称、号码以及协议参数社群。如果ICANN脱轨了,被政府或联合国俘获,名称社群能够拿回根目录(the root)自行公布。根目录是一个两列、无数行的表格。这些人既然能够将它们编辑到一起,也能轻易地公布出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可以选择从他们那里拷贝根目录,也可以选择从ICANN那里进行拷贝。这件事非常容易做。第二是协议参数,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他们可以自行公布参数。他们不需要ICANN的帮助。第三是号码。地区互联网注册机构向各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分配号码。ICANN实际上并不扮演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激发了不满,这三项IANA职能的客户社群具有单干的可能性。
采访时间:2016年6月28日 采访地点:芬兰赫尔辛基ICANN56
格罗斯:(David A. Gross)美国全球传播政策前谈判大使,自从1990年代以来,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关于互联网问题的谈判,次数记录至今无人超越。同时,格罗斯多次参加中美互联网产业论坛。教育世家出身,熟知ITU以及ICANN政策,代表美国互联网治理联盟(Internet Governance Coalition)的声音,该联盟由13家企业组成,包括AT&T、思科、Comcast NBCUniversal、脸书、GoDaddy、谷歌、Juniper网络、微软、西班牙电讯、迪士尼、时代华纳、福克斯、威瑞森通讯。
徐培喜:关于2012年举办的国际电信世界大会(WCIT),您曾写道,本来这次会议的重点应该关注如何更新1988年电信条约,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借此希望让国际电信联盟(ITU)参与到互联网治理中来,包括美国在内的55个国家对此表示不接受。为什么国际电信联盟如此不受美国政府欢迎?
格罗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不觉得国际电信联盟不受美国政府和美国业界的欢迎。国际电信联盟负责的事务非常重要。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国际电信联盟,仍必须重新成立类似国际电信联盟这样的组织。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处理跟频谱(spectrum)有关的问题上。因为国家之间存在边界,协调跨界无线电通信和频谱相关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跨境移动通讯、卫星通讯等问题。卫星通讯也很重要,国际电信联盟负责将信号区段分配给企业和政府。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全球组织,来负责这些重要的事情。国际电信联盟在电信标准方面一直做得很好。与其他标准组织相比,国际电信联盟非常传统,它负责的是电信业务,而不是互联网业务,并且一直都做得很好。国际电信联盟在发展领域问题上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它关注发展中国家。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一直都对国际电信联盟给予很大支持。
但是,美国政府和ICANN都反对由一个政府间国际机构监管互联网,这并非仅仅针对国际电信联盟,任何国际机构都不行。互联网监管应该交给多利益相关方,就像ICANN那样。我们承认,在国内层面,各国政府都承担着各种监管职能,但是,在国际层面,国际机构不该有监管或控制互联网的尝试。这样做没有必要,同时也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所以,我们反对扩大新版《国际电信条约》的管辖权,不希望国际电信联盟将手伸到互联网治理领域。今天,我们的立场仍是如此。不仅是国际电信联盟,任何国际组织,都不应该有监管互联网的权限。
徐培喜:如果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当时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又会怎样呢?
格罗斯:我们所担心的是,他们会借此来限制信息自由流通,限制创新的发展。
徐培喜:就ICANN内部机制而言,政府或政府咨询委员会(GAC)的权力已经被严格限制或边缘化,这是不是实现了您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谈判中代表美国政府所提倡的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说,市场主体在ICANN崛起?
格罗斯:我不认为这是市场主体的崛起,只是一种进一步的演化,并且让人们意识到,只有各个利益相关方都广泛参与,才能做出更好的决策。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政府不应该独自控制互联网,市场不应该独自控制互联网,公民社会也不应该独自控制互联网。他们应当各司其职,携手合作。这样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在新的IANA流程下,这是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徐培喜:您觉得这次移交会顺利进行,还是会出现延迟?
格罗斯:我对此很谨慎,但很乐观。9月30日之前我们会知道答案。国会有可能采取行动进行阻碍,但是国会必须通过立法方能成功。在美国体制下,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而是说时间很紧。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顺利移交,尽管可能会有所延迟。
徐培喜:这个过程为什么如此充满戏剧性?
格罗斯:我倒是能体谅这些波折。ICANN和IANA流程一直运转良好,至少从1998年开始是这样。互联网一直都很稳定、安全。所以大家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去改变一个运转良好的机制?为什么要做出改变?我本人的观点当然是,这次移交能让互联网更加稳定,更值得信赖。但是有人抱持“既然没有出问题那就维持现状”的心态,我也能够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另外,很多美国人无法理解,美国政府放弃了IANA职能监管权,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当然,在我看来,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放弃什么,移交是一种积极的变革。但是,有人从心理上做出不一样的反应,我也能够理解。政治人士之间的分歧也由此体现了出来。这些分歧最终会有结果,但是这次移成为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责任编辑:李晓晖)
ICANN背景链接
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的全称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成立于1998年,是一个非营利公益性国际组织,负责名称、数字、协议参数等互联网关键资源的管理,设有地址支持组织(ASO)、国家代码名称支持组织(ccNSO)、通用名称支持组织(GNSO)三个支持组织和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ALAC)、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RSSAC)、政府咨询委员会(GAC)、安全和稳定咨询委员会(SSAC)四个咨询委员会。
ICANN在程序上奉行自下而上、多利益相关方等原则,由各国政府、商业力量、民间团体共同决策。在代码即为法律的时代,这个机构对于维护互联网的稳定运行非常重要。ICANN每年在不同地区召开全球会议,该会议机制在程序上具有完整的开放性,任何人都可以注册参会。2016年9月30日,美国放弃了通过IANA职能合同对该机构的单边控制,使得ICANN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和社群支持。如今,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不仅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标杆,还影响了许多讨论全球问题的论坛。
2016年10月1日,美国政府和ICANN签订的IANA职能合同正式到期失效,美国政府放弃IANA职能的管理权,将其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该话题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热门政治议题,以下初步梳理了近期关于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的各方观点。
一、反对派
美国国内反对派试图阻碍或延迟,因为移交管理权可能危及网上言论自由,威权国家将获得对互联网内容的影响力。
关于ICANN政府咨询委员会(GAC)权力的争议,一些国家认为政府在ICANN新机制中被彻底边缘化,从而为“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美国产业利益集团让路。[1]
以克鲁兹为首的国会保守派
克鲁兹(Ted Cruz)
共和党参议员,曾为了反对奥巴马“健保改革法”拨款导致美国政府关门。

发动了一系列反对移交的运动,声称美国监管的逐步退出将为威权政府控制互联网打开大门,“他们不保护言论自由,他们积极地审查互联网,ICANN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2]将移交称为对俄国和其他国家的“赠品”(giveaway)。[3]
9月14日,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引用了华盛顿邮报批评ICANN渎职的社论,质疑一个前ICANN领导人继续为中国政府提供建议的行为;其盟友还指向ICANN的业绩记录,包括其2014年混乱的域名扩张给它带来数亿美元收入。[4]
9月21日,在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的支持下,试图对美国临时拨款法案附加条款来阻碍管理权移交,被驳回。
9月28日,四个共和党州——德克萨斯、亚利桑那、俄克拉荷马、内华达四州——的总检察长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反对联邦政府移交管理权的诉讼,认为移交是违宪的,需要经过国会批准。被驳回。[5]
特朗普(Donald Trump)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认为美国政府放弃对互联网关键业务的管理权会面临在线信息外部审查的威胁,奥巴马利用权力将互联网控制权移交给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而民主党和希拉里没能保护在线活动。
9月21日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表声明,声称奥巴马总统计划将互联网控制权交给联合国,表示反对管理权移交。并试图直接插入国会正在进行的临时拨款法案的立法谈判议程中,被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直接忽视。其政策主管米勒(Stephen Miller)声称此举使互联网自由处于危险中。
罗森茨威格(Paul Rosenzweig)
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副助理部长

管理权移交中唯一失去权利的是美国政府,支持进行移交但需要改进,以处理如何解决关于知识产权索赔和人权投诉的争端。[6]
2016年7月7日,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技术自由(Tech Freedom)智库主办了“What Are the Concerns about Ending the U.S.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with ICANN?”克鲁兹发表了主题演讲,技术自由智库主席斯佐卡(Berin Szoka)、遗产基金会的舍费尔、律师麦格雷迪(Paul McGrady)和科温(Philip Corwin)、应用协会(App Association)的佐克(Jonathan Zuck)进行了小组讨论。
舍费尔(Brett Schaefer)
遗产基金会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由中心的国际监管事务研究员

互联网对美国政府放弃其作为互联网治理的最终保证人的长期角色是否准备好,舍费尔对此持怀疑态度,担心过早批准移交将使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失败,政府将获得对互联网新的影响力,互联网自由会受到影响。建议延长一、二年的NTIA与ICANN合同,审查移交方案,完成社群所寻求的所有改革或者进行部分移交。[7]
二、支持派
2013年斯诺登事件使美国在IANA职能管理权方面扮演的特殊角色受到高度怀疑和批评,导致互联网分裂风险。
有观点认为放弃IANA职能的管理权或许会软化一些要求数据本土化的立场,还可避免联合国接管美国政府的特殊角色。[8]而如果延迟移交则会适得其反,将会损害美国在互联网标准和安全国际谈判中的信誉。
ICANN多年来承受了一定比例的抱怨,对互联网成长的适应太慢;许多国家认为美国的监管使其不能真正国际化。[9]
以克鲁兹为首的国会保守派
(一)美国政府
美国商务部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

表示如果贯彻并完成移交,有助于确保私有部门在跟互联网技术结构有关的决策中继续保持领导地位,避免一些外国政府以美国政府的特殊地位为借口主张应该由政府控制互联网域名系统。[10]
施特里克林(Lawrence E. Strickling)
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NTIA局长,美国政府对口ICANN的主要负责人,移交的主要决策者。

这种改变为“保护互联网自由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将在移交后实施强健的制衡措施确保互联网技术管理权得到妥善处理。
关于一些主要争议的观点:[11](1)这次管理权的移交是基于1997-98年制订的私有化目标持续进行的过程,在ICANN机制已经足够成熟以及国际社会对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机制的支持也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才在2014年推出正式移交计划;(2)在ICANN的新章程里政府的权力基本上保持原样;(3)总部必须位于加州这个条款,为了落实社群在问责制方面的期许;(4)某些人对NTIA放弃监管权违反联邦法律的指控毫无事实依据,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扭曲事实。
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卡特赖特(James Cartwright):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支持管理权移交因为它将为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各地自由和开放的互联网铺平了道路,坚信这是正确的事情。
(1)认为反对者关于联邦监管对保护互联网的自由是必要的,私有化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论点是错误的。如果华盛顿未能兑现其私有化的长期承诺,它将重燃独裁政权将互联网治理移交给联合国的努力,由此可能将互联网置于风险中。
(2)放弃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将迫使其他国家建立新的DNS系统,破坏自由开放的全球互联网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果美国拒绝将管理权移交给私营部门,那么私营部门可能会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没有任何声音。
(3)该提案包含了所有的声音,并建立在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基础上,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政策。[12]
切尔托夫还认为如果不转移到一个更全球化的治理方式,会成为分裂互联网的口实,因为不放弃管理权就是存在不良动机,所以必须经历这个过程以维护美国信誉。
格罗斯(David A. Gross)
美国全球传播政策前谈判大使,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关于互联网问题的谈判

这次进展表明即使是复杂和困难的互联网相关问题也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社区驱动的过程成功解决。鉴于美国长期以来作为多利益相关方解决互联网治理相关问题的拥护者,这次成功对美国来说将是非常好的消息。[13]
(二)美国产业界和行业协会几大公司(Intel, Amazon, Microsoft, HP, Dell, Cisco)和行业组织(USCIB, i2Coalition, Internet Association, CCIA, ITI)写给国会的公开信(2016.4):
“我们的公司依赖于互联网稳定和安全的未来,互联网的寻址系统有助于保持互联网的全球性、可扩展性和互操作性”;“确保该系统持续的安全、稳定和弹性的一个重要提案已获得ICANN董事会批准并交付给美国政府”;“我们的公司和行业协会与来自公民社会、政府和技术社群的代表一起制定了提案,以便使美国政府能够无缝地将互联网寻址系统的管理权移交给全球利益相关者”。[14]
在国会的共和党议员试图阻止移交后,主要的互联网公司和行业组织再次写联名信敦促国会不要阻碍“势在必行”的变革(2016.9)。认为一个全球性的、互操作的和稳定的互联网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将继续致力于完成到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转变,以最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15]
沃克(Kent Walker)
谷歌总法律顾问

称IANA过渡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会使创新者和用户在全球互联网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它确保了互联网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使互联网的未来掌握在用户和创新者的手中,而不是独裁政府,保护其免于分裂。[16]
戴尔比安科(Steve DelBianco)
美国互联网行业协会NetChoice执行总裁,ICANN“商业利益相关方社群”政策主席,ICANN新章程的关键设计师和压力测试机制的缔造者。

在徐培喜对其的专访中,[17]表示NetChoice所有成员公司都极力反对将ICANN纳入联合国或其下属的ITU体系,因为该体系下国家选票可能被用于利益交换,而私营团体没有投票权。
此外对外界的一些误解进行了解释:(1)斯诺登泄密事件跟域名系统(DNS)没有任何关系,但为某些政府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及数据本土化提供了动机;(2)ICANN压力测试机制的设计不是为了防止压力本身的发生,而是为了保障当ICANN在针对这些压力做出反应时,对他所服务的社群负责任;(3)ICANN总部落在加州是为了选择加州法律中的指定者模式(designator model)作为ICANN问责制流程,并不意味管辖权也落在加州。
贝克尔曼(Michael Beckerman)
互联网协会(Internet Association)主席&CEO

互联网协会认为一个强大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是维护互联网免于政府控制的最佳方法。维护美国政府的特殊角色会鼓励其他政府建立自己的系统,危及全球互联网的无缝功能和开放性。互联网分裂也将阻碍在线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世界言论自由,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本,不进行移交的风险是显著的,因此应该支持移交。不能成功落实IANA管理权移交将破坏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潜在地剥离掉使如今互联网如此成功的模式的权利。[18]
布朗(Kathryn Brown)
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y)主席

相信该计划能够服务于世界各地互联网用户的广泛利益,相信运营社区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承诺。[19]认为任何延迟会增加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使政府控制互联网的可能性更大。
(三)技术社群和公民社会
苏利文(Andrew Sullivan)
互联网架构委员会(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主席

认为互联网已经为IANA管理权移交等待了很长的时间,延迟没有益处反而可能带来坏处。他觉得该提议是一个可行的方式,能够使政府走出其不需要执行的功能,并确保IANA照常运行。现在IANA负责互联网有限的工作,在将来也基本不变。虽然为了能够移交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变化,但这些都是基于正在运行的互联网功能并符合其他已存在的互联网功能。[20]
公共利益集团(如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Human Rights Watch, Open Technology Institute, Access Now, Public Knowledge Advocate)发表声明支持IANA管理权移交。[21]
三、其他国家
(一)俄国
尼基福罗夫(Nikolay Nikiforov)
俄罗斯通信和大众传媒部长

之前曾指责IT全球系统实际上完全由一个国家和几家公司主导,这不仅指科技巨头的市场份额,也包括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关键要素的控制。这种长期的垄断使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致力于技术解决方案,以防止对国家网络可能的外部破坏性行动。[22]
对于IANA管理权移交,尼基福罗夫在该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俄方欢迎美国商务部的这一决定,并认为此前美商务部下属机构单方面制定的互联网管理条款导致了失衡的互联网管理模式。表示俄罗斯坚持认为互联网这一全球性资源不应被某国不公开地管理,而应遵循公正的国际法机制加以管理。认为此前ICANN奠定了至少两种不平等的权力,一是美国政府相对于其他国家政府的权力,二是政府相对于其他大多数利益相关方的权力。[23]
沃罗比约夫(Andrei Vorobyov)
俄罗斯国家域名管理协调中心主任

“公共技术标识符”接管互联网域名管理权,不应成为国际社会参与互联网管理系统的最终解决措施。他表示,实现上述移交后,“公共技术标识符”组织应该公开透明地开展工作。但这一组织仍按照美国法律被设立在加利福尼亚州,受美国司法管辖,这就会造成以下结果:一旦在域名管理中出现争议,负责审理争议的将是美国法院而非国际法庭。[24]
(二)法国
认为美国政府过分强调中俄等威权国家的风险来迫使其他国家政府同意GAC成为一个被减弱的角色。而且作为属于加利福尼亚的遵循美国法律的非营利组织,美国政府仍然保留了对ICANN明显的控制权。
阿克塞勒•勒迈尔(Axelle Lemaire)
法国政府主管数字行业的国务秘书

担忧这一改革将导致ICANN的私有化而非国际化,尽管公民社会和各国政府努力达成了一个平衡的妥协,但其中某些要素会使国家在ICANN的决策过程中边缘化,特别是与私营部门将扮演的角色相比。[25]
(三)德国
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

对美国政府终结对互联网核心功能的独家监管表示欢迎,称新的管理模式是“支持自由互联网的清楚信号”。他说,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能对大量观点和利益进行平等考虑,继而确保互联网的创新和稳定。
(四)中国
新华社刊文指出

事实上,这次“交权”并非美国政府心甘情愿,而是在国际社会强大压力下的一点点让步。同时,美国政府也不是随便“交权”,而是设置了严格的前提条件,即交给“全球互联网多利益攸关社群”,并设立了复杂的制衡系统,以保证自己在形式的“交权”后仍拥有隐形的控制权。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巨头在“多利益攸关模式”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美国将通过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的企业、硬件和软件技术、人才等优势继续保持影响力。[26]
(整理:陈帅;责任编辑:李晓晖)
参考文献
[1] 徐培喜 . IANA 职能管理权移交谁是赢家 . 网络空间研究学刊,2016-10-02.
[2] Ted Cruz: We Must Keep the Internet Free. 6/24/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WHeVy003c
[3] Internet Oversight Transfer Clears Hurdles to Take Place Saturday. REUTERS, SEPT. 30, 2016.http://www.nytimes.com/ reuters/2016/09/30/technology/30reuters-cyber-internet-transfer.html?_r=0
[4] Cecilia Kang, Jennifer Steinhauer. Ted Cruz Fights Internet Directory’s Transfer.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5,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09/16/us/politics/ted-cruz-internet-domain-names-funding.html
[5] Ted Cruz: We Must Keep the Internet Free. 6/24/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WHeVy003c
[6] AP FACT CHECK: Is US Giving Away the Internet? AP, SEPT. 22, 2016. http://www.nytimes.com/aponline/2016/09/22/business/ap-us-campaign-2016-fact-check.html
[7] ICANN Transition Is Premature: Unanswered Questions Require an Extension, Partial Transition.SEPT. 08, 2016. http:// dailysignal.com/2016/09/08/icann-transition-is-premature-unanswered-questions-require-an-extension-partial-transition/
[8] 转引自戴尔比安科,来源:徐培喜《专访 ICANN 新章程的关键设计师戴尔比安科》
[9] AP EXPLAINS: What's at Stake as US Cedes Internet Control. AP, SEPT. 29, 2016. http://www.nytimes.com/aponline/2016/09/29/technology/ap-us-tec-ap-explains-us-internet-transition.html
[10] NTIA, 2016-06-09. http://www.ntia.doc.gov/press-release/2016/iana-stewardship-transition-proposal-meets-criteria-complete-privatization
[11] 徐培喜 . 专访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劳伦斯 • 施特里克林(Lawrence E. Strickling). 网络空间研究学刊,2016-10-01.
[12] Michael Chertoff And James Cartwright, “How to keep the Internet free and open,” Politico, 6/7/16. http://www.politico. com/agenda/story/2016/06/keep-internet-free-and-open-icann-000140
[13] David A Gros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 Transportation,” 5/24/16
[14] “Open Letter To Congress From U.S. Business,” April 2016.
[15] Letter, September 13, 2016. http://t.umblr.com/redirect?z=https%3A%2F%2Finternetassociation.org%2Fwp-content%2Fuploads%2F2016%2F09%2FIANA-Letter-091316.pdf&t=MzY3MThhMTA4ODdlYjM2OWM4OTk1OTg1ZDllNzA1NDY0MDcxOGM4NixjUVJhejBzOA%3D%3D&b=t%3AbdiNo6lft4TJxWnIrYhvGw&m=1
[16] Kent Walker, “Preserving A Free And Open Internet,” Google Public Policy Blog, 9/26/16. http://blog.internetassociation.org/post/151013524143/what-theyre-saying-about-the-iana-transition
[17] 徐培喜 . 专访 ICANN 新章程的关键设计师戴尔比安科 . 网络空间研究学刊,2016-10-02.
[18] Michael Beckerma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 Transportation,” 5/24/16.
[19] Kathryn Brown, “Important next step in IANA Stewardship Transition: NTIA says proposal meets criteria,” Internet Society, 9/16/16. 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blog/public-policy/2016/06/important-next-step-iana-stewardship-transition-ntia-says-proposal-meets
[20] Andrew Sulliva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 Transportation,” 5/24/16
[21] “Civil Society Statement of Support for IANA Transition,” Best Bits, 5/24/16. http://bestbits.net/iana-transition/
[22] Russia working on ways to protect its internet due to US online dominance – Com. Minister to RT .https://www.rt.com/ news/334269-nikiforov-interview-rt-egypt/
[23] http://www.mngz.ru/russia-world-sensation/2281381-nikolay-nikiforov-privetstvuem-zayavlenie-lourensa-striklinga-o-zavershenii-goskontrakta-ssha-na-vypolnenie-funkciy-iana.html
[24] 互联网域名管理权移交的喜与忧 . 新华社,2016-10-03.http://m.cankaoxiaoxi.com/science/20161003/1328583.shtml
[25] Kieren McCarthy. French scream sacré bleu! as US govt gives up the internet to ICANN. 24 Mar 2016. http://www.theregister. co.uk/2016/03/24/france_slams_us_govt_internet_transition/
[26] 美国真的放弃互联网控制权了吗 . 新华社,2016-10-02.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6-10/02/c_1119659844.htm
2016年8月16日,美国商务部国家通讯与信息管理局(NTIA)致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号码分配机构(ICANN)的一封短信令全球互联网沸腾。信中称:“NTIA于2016年8月12日收悉ICANN提交的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管理权移交实施状态报告。报告确认管理权移交的所有任务已经或者将于2016年9月30日之前完成。NTIA全面审查了该报告。经审议,克服巨大困难,NTIA意愿允许IANA功能合同于2016年10月1日到期。”
寥寥数语,信息量很大。吸引了全球目光的IANA管理权移交究竟为何?移交如何实现?未来发展如何?
2014年3月14日美国商务部国家通讯与信息管理局(NTIA)宣布愿意将负责互联网核心资源的IANA的管理权移交给利益相关各方的全球社群,管理权移交的大幕从此开启。IANA管理权是何方神圣?引群雄逐鹿?它其实是开启互联网黑魔法的钥匙。
互联网域名系统最初的技术开发者与管理者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Jon Postel博士,他掌管互联网初期核心资源如根服务器的管理和分配。1987年他分配了7个根服务器(后扩展为13个根服务器),全部位于美国。由于互联网增长迅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国政府认为一个人管理这些互联网核心资源不够安全,1988年,美国政府要求Jon Postel采取更安全和更合理的措施来保证互联网核心资源的分配和管理。JonPostel于是建立了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负责管理互联网核心资源。1988年以后的互联网资源分配即由IANA进行。IANA有三项职能:(1)管理全球域名系统;(2)协调互联网协议(IP)数字地址的分配;(3)根服务器协议的协调。这三项权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互联网根的管理权。IANA是互联网这样完全非中心化的分布式构架中唯一中心化的部分。不知如此设计,是Postel博士的天才还是错误。
ICANN于1998年建立,总部设在洛杉矶郊区Marine Del Ray,是一个采用国际化组织形式运营的非盈利性机构。ICANN机构注册地在美国,是遵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成立的非政府机构。ICANN必须遵守美国法律,并可受到美国的司法管辖。
ICANN建立之始,美国商务部与ICANN签署了“合同”,将IANA功能以“零成本”委托给ICANN管理。双方合同约定,IANA所管理的根服务器功能系美国政府资产,美国政府通过有期限的合同将IANA委托给ICANN来运行。IANA从此成为ICANN的一项功能,由其一个内部部门运行。根据和美国商务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和合同,ICANN的工作就是负责在互联网域名系统和地址系统上的政策协调。ICANN形成的政策决议,由IANA人员在根服务器的根区文件中进行体现。美国商务部对于IANA的运行有最终的管理权。
IANA系互联网核心资源,如同一个人的神经中枢,在身体健康、行动自如之时,只在“后台”悄然运行、难以察觉,但是一旦受到打击或者损害,就会导致整个人瘫痪。由于互联网的全球性特点,根的任何改动都影响到互联网在全球的正常运行,特别是互联网在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
美国政府对于IANA的终极管理权力,一向令其他国家与全球互联网社群不满。在斯诺登事件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抨击,在IANA管理权方面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2014年3月14日美国商务部国家通讯与信息管理局(NTIA)宣布,IANA的管理权将移交给利益相关各方的全球社群,责成IANA的现行运行机构ICANN召集全球利益有关各方,发展形成有关IANA管理权移交的建议。美国商务部国家通讯与信息管理局要求ICANN所提交的建议应当在得到全球社群广泛支持的前提下,符合如下4项基本原则,即:(1)应当支持与加强利益有关各方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2)应当保持互联网域名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强韧性;(3)应当满足全球IANA使用者与合作者的需求与预期;(4)应当保持互联网的开放性。
1、IANA管理权的移交方案
为此,ICANN于2014年7月成立了IANA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ICG),由来自13个不同社群的30位专家组成,其中包括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有关方。鉴于IANA功能与使用者分为域名、数字地址、互联网协议参数三个部分,协调小组让域名社群(由ICANN内部的支持组织与咨询委员会组成)、数字地址资源社群(由地区性互联网地址分配机构RIR组成)和互联网协议参数社群(由互联网工程工作组IETF组成)三个不同社群分别形成有关的建议。三个社群按照自身的程序与方式形成关于IANA管理权移交的相关建议,提交协调小组。协调小组在征求公众意见之后,整合三个社群的建议,最终提交美国商务部NTIA。美国政府有权审议有关的建议是否符合移交管理权的前提条件与基本原则,并最终决定是否完成IANA管理权的移交。
2015年10月协调小组公布了关于IANA管理权移交的域名、数字地址、互联网协议参数三个社群已经完成的建议方案。
(1)以IETF为代表的互联网协议参数社群对于ICANN目前运行IANA的相关功能表示满意,不建议移交管理权之后进行改变。
(2)以RIR为代表的数字地址社群基本同意ICANN继续运行IANA的相关功能,但是将与IANA运行机构签订服务水平合同,并建立由来自RIR的社群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审议IANA运行机构的服务情况。
(3)由ICANN各个支持组织与咨询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域名社群工作组建议:(a)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法人组织,即“移交后的IANA”(简称PTI),不再是ICANN的内部部门,根据与ICANN之间的合同,成为ICANN的一个分支机构及IANA中的域名功能的运行机构。ICANN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司法管辖权维持不变。(b)建立使用者常设委员会,根据合同要求与服务水平的预期,监督移交后的IANA的运行情况。(c)建立利益有关各方共同参与的IANA功能评审程序,审议IANA与域名相关的功能的运行情况。(d)域名社群的建议以ICANN跨社群工作组正在形成的关于问责制度的建议完成为前提条件。
数字地址社群与互联网协议参数社群均同意域名社群关于建立“移交后的IANA”(PTI)的建立,保证移交后的IANA将运行现有的全部三项功能,但是三个社群将分别享有审议与变更相关功能的权力。
2、ICANN问责制度的改革
IANA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公布了三个社群的建议之后,收到的多方反馈,均对于IANA管理权移交之后ICANN的问责制度,各方表示了质疑与不信任。正如互联网社群不信任美国一国掌控IANA一样,ICANN如果独揽大权,也将不被信任。不论是ICANN的现行宪章还是ICANN的内部结构,均没有有效的内部与外部机制对于ICANN权力加以问责与制约。因此,IANA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表示在完成关于完善与改革ICANN问责制度的建议、并满足域名社群关于ICANN问责制度改革的要求之前,不将全部建议提交美国商务部。
2014年12月ICANN中的ASO、ccNSO、GNSO三个支持组织与ALAC和GAC两个咨询委员会(另外两个咨询委员会SSAC、RSSAC可以随时加入)共同起草了章程,建立了关于ICANN问责制度的跨社群工作小组(CCWG),以加强在IANA管理权移交之后ICANN的问责制度。[1]根据跨社群工作小组的章程,在终止与美国政府之间历史性的合同关系,IANA管理权转移给全球互联网社群之后,ICANN必须加强其问责制度,各个社群必须强化对ICANN权力的约束与制衡。同时,完善与改革ICANN的问责制度也是为了满足域名社群提出的IANA管理权移交的建议的要求。跨社群工作小组将其工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WS1)是在完成IANA管理权移交之前必须建立与强化的问责制度,第二部分(WS2)是在移交完成后可以继续开发完善、全面实施的制度。
跨社群工作小组由ICANN各个支持组织与咨询委员会的28名代表与175名其他自愿参与者组成,其中比较活跃、不断发言与提议的人不超过15人。跨社群工作小组经历了300多个会议与电话会议,三万多封电子邮件讨论磋商,前后四易其稿,先后三次征求ICANN社群的意见,终于2016年2月25日公布了关于第一部分的问责制度改革建议的报告。当时尚有少部分问题未能在各个社群之间达成共识,其后跨社群工作小组征求了各个支持组织与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后,形成了最终报告。
跨社群工作小组提出了完善与改革ICANN问责制度的12项建议,主要包括如下四类内容:
(1)修订ICANN的使命宣言,澄清了ICANN不得随意超越其使命范围行使权力或者发挥作用;
(2)强化了独立评审程序,通过有约束力的独立评审裁决,遏制ICANN越权行为;
(3)赋予ICANN社群7项新的权力,在现行的磋商、讨论、构建共识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对ICANN采取行动,包括:
-否决ICANN预算、IANA预算、ICANN五年期战略及运行长期计划;
-否决ICANN对其宪章核心内容的修改;[2]
-批准ICANN新的根本性宪章、细则及ICANN重大财产的出售与其他处置;
-罢免ICANN理事会中的某个成员;
-罢免整个ICANN理事会;
-发起独立评审程序,裁决结果对ICANN具有约束力,并可据此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否决ICANN理事会作出关于IANA功能运行的决定,包括不允许移交后的IANA独立或者分离的决定;
-监督与调查ICANN理事会、官员及工作人员的权力。
(4)发起社群性的独立评审程序,监督ICANN理事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的正当性与适当性。
上述所有建议的社群权力均必须在广泛磋商讨论、努力消除分歧,构建共识的前提下,才能行使。一旦磋商讨论无法达成共识,组成社群的支持组织与咨询委员会将通过多数票表决的方式决定是否及如何行使社群性权力。关于投票的程序及适合的投票人,各个社群之间存在很大的争议与利益冲突。政府咨询委员会(GAC)是否应当被排除在社群性权力之外就曾是争议的焦点之一。目前的妥协性方案是GAC在部分情况下被排除于社群性权力之外。GAC中的14个国家政府代表曾对此明确表示反对。
为了行使社群性权力,ICANN社群需要成为所谓“赋权性社群”,并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获得法律上的依据与支持。根据建议,赋权性社群将依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ICANN注册地)成为所谓“单一授权代表”(Sole Designator),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ICANN所有核心性质的治理文件(包括根本性宪章、细则)的修订都必须经理事会与赋权社群双方同意。
除此之外,跨社群工作小组还建议在如下方面继续工作,包括如何在ICANN中引入尊重人权的原则,如何将2009年9月30日美国政府和ICANN签署的“承诺确认文件”(Affirmation Of Commitments,AOC)中对于全球互联网社群的承诺引入宪章中,[3]以及如何加强各个社群组织自身的问责制度。跨社群工作小组还在筹备在IANA管理权移交完成后继续完善并监督有关的问责制度的实施。
3、进展情况
关于IANA管理权移交的方案与ICANN问责制度改革的方案,经ICANN社群的广泛讨论与评议,终于获得大多数的支持。根据管理权移交与问责制度改革所达成的方案以及美国商务部NTIA的要求,ICANN于2016年5月27日批准了对于ICANN宪章的修改,与IANA运行有关的其他机构签署了新协议,于8月9日批准了对于ICANN章程的修改。2016年8月10日,ICANN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递交了建立“移交后的IANA”机构的申请文件,新机构定名为“公共技术性识别符”机构(简称PTI)。在管理权移交完成后,PTI根据与ICANN之间的协议,将取代IANA并运行其所有的功能。
根据IANA管理权移交方案,ICANN应当在移交后的IANA建立相应的监督、审议机制。为此,2016年8月12日,PTI的根区评估评审委员会建立。8月12日,PTI的宪章公布,供公众评议。9月份,ICANN与PTI的各项功能协议与服务协议将相继公布,全部程序至9月底完成。ICANN于2016年8月12日向美国商务部NTIA报告了进展情况,并于8月16日收到了NTIA的正式回复,确认管理权的移交将于10月1日开始。
总之,IANA管理权移交与ICANN问责制度改革的方案是几经周折、利益有关各方冲突与妥协的产物,它看起来宏大、复杂、充满想象力,实际上还有诸多细节尚待完成,在实施中尚有诸多挑战。魔鬼总隐身在细节之中。
1、后斯诺登效应
2014年美国商务部NTIA作出IANA管理权移交的姿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国际社会对其一国控制互联网关键资源的长期压力,同时平息因美国情报部门大规模监控非美国公民被斯诺登披露所造成的国际社会、甚至其主要西方盟国的强烈不满。2015年10月6日,欧洲法院裁决欧盟委员会2000年作出的承认美欧之间跨境数据流动的避风港原则的决定无效,[4]理由是美国情报部门大规模地从避风港认证的公司获取数据,因此避风港无法充分地保护欧洲公民的个人数据。[5]欧洲法院的裁决说明,斯诺登事件仍然在持续发酵,美国继续单独控制IANA这一互联网关键资源已经丧失了国际信誉与合法性。
美国商务部作出关于IANA管理权移交的声明之后,得到了欧盟国家强烈支持与赞同,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美欧之间的联盟。在IANA管理权移交建议与ICANN问责制度改革建议的形成过程中,美国之外最为活跃的群体就是欧洲国家的政府、域名注册管理机构、企业界及民间组织的代表,他们参与讨论,提出议案,与美国的参与各方一起左右了建议的走向及最终的内容。因此,美国所谓将IANA管理权移交给全球互联网社群,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与欧洲盟国分享权力,巩固与重构美欧共同利益的联盟。
2、利益有关各方共同治理
IANA管理权的移交是对ICANN治理模式的考验。ICANN采用所谓“利益有关各方共同治理”的模式,为此还造出了Multistakeholderism一词。Stakeholder在国内还没有准确的翻译,在此暂且将其翻译为利益有关方,multi-stakeholder就被解释成了利益有关各方。
从ICANN的机构构成中就能看出,它是被互联网影响到的各国政府、顶级域注册管理机构(gTLDs和ccTLDs)、域名注册商、ISP、使用互联网的公司(如Google或可口可乐公司)或机构(如国际奥委会)、社会团体(如隐私保护组织)、学者以及普通互联网用户都可以以“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发起并“建立共识”设立政策的形式来参与ICANN的政策制定工作。
具体来说,如果有任何一个利益有关方(Stakeholder),在ICANN内部,如果有对于某个政策的设立或者修改的提议,不管这个提议是来自于社区成员还是ICANN外人事,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大会发言等形式向ICANN直接发表意见或建议。ICANN会将问题归类提交各支持组织与咨询委员会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提请公众讨论。如果提议得到认可,将会成立工作组起草政策建议。政策建议在得到支持组织与咨询委员会的认可之后,将会提交到ICANN理事会进行讨论。一旦通过,将成为ICANN的政策并得到执行。在整个政策讨论的过程中,ICANN都要尽可能通过其网站公开政策讨论的全部过程,并邀请所有人参与对创制政策发表评论或意见。
在ICANN的政策制定进程中,单个互联网用户可以就ICANN职责范围内的任何事务发起意见或建议。有的时候,一个政府的提议或建议会由于某个技术专家的反对意见而被阻止通过。在形式上,个人用户、商业机构、社会团体和一个国家政府所具有的政策建议权和参与的权利是一样的。
ICANN的多利益有关方模式是传统的IETF个人模式和国际组织多边模式的混合。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恰当地反映出互联网上ICANN职责的复杂性。一方面,ICANN仅仅是一个美国注册的私营性非营利公司,但是ICANN的职责和管理却是全球性的;另外一方面,ICANN以“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来制定政策,自称同时向ICANN内部的社群和外部全球互联网社群负责。
美国商务部为IANA管理权的移交设定了前提条件与基本原则,只能移交给互联网全球社群,明确排除了向联合国系统或者任何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移交的可能。但是,互联网全球社群并非清晰的可界定的概念,商务部所设定的条件为美国维护其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在建议形成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并未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干预各个社群或者相应的工作机构的工作,但是美国的企业界、域名业界、学者、民间智库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产生了左右全局的影响力,充分体现其在国际活动中非政府的软实力。同时,IANA管理权移交方案在ICANN社群得到大多数支持,被广泛认为是利益有关各方共同治理模式的胜利,该治理模式经受了考验,足以在复杂环境下完成重大的制度设计与改革。
3、权力新格局
从IANA管理权移交与ICANN问责制度改革之后,ICANN的权力结构与治理模式将有较大的改变。其中,ICANN理事会的权力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与约束,新增的社群的权力将全方位、多层次地监督、审查与制衡理事会的决策;与此同时,由142个国家政府代表组成的政府咨询委员会(GAC)在现行制度下的权力与地位将受到极大的遏制,在现行模式下,该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的共识性建议,如非特殊情况,理事会必须采纳执行,但是改革后理事会即便采纳执行,赋权的社群也可以动用其权力否定理事会的决定,甚至罢免整个理事会。根据建议,ICANN的权力将更加分散,各个部分之间彼此牵扯,构成更加复杂的结构与系统,这将对缺乏经验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政府、企业参与ICANN有关的政策制定与资源分配,构成更大的挑战。
4、美国国内政治
IANA管理权能否最终完成移交,ICANN问责制度改革能否实施,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2014年3月美国商务部宣布移交IANA管理权的意愿之时,ICANN与美国商务部之间关于运行IANA功能的合同将于2015年9月30日到期。因此,美国商务部预计IANA管理权可能在2015年9月30日前完成。但是,此预期落空。2015年8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与ICANN之间的IANA合同延长一年至2016年9月30日。美国商务部官员曾经非正式表态,移交的过渡期可以自2015年9月起延长四年,而且即便ICANN社群有关移交的建议在2016年9月前提交,美国商务部也将非常审慎地评估。
2016年8月16日,美国商务部NTIA的信函一经公布,一时间各种解读纷至沓来,绝大多数人认为IANA管理权移交大功告成、尘埃落定。然而,舆论中心的ICANN却对此“爆炸新闻”保持了意味深长的沉默。一方面,NTIA的官方表态说明,奥巴马政府决计在有限的剩余任期内完成历时冗长、工程浩大、复杂艰难的IANA管理权的移交,给密切关注与参与此事的全球互联网社群一个交代。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笼罩在管理权移交之上的阴影仍旧挥之不去。美国国会曾举行数次听证,审议IANA管理权的移交是否会造成美国国有财产的流失或者国家利益的损害,甚至一度出现制止管理权移交的立法提案。虽然国会至今未采取实质性的手段干预奥巴马政府的行政决定,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国内保守派仍然蠢蠢欲动,寻找各种可能的手段在最后阶段予以阻挠。正在进行、高潮迭起的美国总统大选也给管理权的移交平添变数。由于美国正值总统大选之年,各方政治势力纷纷借此角力,前总统候选人克鲁兹在内的很多议员对于移交表示了强烈反对。一旦IANA管理权移交未能在奥巴马政府的任期内得到批准,总统大选之后,一切将难以预测。NTIA在信中称“克服巨大困难”,实有所指,一言难尽。因此,只要2016年9月30日未至,NTIA、ICANN与全球翘首以待的互联网社群均仍然处于忐忑不安之中,喜大普奔,为时尚早。
不论多少艰难波折,多少妥协无奈,IANA管理权移交与ICANN问责制度的改革已成天下大势,顺应着互联网安全与稳定、开放与互通的潮流,呼应着全球互联网社群“同一个互联网”的梦想,已经不可逆转。互联网治理旧的时代终将结束,新的篇章正在开启。 (责任编辑:李晓晖)
The new era of global governance IANA over control with ICANN accountability system reform
XUE Hong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 made the announcement in March 2014 that the IANA stew ship may be relinquished to the global Internet community through a process convened by ICANN, which has been operating the IANA function. All through two years, the ICANN IANA Stewardship Transition Steering Group (ISG)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proposal. Meanwhile, ICANN cross- community working group worked out the proposal on the reform of ICANN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which is supplementary to the Stewardship Transition. The NTIA confirmed in August 2016 the proposals submitted by ICANN and announce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tewardship relinquishment from October 1, 2016. The Public Technical Identifier (PTI), a new organization operating IANA function under the contract with ICANN, has been established. ICANN’s Bylaws and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have been amended to implement the new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With the coming close of the saga, the new power landscape will emerge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will be changed.
Keywords: ICANN; IANA; Stewardship Relinquishment; Accountability; PTI
作者简介
薛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互联网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1] ICANN 社群由数字地址支持组织(ASO)、国家顶级域名支持组织(ccNSO)、通用顶级域名支持组织(gNSO)、 普通用户咨询委员会(ALAC)、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SSAC)、根服务咨询委员会(RSSAC)与政府咨询委员 会(GAC)组成。
[2] ICANN 的 “Bylaws”确定了其根本使命、地位、权力范围、责任与义务,是最根本性的治理文件。Bylaws 区别于 ICANN 的“章程”(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后者主要是组织机构登记、注册的运行文件。为了显示两者的区别, 突显 ICANN 公共治理方面的地位,本文将“Bylaws”译为“宪章”,特指该文件对于 ICANN 及其社群的约束力。
[3] 2009 年 9 月 30 日, 美国政府和 ICANN 签署了“承诺确认文件” (Affirmation Of Commitments, 简称 AOC) , 声称 ICANN 已经实现完全独立,ICANN 今后将真正实现向互联网社区的所有利益有关方负责;美国商务部重申承 诺支持一个由多方利益有关方参与,私营部门主导,拥有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机制的域名系统技术协调发展模式。 AOC 承诺对 ICANN 组织的问责性和透明度定期审查。审查小组将由社区志愿成员组成,需接受公众发表意见。审 查后产生的报告将提供给 ICANN 董事会和征求公众意见。根据 AOC 的规定,为了确保 ICANN 的责任度和透明度, ICANN 需要设立了四个评审小组:责任度和透明度评审小组、安全与稳定评审小组、竞争与用户保护评审小组、以 及 WHOIS 政策遵守评审小组。ICANN 通过评审不断改进其治理模式与结构。
[4] 为了美国企业能够满足欧盟关于数据与隐私保护的相关指令,使个人信息能够获准从欧盟传输至美国,2000 年 5 月 美国通过了与欧盟互相承认的“避风港原则”。
[5] 美 国 与 欧 盟 经 重 新 谈 判, 于 2016 年 2 月 形 成 了 新 的“ 隐 私 盾 框 架 协 议”(US-EU Privacy Shield Framework Agreement),取代了原来的避风港原则,2016 年 8 月 1 日开始实施。
2016年8月16日,美国商务部电管局(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缩写NTIA)通知互联网名称与地址管理机构(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缩写ICANN),如无重大意外,将考虑让互联网地址分配局(the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缩写为IANA)监管权限的委托合同于2016年10月1日自动过期。[1]如果生效,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将被解读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朝着“国际化”,或者说,摆脱美国政府事实上的单独控制,迈出重要的一步。
截至2016年9月20日,上述转让进程已经进入最后、也是最为艰巨的阶段,即美国国会要批准商务部电管局同意转让监管权限的决定。2016年9月8日,美国参众两院4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商务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要求相关部门在10月1日之前,就监管权限转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由于转移监管权限可能导致威权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地位上升”问题,做出详细回答。[2]
除了美国国内,IANA监管权限的转移,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ICANN治理架构变革,也是利益相关方密切关注的焦点。这个变革的方向,在ICANN官方网站的移交权限专栏,以及美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中,都称其为“私有化”(Privatization);而在另一些场合,其他利益相关方,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代表,则通常会使用“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来描述这一进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私有化”和“国际化”就贯穿在IANA监管权限机制构建的始终,也一直左右着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革前行的方向。
有关ICANN以及IANA监管权限国际化的问题,核心指向支撑互联网乃至全球网络空间正常运行最为关键,可能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资源,包括域名注册、解析、根服务器、根区文件和根区文件系统等。[3]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这一问题的起点,是1997年7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行政备忘录,要求美国商务部推进实现域名解析的私有化,这一私有化必须有助于增强域名解析的竞争性,并有助于推动域名管理的国际参与。[4]
为了回应这一要求,美国商务部电管局在1998年1月30日出台了名为“绿皮书”(Green Paper)的政策立场文件(Statement of Policy)初稿,尝试落实克林顿政府推进域名解析私有化的要求。在此之前的两天,1998年1月28日,在域名解析的技术和早期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导创建IANA的波斯特尔(John Postel)教授,进行了一项理应被关注,但经常被忘记的实验:通过一份电子邮件,他将12台互联网区域根(域名)/辅助根服务器(regional root nameserver)中的8台,指向了一个不同的主根服务器:从原先国际应用科学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缩写为SAIC)下属网络解决方案(缩写为NSI)公司的A根服务器(名称为:A.ROOT-SERVERS.NET,IP地址为:198.41.0.4),指向了IANA自有的根服务器(名称为:DNSROOT.IANA.ORG,IP地址为:198.32.1.98)。在一段比较有限的时间里,当时全球的互联网实际上运行在具有两个“根服务器”构成的域名解析系统里,其中一个根区包含一台主根服务器,八台处于非美国政府部门控制下的辅助根服务器;另一个根区包含一台主根服务器,四台处于美国政府部门(航空航天署,国防部,弹道导弹实验室)控制下的辅助根服务器。用户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影响。从能够接触到的公开材料看,各方倾向于将此描述为一个“实验”,在接到政府官员等各方的系列电话、要求以及命令之后,波斯特尔教授在1998年2月5日前结束了这一“实验”,将整个域名解析系统的根区恢复原状。[5]
“实验”结束之后,同年2月11日,波斯特尔教授与时任互联网架构理事会(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缩写IAB)主席卡朋特(Brian Carpenter)成立了IANA移交建议组(IANA Transition Advisor Group,缩写为ITAG),整个组包含六个小组,成员来自与互联网工程师任务力量(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缩写为IETF)长期保持联系的“圈内人士”:除了卡朋特之外,还有Verio国际公司布什(Randy Bush),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伯(David Farber),澳大利亚域名电信供应公司Telstra的胡斯顿(Geoff Huston),MCI的柯林森(John Klensin)以及思科公司的沃尔夫(Steve Wolff)。[6]
ITAG的成立,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妥协方案:波斯特尔教授停止并修正他的“实验”之后的一周内,美国商务部电管局立刻通过了一个名为“改善互联网名称和地址管理倡议”的文件,其中明确规定了任何对根服务器、根区文件和根区文件系统的修改,必须得到美国商务部电管局的书面许可。对于电管局和波斯特尔教授之间的这一轮互动,比较中性的解读是:波斯特尔教授,作为DNS的“教父”,对绿皮书的私有化方案存在相当不满,因此通过实验方式直接展示了另一种更符合国际化审美标准的解决方案;但这个实验所暗示的内容,即当时的互联网根服务器、根区文件和根区文件系统并不处于美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一封电子邮件就可以指导运营商对此进行重新设定,在美国政府内部造成了巨大的恐慌,美国政府通过改变操作流程的方式,强化了控制。但最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能彻底的闹僵,于是这个工作组的建立,成为帮助波斯特尔教授缓和与美国政府关系,推进以符合波斯特尔教授等人“国际化审美”的方式,来实现对根服务器、根区文件和根区文件系统的管理。
这个最终的妥协方案,就是最终被称为“白皮书”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形成了从199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管理机制:首先是由私营机构牵头,构建一个“美国的非盈利机构”,即现在人们熟悉的ICANN,在ICANN的架构设计中,确保既能够满足波斯特尔教授等需求的国际化因素,又能够确保避免其他国家的政府人员在其中获得决策权,因为相关章程明确规定有政府职务者不能在ICANN理事会中获得具有投票权的职位,同时来自各国政府的代表只能组建政府建议委员会,该委员会不具有决策权;其次是将IANA从一个事实上独立存在的机构,变成一种介于功能和实体机构之间的存在,并确保ICANN必须以招标合同的方式,按照一定期限由ICANN从美国商务部电管局通过招标方式获得;第三是开始在ICANN和根服务器、根区文件和根区文件系统的实际配置之间设置比较明确的区隔,由私营公司实现最终的技术性操作。这方面一个比较重大但同样容易被忽视的变化,发生在1999-2000年间,在此期间,根服务器从NSI公司,通过并购业务的方式,转由威瑞信(Verisign)公司负责;并且修改了主根服务器和辅助根服务器的配置,将原来的“1+12”的结构变成了“1+13”,即取消主根服务器和辅助根服务器的区别,设置一个被称为“隐藏分配主服务器”(hidden distribution master server)的“数据源”,13台公开的根服务器之间不再有主根和辅助根的区别,形成了“隐藏分配主服务器”+公开服务器+镜像服务器的架构。[7]
整体来看,在从“绿皮书”到“白皮书”的发展过程中,“私有化”和“国际化”的主张进行了第一轮较量。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波斯特尔教授主张的“国际化”是一种更具理想主义乌托邦色彩的主张,比现在所说的“国际化”更加理想化;在整个互动过程中,波斯特尔教授真正坚持了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权威主义思潮那里继承下来的精神,以在网络空间追求真正的个体解放、社群主导和公平的国际化为目标,努力避免代表资本力量的大财团,以及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部门,实质性地介入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的管理。这种追求,有着显著的个人色彩,也更加纯粹。
至于美国政府的主张,克林顿签署的私有化备忘录,整体是克林顿政府时期推行政府部门绩效改革大潮的产物,他所要求的国际参与,是用来点缀和修饰私有化的,更准确地说,是要实现如下目标:首先,政府部门要重建对根服务器、根区文件和根区文件系统的有效控制,当然这里说的是美国政府。从波斯特尔教授做的实验,以及实验前后美国商务部的反应可以知道,确实一段时间里,技术社群的实践某种意义上处于比较严格的政府监管范围之外,不受政府监管的技术操作,比如转换一个根区,已经达到美国政府能够忍受之外;其次,私有化是最重要实现的目标,也就是互联网必须为资本增值服务,技术社群活动的整体大方向不能与之违背;第三,面对来自波斯特尔教授这样罕见的实验,其威望、影响和行动能力确实可以阻断美国政府的初衷,采取更加变通和务实的做法,但最终,私有化这个大目标和大方向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冒出来。
最后,需要说一下国际化与私有化进程博弈的某个阶段性标志:1998年10月16日,文中提及的“实验”结束9个月后,波斯特尔教授因为心脏手术的并发症在洛杉矶去世,时年55岁。指出这一点,是为了铭记历史;也有助于人们意识到,真正要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结构的变化,需要怎样的勇气,以及,曾经有人为此做出过何等努力;需要指出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从2014年3月14日美国商务部宣布考虑转让监管权限以来,波斯特尔教授做的实验以及他的逝世,基本没有在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被提到的;2016年9月14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属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这个互动的过程,也被轻易的跳过了,似乎这段历史从没有存在过。
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在全球范围的高速扩展,全球网络空间的形成,及其与现实生活的紧密嵌入与互动,促成了新一轮要求互联网治理国际化的浪潮。这个浪潮的主要源头,是在冷战后迅速涌入全球网络空间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存在巨大需求但实力和能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如此,这一轮国际化的尝试借助联合国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大平台,及其下属的国际电信联盟这个机构,作为推动国际化尝试的大平台。
这种尝试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全球信息社会峰会的召开。在2003年召开的全球信息社会峰会(World Summit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突尼斯会议上首次就互联网是否要治理,如何治理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一讨论的结果,推动联合国秘书长设置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授权此小组研究并提出网络治理的定义;2004年至2005年,此工作组召开了四次会议,最终于2005年6月,互联网治理工作小组提交了工作报告,此报告界定了互联网治理的工作定义:互联网治理就是政府、私营公司和社会,根据各自的角色、共享的原则、规范、规则、决策过程以及程序,来塑造互联网的演化和使用。与此同时,这份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互联网治理的对象:网络治理的对象远远不止网络地址和域名管理,还包括更加重要的内容,包括关键网络资源,互联网安全,确保使用互联网促进发展等。[8]
这份报告同时对当时全球互联网的治理状况进行了评估,然后从六个方向指出了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根区文件和文件系统的管理,事实上处于美国政府单独控制之下。报告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历史因素,即美国政府在推进互联网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因此美国政府是唯一一个在现有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中有权且有能力更改根区文件和系统的主权国家;同时,从技术操作流程看,对根服务器、根区文件和文件系统有操作权限的行为体与美国政府之外的主权行为体缺乏正式的法律管辖关系,换言之,这意味着其他主权国家对这些资源缺乏有效的法律管辖。这个论断,也构成了推进ICANN改革的争议焦点;根据比较经验的归纳来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焦虑,主要的认知变革——行为路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配合美国公共外交,构建美国属于良性霸权的形象,进而认可和接受。比较初步的经验观察显示,在互联网治理结构变革,以及斯诺登披露棱镜系统之后,这种认知变革——行为路径在全球各主要标志性国家和地区,以及关键人群中,均有效发挥了缓释效用。[9]
其二,互联网接入费用,存在显著的不同平分布。报告认为,从实践,距离骨干网越是遥远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也即越是来自落后区域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越是需要支付昂贵的网络接入费用。而在报告撰写时期,对这一接入费用的问题,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是报告从发展角度指出数字鸿沟将如何阻断和影响网络用于发展的最具体的描述。造成这种现象的机制,就是私有化机制。互联网在这种私有化的背景下,被当成纯粹的获取利润的工具,加剧,而非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10]
其三,报告认为,在保持互联网的稳定、安全以及预防网络犯罪方面,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和工具。报告认为无论是考虑到保持互联网接入的稳定和安全,还是有效打击网络跨国犯罪的问题,当时的互联网均未能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11]
其四,就各类行为体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政策制定的问题,报告明确指出,现有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存在显著缺陷,阻碍了弱势方实质性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报告认为,这一缺陷的主要表现,是缺乏透明度、公开性和可参与的进程;政府间组织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受到限制,对发展中国家、个人、社会组织和中小企业来说进入门槛过高;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会议举办集中在发达国家;缺乏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的参与机制。从已经有的实践看,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以及所谓技术社群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等,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排斥普通人,即不是熟练的技术人员,不能熟练识别那些专业缩略用语的行为体,实质性地进入并在决策过程中有效地输出意见。在具有决策权力的关键岗位的选举机制上,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下实质运行的更像是常见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兄弟会”架构,海量的基础参与者,与少数依托人际关系和信任组织起来的圈内精英人士,共同组成这个架构。基础参与者负责提供形式和程序上的合法性,精英则实质性地垄断决策过程。
不过整体来看,尽管WSIS的报告曾经正确地指出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化的目标与方向,面临的弊病,但最终凭借技术、产业方面的硬实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以及制度创建与议程主导能力的优势,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有效地抵制并迟滞了要求ICANN国际化的进程。美国实践的方式,在最为极端的情况下,可以包括否决ICANN的招标资格。[12]
2014年3月,在棱镜系统曝光之后明显感受到巨大压力的美国政府,宣布将放弃对互联网数字分配当局(IANA)的监管权限,尽快把它移交给一个遵循“多边利益相关方”组建的私营机构。移交进展才开始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这份声明中,IANA也表示这次转让实则是在履行1998年成立ICANN时商务部发表的《政策申明》中的承诺——确保私营机构(privatesector)在域名管理中处于领导地位。因此,美国政府在确认转让这一方案的同时,通过申明四大原则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新的方案,这四条原则对理解IANA的转让方案有着重要作用:
第一个原则是支持和促进“多利益相关方”模式。通常来说,“多利益相关方”(Multistake-holder)模式是相对于“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而言,“‘多利益相关方’为欧美发达国家所偏好”,包括各种形式的国家,公司,非政府组织及个人;“‘多边主义’则被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喜爱”,主张“主权平等”的主权国家为中心对全球网络空间实行共同管理。美国主张将ICANN管理权移交给“多利益相关方”,而极力反对“让一个由政府主导的(government-led)或政府间(inter-government)组织来接管”,其理由是“比起政府主导的或政府间组织,私营机构能够更多地创新和发展出解决问题的技术,从而促进互联网发展”,政府应该仅作为利益相关方中的一方,通过ICANN下属的政府建议委员会(GAC)或以个体的身份参与到管理中来。
第二个原则是维持全球网络域名系统(DNS)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弹性。IANA通过这一原则试图说明,原有的DNS集中分配式的结构应该被保留,新的管理机构也应该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继续实行责任制。而为了维护全球网络系统的稳定,ICANN和威瑞信公司(Verisign)共同管辖的根服务器也应该保持原有状态。
第三个原则是满足全球IANA客户的需要和期望。也就是说,ICANN管理权的转移及其有关的政策发展应该和它的日常运营活动区分开,以保证客户的需求不会因为其内部政策变化而受影响。
第四个原则是维持全球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在IANA看来,保持全球市场的开放实际上就是维持ICANN管理部门的中立和自由裁决,契合了其倡导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四大原则伴随着IANA的移交方案应运而生,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对ICANN的移交始终围绕着强化“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看似放弃管理权的方式实际上是“以退为进”,继续维持强化这一模式,意味着美国仍然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公司,个人,社会团体等优势通过“利益相关方”的方式参与到ICANN管理之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没有在IANA的移交方案中看到任何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管理全球网络空间的可能,也无法改善在关键资源控制上所处的不利地位。
在这个移交进程中,有关治理原则之争,主要体现在如何认识和理解“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争议中:所谓多边利益相关方,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推进互联网商业化进程中采取的一种运作模式,将公司、个人、非政府组织以及主权国家都纳入其中,最高决策权归属于由少数专业人士组成的指导委员会(BoardofDirectors),相关的公司、个人、非政府组织在下属的比较松散的区域或者专业问题委员会开展工作,政策制定采取所谓“自下而上”的模式,有下级支撑委员会向指导委员会提出建议和草案,然后指导委员会加以通过;其他主权国家的代表则被纳入政府建议委员会(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只具有对和公共政策以及国际法等相关的活动或者事项的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其建议也不具有强制力。[13]
纵观整体发展,可以说,发端于2014年的IANA监管权限移交进程,新监管权限本质上是一个“私有化”方案,而非“国际化”方案。最终移交效果从三个方面被纳入美国预期的轨道:
其一,坚决杜绝任何主权国家进入的可能,为此不惜动用美国的否决权,即保留对所有移交方案以及ICANN章程最终修订版本的最后审核权;其二,主动用私有化方案作为移交方案的基础,将移交方案讨论的焦点,从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对根服务器、根区文件系统的国际化管辖,转移成为对ICANN工作流程透明度和有限监督的讨论,通过这种讨论,实现对ICANN理事会的弱化、虚化,用社区授权机制和授权委员会实质性削弱乃至架空理事会,同时有针对性地继续削弱本来就不强势的政府建议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其三,在人事关系方面,强化ICANN决策层的兄弟会属性,严厉打击ICANN高层改善与美国之外国家,尤其是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举动。美国国会,以科鲁兹参议员为首,组建专门的国会连线,对ICANN高层任何被视为靠拢中国的举动,通过媒体进行严厉质问,通过ICANN社群进行直接施压,确保中国能够被严格地排除在相关变革进程之外。
美国能否如期完成ICANN的转让,一个关键点就是它所提出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能否得到落实。由美国官方对已有的移交方案反应来看,凡是提案中有涉及“由主权国家或政府间组织来接管”的内容,美国政府一律表示了否决态度,并广泛向世界多利益相关方征集议案。发展中国家的“多边主义”原则虽然注重对主权的尊重,但是,受到具体能力的制约,对“多利益相关方”原则的冲击和挑战,还很难落到实处。而发展中国家在网络空间管理中面临的不利局面,最主要的是在技术等硬实力上的不足,美国在互联网芯片,操作系统,关键基础设施的绝对垄断优势,决定了其在网络空间的绝对话语权。因此,ICANN的转让仍然会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进行,IANA只接受来自利益相关方委员会的方案,并且只有当方案满足了其提出的要求时才会接受,这也就进一步模糊了其转让的时间。
从最积极的视角看,无论如何,只要美国国会没有实质性的否定移交方案,整个ICANN的国际化,就将取得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进展。这一进展的意义在于,尽管ICANN还是处于美国加州公司法的管辖之下,但美国政府如果真的要启动或者说使用对ICANN的管辖,很难轻易通过美国行政机构内部的流程完成相关工作,管制效率会呈现显著下降;更直白地说,完成这一私有化进程的ICANN,将在一定意义上进入一个“各显神通”的竞争状态,未来发展的方向将因此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当然,美国政府是不会松口说这一私有化的进程会削弱美国的实际利益,或者对全球网络空间的管控。一如在2016年9月的听证会上,积极推进如期移交监管权限的美方官员是用这样的逻辑来说服组织听证的国会议员的:按期移交,将提升美国的声望,有助于推行和实现美国倡导的基本价值,即互联网自由。如果对美国的内政与外交比较熟悉的话,可以发现,这个说服逻辑,和20世纪90年代白宫游说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贸易议案,包括同意中国加入WTO等,都曾使用过。至于效果,见仁见智。
从全球网络空间的发展和演变来看,美国在其中逐渐失去曾经有过的绝对优势,并使得全球网络治理结构慢慢走向国际化,是一个毕竟东流去的进程,包括中国在内,可以从长期和战略层面,维持谨慎的乐观。当然,在具体细节上,如果真的希望实质性地推进ICANN国际化,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地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化,应该还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
1、全面改变资源分布和能力分配的不对称性,是推进未来ICANN以及更加重要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真正实现国际化的关键。尽管存在很多理论分析和政策术语,但本质上全球网络空间的治理结构是由客观的实力以及资源的分配所决定的。意图,构想,规划或者设计,只有在与之相互匹配的实力的支撑下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导致此次IANA监管权限转移事实上被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关键,就是资源和能力的不对称分布。这种不对称分布,包括技术和产业领域的不对称分布,包括支撑全球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的不对称分布,包括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组织结构的关键节点上的不对称分布。
2、明确国际化和私有化的实质性区别,进而设立推进国际化应努力争取的方向和目标。ICANN的国际化进程,IANA的监管权限,是讨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化进程中最具象征意义,也最容易得到媒体聚焦和关注的问题。“私有化”和“国际化”的区别是直接而清晰的:其一,“私有化”的主导力量是私营部门,尽管遵循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但最终整个主题的定性仍然是私营部门;而字面意义上的“国际化”则要通过正式的程序让其他主权国家能够对决策过程有实质性的影响;其二,“私有化”与“国际化”在司法管辖权上存在本质的差别,“私有化”方案形成之后,坐落于美国领土边界内的“私有化”实体仍然将接受美国的司法管辖,“国际化”方案如果真的通过,将让新的行使IANA权限的机构变成类似联合国框架下的各种组织,即使地理位置处于美国领土边界之内,但却不能依托美国国内法对其实施司法管辖;其三,从主导力量看,“私有化”方案最后形成的实际运作流程,必然是与资本密切结合,或者说能够得到资本支持的技术精英在“自下而上”“社群决策”的外壳下,实质性主导这个进程;“国际化”方案最终是要让主权国家,尤其是技术、产业、资本、治理等实体能力相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依托主权平等提供的法权基础,在全球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的治理上占据更多的发言权,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相对弱势的群体总是更容易占据数量上的优势。
3、提出具有吸引力,符合各方合理利益需求的解决方案,并着手启动相应的进程,实质性地推进。ICANN的国际化进程,在相当程度上有些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直到中国推出并成功实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以前,相关的改革进程进展缓慢。在通过展示补充性的,但又相对独立的新解决方案之后,有关强势方才会有更大的动力来做一些实质性的变革。美国主导这一轮ICANN国际化改革,是在缺少真正有影响的替代性解决方案的大环境下进行的。
巴西曾经提出过温和改进方案,即所谓的Netmundial方案。该方案于2014年4月圣保罗会议上出台,其核心要义是试图对ICANN架构做出温和的调整,要求有限度地提升ICANN内政府建议委员会(GAC)的立场;将ICANN制定网络治理政策的职能,和直接管理并配置根服务器权限的职能分离;明确局限要管辖的根服务器是由Verisign公司和ICANN管辖的三台顶级根服务器,不触及对其他处于美国政府部门、高校管辖下的根服务器。这个方案体现了巴西等国家的利益偏好,他们并没有多大雄心塑造一个全新的网络空间新秩序,而是希望通过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有限改革,换取美国政府极其有限的让步,即确认ICANN对其所管辖的数量有限的服务器的独立管辖。这种让步的本质,就是希望占据实力优势的国家能够自我约束。
印度则出台过比巴西方案更加激进的调整构想,其核心要求是试图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主要职能转交给国际电信联盟(ITU)。为了实现这一策略,他们首先是在2014年国际电信联盟的釜山会议上尝试将有关关键技术和权限交给电信联盟,为此不惜令釜山会议面临流产的险境;同时,印度关于重组全球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的建议也是颠覆性的,它提出应该参考现有的国际长途电话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各国将数据资源置于本国境内,然后通过类似拨打国际长途电话的方式,在访问相关网络资源时,使用统一分配的国别网络识别码,再进行接入。由于构想过于惊世骇俗,在提交大会讨论时又存在程序瑕疵,印度这个方案至少在釜山会议当场就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美方明确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抵制印度的方案。釜山会议之后,有美国研究者在不同场合都提到,“因为印度在釜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所以印度已经失去了继续推进网络空间新秩序建立所必须的声望”。
对中国而言,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是构建更多建设性、参与性的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性参与。同时,在参与和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国需要在观念和能力上进行有效的调适和建设:一方面是要形成从中国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出发,构建中国方案。这个方面工作的重点是要勇于和善于讨论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是要提升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战略决策能力,这个方面工作的起点可能是国内网络治理领域的战略创新。从实践看,要在全球网络空间技术社群提升中国的地位,就必须提升能够进入这个社群的中方技术精英的国家认同感;实现有效创新的目的,是确保在这些社群,有能够代表中国利益的有效意见输入,而不是相反。(责任编辑:钟宇欢)
Direction disput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change of ICANN : internationalization, or privatization?
SHEN Yi
Abstract: The result of IANA regulatory authority transfer process will be announced on September 30, 2016. It will be the most symbolic event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change of ICANN and the global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ization or privatization is the main issu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hange. It’s inevitable when capital and political power spread to cyberspa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riefly sort out the relevant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basic implementation and policy practice.
Key words: cyberspac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ivatization
作者简介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Lawrence E. Strickling,“Update on the IANA Transition”, http://www.ntia.doc.gov/blog/2016/update-iana-transition,(2016 年 9 月 10 日)
[2] 来源:https://www.judiciary.senate.gov/imo/media/doc/2016-09-08%20CEG,%20Senate%20Commerce,%20House%20Judicairy,%20House%20E&C%20to%20DOJ,%20DOC%20-%20IANA%20Transfer.pdf (2016 年 9 月 10 日)
[3] 相 关 参 考 和 说 明 资 料, 参 见 RFC 2870 – Root Name Server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RFC 2826 – IAB Technical Comment on the Unique DNS Root。
[4] 参 见:The White House, “Memorandum for the Heads of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July 1, 1997), http://clinton4.nara.gov/WH/New/Commerce/directive.html(2016 年 9 月 10 日)
[5] 根 据 相 关 资 料 整 理, 主 要 来 源:Klein, Hans. "ICANN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Leveraging technical coordination to
realize global public polic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8.3 (2002): 193-207;Mueller, Milton. Ruling the root: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taming of cyberspace. MIT press, 2002.
[6] Mueller, Milton. Ruling the root: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taming of cyberspace. MIT press, 2002.
[7] 参 见:https://www.ripe.net/participate/meetings/roundtable/march-2005/presentations/the-root-name-server-system-operation-of- the-k-root-server,(2016 年 9 月 10 日)
[8]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9]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10]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11]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12] Notice - Cancelled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 Functions - Request for Proposal (RFP) SA1301-12-RP-IANA, 来 源:http://www.ntia.doc.gov/other-publication/2012/notice-internet-assigned-numbers-authority-iana-functions-request-proposal-rf,(2016 年 9 月 10 日)
[13] Kruger, L. G. (2013).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Domain Name System: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和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上个世纪中期以来,飞速发展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和冲击,许多专家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第一次系统地对信息和传播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进行评估和讨论,则始于2003年和2005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orld Summit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WSIS)。这两次峰会分别在日内瓦和突尼斯召开,主要由世界各国的政府代表团参加。由于信息社会所牵涉的议题广泛,同时也邀请了相关的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私营企业参加,从而缔造了一个典型的“多方利益相关者”(Multi-stakeholder)参与的进程和论坛。以日内瓦峰会为例,来自175个国家的4,590位政府代表,3,310位非政府机构的代表和514位企业界人士,总计一万多人参加了会议。[1]由于这次日内瓦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后续的二段突尼斯峰会总参与人数达到了19,401人,政府代表5,857多人,非政府代表6,241人,以及大幅度增加的企业代表4,816人。[2]
表1:2003年 年日内瓦峰会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

正是由于广泛的参与,这两届峰会就信息社会的走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达成了深远的共识,提交了四个纲领性文件:1、《日内瓦原则宣言》;2、《日内瓦行动计划》;3、《突尼斯承诺》;4、《突尼斯信息社会议程》。
2003年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明确提出国际社会“以人为本,包容全纳,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愿景,在此信息社会中,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使个人、社区和各国人民均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3]这就是峰会达成的全球信息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也设定了信息社会的宏大目标,具体如何践行呢?《日内瓦行动计划》进一步概括了各国在截止2015年建设信息社会的11个方向和专业领域:[4]
1.各国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在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即政府和公众以及企业应当建立伙伴关系,有效参与信息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也就是建立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制。
2.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即各国在信息科技战略方面要首先提供硬件设施和网络连接,尤其是在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3.获取信息和知识:即个人,组织和社区都可以利用通信网络获取信息和知识,使得信息和知识通过新兴传播技术实现广泛分享。
4.能力建设:即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公众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技巧,包括专业人员,女性和儿童。
5.树立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即在国际和国内范围提高信息技术和数据信息的安全性。
6.环境建设:主要指建立配套的法律监管和政策环境。
7.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即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在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电子商务、电子学习、电子卫生、电子就业、电子环境、电子农业、电子科学等。
8.文化多样性与特征,语言多样性与本地内容:即通过信息技术来保护和促进文化语言和内容的多样性,包括通过传统和数字媒体服务,提供与信息社会中个人的文化和语言相适应的内容。
9.媒体:即在传统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媒体例如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新型媒体应当在信息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独立,自由和多样化的媒体在建设信息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鼓励南北国家之间的媒体合作和交流,优化信息技术的媒体功能,鼓励媒体发挥弥合知识鸿沟和文化多传播的内容。
10.信息社会的道德内涵:即弘扬信息社会应遵从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推进公共利益,防止滥用信息通信技术。
11.国际和区域性合作:即通过国际和区域合作进一步促进普遍接入和弥合数字鸿沟。《突尼斯承诺》[5]强调了弥合数字鸿沟的社会性挑战,即在促进各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弥合数字鸿沟要以人为本,包括使得残疾人、妇女、儿童、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原住民等都能够从信息社会受益,而在国际范围内,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期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其它处于困难时期的国家的特殊需要。针对作为社会数字鸿沟一部分的性别鸿沟,主张鼓励妇女参与信息社会和决策过程。
表2:过去十届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的举办国以及大会议题一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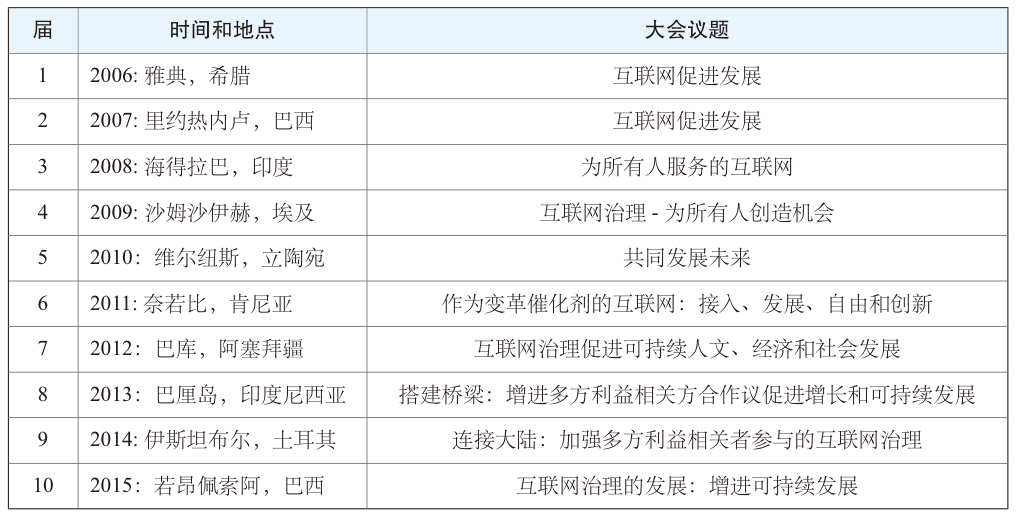
鉴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普及,2005年的《突尼斯议程》[6]最重要的贡献是设置了全球互联网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的议程。该文件明确指出“互联网已发展成为面向公众的全球性设施,其治理应成为信息社会日程的核心议题”。《突尼斯议程》前瞻性地提出:“互联网的国际管理必须是多边的、透明和民主的,并有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的充分参与。它应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促进普遍接入,并保证互联网的稳定和安全运行,同时考虑到语言的多样性”。[7]这段话列出了多方利益相关者(Multi-stakeholder)的主体: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在过去十年里,随着社会各界更广泛地参与互联网治理,参与者的范围也在扩大,国际社会逐渐认可了一些新的利益相关者,比如2014年巴西召开的全球互联网大会(Netmundial)就在成果文件里正式确认了“技术团体”(technical community)“学术团体”(academic community)以及网络用户个人(users),[8]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互联网治理的成果文件[9]里,还确认了新闻媒体(news media)作为互联网治理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
关于互联网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2005年的时候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突尼斯议程》的第34段给出了工作定义:“由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基于各自领域,共同制定和采纳可以共享的原则、规范、规则、决策程序和项目,从而指导和引领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方向”。[10]《突尼斯议程》的第35段强调互联网的治理包含技术和公共政策两个方面的问题,而且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相关政府间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电信联盟ITU等)的参与。与此对应的还有更加具体的举措:《突尼斯议程》的第72段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一个开放而包容的进程中于2006年召集一次有关利益相关方政策对话的新论坛,该论坛被称为互联网治理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IGF),以讨论互联网治理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2006年,第一届互联网治理论坛在希腊的雅典召开,由此开启了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序幕。这是一个鼓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开放式国际论坛,所有人只要在网上注册就可以参加论坛。该论坛为期一周,2000多名政府、私营企业、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代表自主组织和参与两百场左右的分会场,工作坊以及圆桌会议,议题涉及网络接入,开放性,网络安全和多样性四大领域。在过去十年中,互联网治理论坛便在各国政府的接力主办下声誉日隆,议题和参与者也经历了很大演变,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最有代表性的旗舰式论坛。过去十年中,该论坛逐年在不同的大洲和不同的国家举办,[11]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会者,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政策讨论最权威的论坛。2016年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将于12月在墨西哥举行。[12]
以2015年在巴西举行的第10届互联网治理论坛为例,由于恰逢信息社会峰会的十年审查进程以及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主题聚焦于互联网治理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而事实上在过去10年中,“发展”是几乎每届论坛主题的关键词,这充分体现了互联网治理论坛对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以人为本,包容全纳,和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理念的贯彻。在2015年巴西大会上,共有来自116个国家的2000多名注册参会者,以及上千人通过网络远程参与论坛讨论。为期四天的会议,总计超过150个分会和工作坊,讨论了包括网络安全和信任、互联网经济、包容全纳和多样性、开放、加强多利益相关方合作、互联网和人权、关键的互联网资源以及新近话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本着透明和分享的原则,这十次论坛的大会议程和会议纪要,逐场文字实录都如实地保存在联合国经社部互联网治理论坛秘书处维护的互联网治理论坛网站[13]上,成为普遍接入和分享的公共信息资源,为世界范围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最近有一个自发性的活动叫“互联网治理论坛之友”,通过更加先进的数据管理和搜索技术,建立了一个十分用户友好的网页,[14]方便读者从理解使用关键字来查询互联网治理论坛的网站内容。
日内瓦和突尼斯峰会之后,日内瓦行动方案的11条发展方向和专业领域主要由联合国系统几大国际机构牵头协调和执行: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联合国发展基金(UNDP),总协调机构是位于UN总部直接向联合国大会(UNGA)报告的经社理事会(ECOSOC)及其授权的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CSTD)。在过去十年中,国际电信联盟在其他机构的合作下,每年在日内瓦举行世界信息社会峰会论坛(WSIS Forum),旨在跟踪和讨论日内瓦行动计划的贯彻执行情况。
2015年12月份,联合国第70次大会审批和通过了《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15]标志着峰会后续执行的第一个十年告一段落,同时展望了2015后致力于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16]的信息社会战略。《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充分认可了过去十年信息传播技术在连通性、使用、创造和创新方面实现的显著增长,这些技术成为消除贫困和改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新工具。该文件特别引用了许多具体数据来说明这一点:全球移动电话用户数目已从2005年的22亿增加到2015年的71亿;到2015年底,有32亿人上网,超过世界总人口的43%,其中20亿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固定宽带用户普及率已近10%,2005年为3.4%;移动宽带仍然是增长最快的市场部门,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在2015年达到47%,自2007年以来增加11倍。
日内瓦峰会确立的“以人为本,包容全纳,和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的愿景在过去十年来持续激励全球范围内的后续行动,而这一愿景正在逐渐地变成现实:从2005到2015十年间,信息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迅速增加,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经济论坛都有报告和数据证明这一点。
下面图表来自国际电信联盟2013年发布的全球报告,自2003这10年来最为显著的发展就是全球手机用户的剧增,从20%多增加到96.2%,几乎实现了全球范围的全面普及,成为最为广泛的信息接入方式。其次就是全球互联网接入率从不到20%增加到41.3%,与此同时移动宽带的接入近年来高速增长到29.5%,直追固定电缆网络接入的38.8%。而唯一出现下降趋势的就是传统固定电话的用户,已经逐渐减至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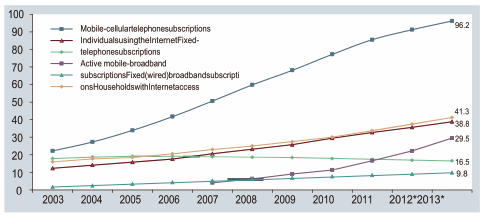
图1:全球信息传播技术接入的发展,2003-2013[17]
本着日内瓦信息社会峰会“以人为本,包容全纳,和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的精神,信息传播技术的物理接入鸿沟的弥合并不意味着数字鸿沟的全面克服。《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关切数字鸿沟的社会层面挑战,例如互联网使用的社会鸿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以及男女之间的数字鸿沟仍然存在,为此须采取进一步行动,并加强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国际合作,以改善互联网接入的可负担性、互联网用于获取工作和教育机会、促进能力发展、互联网上多种语言的内容生产、通过互联网促进多元文化保护、促进互联网方面的投资和适当筹资,等等。从下图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的一大挑战,互联网使用的性别鸿沟,相比发达国家男女网民几乎持平的情况,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网民比男性网民低16%。因此在未来要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信息社会并有机会获得新技术,特别是促进发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确保妇女在相关领域的权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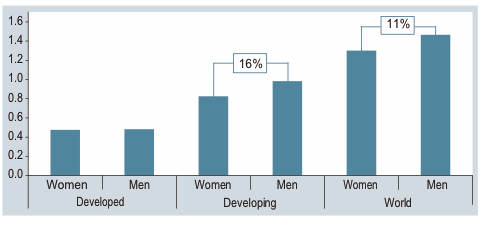
图2:互联网使用方面的性别鸿沟:2013 [18]
为综合测量信息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国际电信联盟于2009年开发了信息技术发展指数(ICT Development Index,IDI),该指数由信息技术接入指标(包括电话,手机,电脑和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数)、使用指标(互联网用户、宽带用户和移动宽带的比例)和技能指标(指平均识字率、高中入学率和大学入学率)组成,用来测量不同国家信息技术接入、使用和所掌握的技能的水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指标上有显著差异,以2013年为例,发达国家的IDI指数为7.25,而发展中国家为4.88。[19]基于此,国际电信联盟2014年发布的报告作了一个信息技术发展指数和人均国民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从结果来看,两者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r=0.78),图中信息技术发展指数较高的国家所对应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欧洲,北美和亚太较发达国家。该报告还指出,在那些信息技术指数领先的国家,信息技术市场的自由度和竞争性更强,更多创新,而且人们使用信息技术的技能更好。[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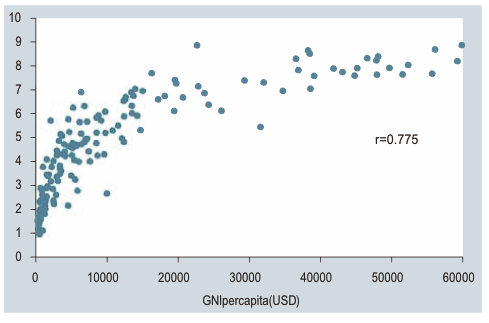
图3:信息技术发展指数(IDI)与人均国民收入[21](GNI)的相关性分析2013
正基于此,《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中一个重要和日益增长的组成部分,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相互关联,扩大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中的参与至关重要。而且,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包容程度,为公民、企业和政府提供了新的渠道,使其能够分享和增进知识并参与影响其生活和工作的决策。藉助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教育、保健和就业以及在商业、农业和科学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过去可能难以企及或负担不起的服务和数据。
为了更加全面衡量不同国家和社会信息技术发展的完备程度及其对社会和经济的促进程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研发了网络完备度(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NRI)的综合指数,综合考量了四大分支指标:1、政策法规和企业创新环境2、基础设施,数字内容,可负担的价格和技能3、个人使用、企业使用和政府使用水平4;经济和社会影响水平。[22]该指数的统计结合了定量和定性的数据,并广泛采纳了国际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可靠数据。从2014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图表4),网络完备程度最高的前十国家主要是北欧、北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其网络完备指数在5.4-7.0之间,中国的网络完备指数为4.05,居世界第62位。
该指数意在说明一个国家的信息技术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福祉,该报告还分析了一些代表性国家网络完备指数的成因:[23]以连续2013-2014两年网络完备指数居首的芬兰为例,芬兰拥有出色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90%的人口上网,技术和非技术创新水平高,加之芬兰自1990年中期以来将建设信息技术生态系统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而且所有利益相关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等)都积极参加了这个过程,因此总体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新加坡的信息完备指数连续两年位居第二,成功原因在于其十分有利于企业和创新的政策法规环境,政府制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数字战略,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在线服务,其城市规模也有利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提高,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质量。中国尽管从整体规模上是一个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大国,但网络完备指数偏低,主要因为中国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潜能方面相对滞后,虽然专利申请数目有所增长,但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世界第32位):每100万人口只有11.5个专利申请。虽然中国的个人上网率增加很快,但只有40%的网民比较常用互联网,而且固定宽带接入率只有13%(世界第51位),移动宽带接入为17%(世界76位)。因此同企业(44位)和政府(38位)相比,中国的个人互联网使用程度相对较低(80位)。中国有人口规模的限制,政策和税收环境也需要朝着更有利于信息技术采用和企业发展方向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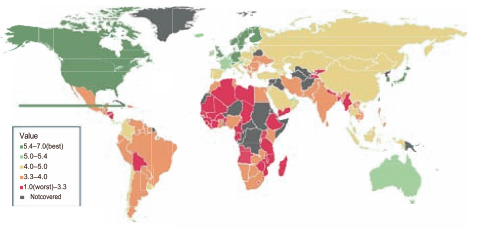
图4:网络完备指数(NIR2014)[24]
总的来说,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撰写的《信息峰会十年回顾报告》[25]的评价:“信息科技网络和服务能力比十年前增畅了30倍,万维网由于社交媒体和其他用户生产内容平台的出现变成一个更加交互的平台,而新兴的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社交媒体分析等,都在催生新兴的企业和政府运作形式,增进人民对社会和经济趋势的预测,并为促进发展的新举措开辟新道路。然而,在2005年人们讨论《突尼斯议程》时,固定和无线宽带、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云计算、开放数据、社交媒体和大数据都还没有进入视野,但现在已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进工具。这也体现了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之快和不可控制的特点,正因如此,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信息技术的潜力,如何将信息技术融入社会和经济发展,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改善政府、企业、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事业,如何制定和更新相应的政策法规框架,如何赋能每一个公民和个人通过信息技术获益,都将持续挑战2015年后的每一个国家和社会。
为应对这些挑战,《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再次强调了多利益相关方合作和参与的价值和原则,这种合作和参与是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进程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特征,确认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国际组织、技术和学术界以及所有其他相关利益相关方的各自作用和责任范围内的有效参与、伙伴关系和合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均衡代表性的前提下,对于建设信息社会仍然至关重要。
已经举办十届的全球互联网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缔造和实践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讨论的最佳典范,也是信息社会峰会后续的显著成就之一。而这种参与模式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复制和铺开。除每年一度的全球互联网论坛,每年世界上所有地区和许多国家还举办总计超过70个以上的地区性和国家范围的互联网治理论坛,而且还开创了诸如“动态联盟”(dynamic coalition),“最佳实践分享论坛”(Best Practice Forums, BPFs),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关领域的参考文件和资源,比如如何规范和消除不良通讯,如何建立计算机安全事件反应团队(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s,CSIRTs),如何建立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制,如何应对网络欺凌和针对女性的网络暴力,如何就IPV6和IXPs制定政策等等。
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一个制度性创新是于2011年创建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咨询组”(Multi-stakeholder Advisory Group-MAG[26]),这是一个由联合国秘书长直接任命的专家组,为秘书长就互联网治理论坛的组织和日程给予建议,一般由55位来自政府、私营企业、公民团体、学术和技术团体的专家组成,由各团体自主推荐人选,除政府代表由各国政府指定外,其他成员每年轮换大约30%。也就是说,每位MAG成员的最长任期是3年。中国互联网协会于2013年首次成功推荐了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专家进入到MAG专家组参与互联网治理论坛的管理和组织工作。[27]MAG专家组不仅讨论确定每年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主题,而且直接评估并批准每年来自全球各方的200多个工作坊提议,因此对整个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成功举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他们代表多方利益和观点的兼容并包性则从制度上保证了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代表性。
因此,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不再只是一个年度论坛,而是成为一个庞大的全球性生态系统,[28]在这个生态系统里,各方人们就他们关心的互联网使用和政策问题在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进行广泛和无微不至的参与和交流,从而影响和催生互联网政策和实践的结构性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治理论坛中的代表性持续增加,从最早的发达国家为主到目前基本持平。以2016年底即将举行的第11届论坛为例,大会一共收到超过270个工作坊的提议(最终由MAG专家组筛选出100个左右给予举办),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提议数量是54%,发展中国家的提议数占46%。
互联网治理论坛也广泛采纳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设置的议题,在即将举办的11届大会,来自公民团体的提议占了二分之一强,其次是技术团体,来自私营企业和政府的提议分别占10%和6%,MAG专家组认为应该鼓励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更加积极的参与论坛议题的建议,以进一步提高论坛政策讨论的代表性和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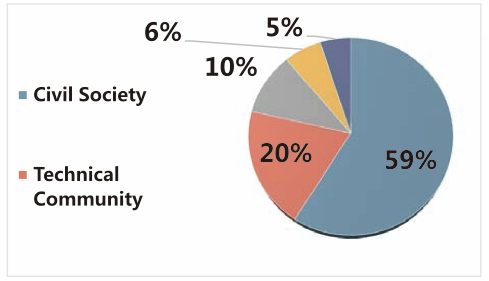
图5:2016互联网治理论坛工作坊提议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比例
在过去十年的论坛进程中,有关互联网治理的议题也逐步确立了各方共同关注的核心领域,而每个领域的具体议题则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以应对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新挑战。总的来说,正如《突尼斯议程》定义的那样,互联网治理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从第一届雅典开始基本确立了内涵十分丰富的五大议题领域:
第一大议题领域:互联网的开放性(Openness)。开放性,被认为是互联网最重要和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互联网为亿万网民提供了无远弗界的实时动态交流平台。互联网治理论坛所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维护这种开放性,不因种种政策和技术更新而受到不利的限制,也不因国家和用户的贫富而在获取信息方面受到影响,从而使得互联网的开放性服务于社会发展和推进公民线上的表达自由和信息接入权利。
第二大议题领域: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网络安全既指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安全,这需要国家、国际组织、私营企业以及技术团体的通力合作,同时也包括网民个人的隐私权不受侵犯以及用户免予受到网络病毒、垃圾邮件以及其他形式的网络攻击。网络安全的问题在“斯诺登泄密”事件后急剧升温,国家如何合法合理的进行互联网监控,国家安全措施如何不以妨害网民隐私权和其它基本权利为代价,等成为互联网治理论坛上持续讨论的热点问题。
第三大议题领域:互联网的多样性(Diversity)。互联网多样性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多样化(Multi-lingualism),互联网作为全球性的公共舆论和信息交换平台,应该承载丰富多样的语言内容,各国应该鼓励和推动网民使用本地语言上网,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29](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推行的国际化互联网域名(International Domain Name)到政府和企业采取措施促进多语言接入互联网和本地内容的生产,都有利于促进互联网的语言多样化以及文化多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03年通过了《关于普及网络空间及提倡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30],就“开发多种语言的内容和系统”、“推动网络和服务的使用”、“开发公共领域的内容”和“重申公平兼顾权利拥有者与公众双方的利益”四个方面给予了政策建议。
第四大议题领域:互联网接入(Access)。2005年,全球有10亿网民,2010年增加到20亿,2014年增加到30亿。[31]如何让下一个10亿人上网,是互联网治理论坛的经典话题。政府在国家层面营造适当的政策环境,促进电子商务,扩大宽带覆盖面,鼓励互联网服务商的竞争以便降低价格,对于互联网的普及起关键作用。
第五大议题领域:关键的互联网资源(Critical Internet Resources)。这个议题涵盖互联网物理和逻辑基础设施的一系列问题:互联网域名domain name system (DNS)和Internet protocols地址的管理问题,根服务器的管理,网络标准制定,互联节点(interconnection points),电信基础设施,涉及许多国际机构、技术团体,如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全球互联网技术规范的研发和制定)、W3C(万维网联盟,国际中立性技术标准机构)、ISOC(国际互联网协会,负责制定互联网相关标准及推广应用为目的)等。而位于美国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作为域名体系和根服务器等诸多关键互联网资源的管理者,成为讨论的焦点,许多人担心该机构由于其同美国商务部的合同关系,会使得属于世界的互联网的关键资源受到美国政府的控制。经过许多届论坛的争议(论坛似乎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应该是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美国商务部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于2014年3月14日做出了一个历史性决定,即宣布将互联网关键职能IANA(ICANN中管理域名、互联网协议地址、相关数字标识符和协议参数的顶级注册管理机构)的管理权移交给全球互联网多方利益相关社群,而这一移交进程仍在进行之中,并持续在互联网治理论坛上进行讨论。
在最近几次互联网治理论坛上,由于“斯诺登泄密”事件的持续影响,公民的隐私权利和线上表达自由权利成为热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因此于2012年通过了《促进、保护和享受互联网上的人权》[32]决议,联合国大会于2014通过了《数字时代的隐私权》决议,[33]决议强调,按照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各国义务,任何人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均不得受到任意或非法干涉。该决议促请所有国家审查其有关通信监控的程序、做法和立法,及其截获和收集个人数据,包括大规模监控的做法,以期通过确保充分和有效执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所有义务,维护载于《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公约缔约国)的隐私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5年任命了第一位隐私权的特别报告员,[34]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于当前网络隐私权的重视驻日提高,许多国家把隐私权方面的立法保护和更新提上日程。
在过去十年中,受互联网治理论坛启发,催生了一系列全球性互联网政策论坛和机构,例如智囊机构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非洲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的“非洲互联网权利和自由运动”(African Declaration on Internet Rights and Free dominitiative ),巴西政府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2014年联合举办了世界互联网大会(“NETMUNDIAL”),一千多名世界各地的代表起草并通过了世界互联网[35]多方利益相关方文件,里面设定了有关互联网治理的基本原则和路线图,在互联网政策界成为广为引用的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3月份举办了“点点相连”互联网多方利益相关者大会,其195个成员国在2015年底的38届大会上通过了“点点相连”大会的成果文件和“互联网普遍性”(Internet Universality)的概念框架,为该组织在互联网接入、言论自由、隐私和网络伦理四个领域确定了未来发展方向,并提出了38项行动建议。
在2016年论坛的工作坊提议中,下列图表统计了各方所关注的议题分布,最受关注的议题集中互联网上的权利问题(包括隐私权、自由表达权、性别平等、儿童保护等)和互联网的接入和发展问题(包括网络接入、互联网经济、网络安全、网络素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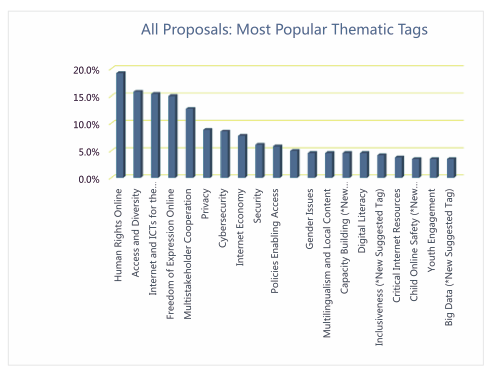
图6:2016年互联网治理论坛的议题比例[36]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十年历程显示,信息技术不但带来经济繁荣,而且促进社会进步。《信息社会峰会成果文件》制定的愿景是: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兼容并包和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国际组织、技术和学术界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需要持续努力和行动。
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作为世界信息社会峰会的重大成果之一,也需要进一步提升所有相关方的参与。联合国经社理事部(UNDESA)作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主管单位,于2016年7月在纽约举行了互联网治理论坛研讨会,并公布了研讨纪要,[37]总结了互联网治理论坛举办十年来的主要影响。在过去十年里,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框架下,诸如网络犯罪和人权、连接下一个10亿人上网、互联网监控和隐私等热点问题得到充分讨论与关注。该论坛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更具有兼容性和包容性的政策讨论和决策文化,打造了一个包括技术团体、政策团体以及民间团体可以有效对话的全球性动态社区,促进了国际和地区性合作,也持续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各个层面的政策讨论。过去十年来地区和国家层面的互联网治理论坛(national and regional IGFs (NRIs)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当然,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还面临许多挑战和不足之处,比如,发展中国国家,互联网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以及年轻人的参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互联网治理论坛作为知识的运输站,也缺乏学术界的广泛参与,尤其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各界参与。
WSIS and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Ten Years Review and Future Outlook
HU Xian-hong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uthor’s ten years work experience in WSIS and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aims at introducing the core idea of WSIS and the central topic of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The article also want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topics, the new topics and the substantive results of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WSIS completed the first 10 years target in 2016, start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next 10 years. This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legal instruments, main spirit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in the past ten years, providing some sources of frequently-used data and related index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community, with the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somecertain policy and academic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in China.
Key words: information society; internet governance; People-centered; inclusiveness
( 责任编辑:李晓晖)
作者简介
胡献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传播 与信息项目官员,2007 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传播学博士。
参考文献
[1]数据见国际(ITU)官方统计:http://www.itu.int/net/wsis/geneva/newsroom/index.html
[2]数据见国际(ITU)官方统计:http://www.itu.int/net/wsis/tunis/newsroom/index.html
[3]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原则宣言》(2003):http://www.itu.int/ne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1161|0
[4] http://www.itu.int/ne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1160|0
[5] http://www.itu.int/ne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2266|0
[6] http://www.itu.int/ne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2267|0
[7] http://www.itu.int/net/wsis/documents/doc_multi.asp?lang=en&id=2267|0
[8]这 种 提 法 可 以 参 见 2014 年 互 联 网 治 理 的 里 程 碑 式 文 件 Netmundial 推 荐 原 则 http://netmundial.br/wp-content/uploads/2014/04/NETmundial-Multistakeholder-Document.pdf
[9]又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ConnectingtheDots 成果文件 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I/CI/pdf/outcome_document.pdf
[10]注:所有这四个纲领性文件都有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版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和中文),本文主要 在参考英语原文的基础上,采纳大部分中文版的翻译,但某些关键定义,比如“互联网治理”,进行了更加精确化 的翻译和处理。
[11]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home-36966
[12] http://www.igf2016.mx/
[13]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home-36966
[14]互联网论坛之友:http://friendsoftheigf.org/
[15]《关于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执行情况全面审查的大会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http://workspace.unpan.org/ sites/Internet/Documents/UNPAN96085.pdf
[16]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17]国际 2013 年报告:测量信息社会,第 2 页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publications/mis2013/MIS2013_without_Annex_4.pdf
[18]国际 2013 年报告:测量信息社会,第 12 页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publications/mis2013/MIS2013_without_Annex_4.pdf
[19] 2014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第 65 页: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0]国际 2014 年报告:测量信息社会,第 46 页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1]国际 2014 年报告:测量信息社会,第 60 页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2] 2014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第 6 页: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3] 2014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第 9-23 页: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4] 2014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第 9 页: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4/
[25]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tlstict2015d3_en.pdf
[26]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magabout
[27]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component/content/article/121-preparatory-process/1290-mag-2013
[28] David Souter “Insid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IGF - retreating to advance, https://www.apc.org/en/blog/inside-information-society- igf-retreating-advance
[29] https://www.icann.org/zh
[30]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about-us/how-we-work/strategy-and-programme/promotion-and-use-of-multilingualism-and-universal-access-to-cyberspace/
[31]数据来源:http://www.internetlivestats.com/internet-users/
[32] http://hrlibrary.umn.edu/hrcouncil_res26-13.pdf
[33]http://unbisnet.un.org:8080/ipac20/ipac.jsp?session=1PQ86449792T1.4551&profile=bib&uri=full=3100001~!1038902~!113&ri=1&aspect=subtab124&menu=search&source=~!horizon
[34] http://www.ohchr.org/EN/Issues/Privacy/SR/Pages/SRPrivacyIndex.aspx
[35] http://netmundial.br/netmundial-multistakeholder-statement/
[36] MAG 咨询会文件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documents/igf-meeting/igf-2016/magmeetings/801-open-consultations-12-july-igf-2016-workshop-evaluations-stats-synthesis
[37]互联网治理论坛十年研讨纪要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documents/igf-meeting/igf-2016/812-igf-retreat-proceedings-22july/file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国逐渐认识到互联网的意义,并开始谋求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1]各国也越来越意识到,互联网技术治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一个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制度,在一系列国际论坛上引发了关于全球互联网治理(GIG)的合理形式和范围的争论。[2]与互联网的成长和互联网全球治理紧张局势并行的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强势崛起。[3]与其他全球治理领域一样,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参与越来越重要。[4]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倡导的治理模式已经对当今美国主导的、自由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形成挑战。中国政府主张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来取代现存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关于中国政府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英文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探讨中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在政府制定总体政策中的作用,二是探究中国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中的一些具体的治理问题。[5]除此之外,大多数论及中国政府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论文没有具体聚焦到本文探讨的话题。有两部学术著作具体阐述了中国政府针对“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政策。刘杨钺的文章谈到中国政府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以及这种治理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对全球互联网治理改革的某些方面做出了贡献,未来随着力量增长有可能会做出更多贡献。[6]弥尔顿•穆勒则认为:中国不大可能成功地改革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多利益攸关方”特性。[7]然而,这两个研究都没有对中国政府参与具体工作进行实证研究,而是将它放在一个广泛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机构以及技术或非技术的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中来考察。关于中国政府参与“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的中国文献比相应的英文文献要丰富一些。然而,同英文文献所受的局限性一样,中文
文献总体上也没能从大量的实证细节来验证中国政府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8]本文旨在以下两点做出贡献:一是填补文献上的空白。在当代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体制中有一些关键性的组织机构,本文对中国政府参与这些组织中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做了实证性详细描述。二是概述推动和制约中国应对“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政策的因素。
网络治理有多种理解方式,取决于不同需求各有所侧重。其中,“互联网治理工作小组”(WGIG)是治理机制之一。WGIG是在联合国主持下成立的,代表着国际政治界关于网络治理涵义的共识,广义理解为:“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在发挥各自角色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和应用一致的原则、规范,共同制定政策,以及开展各类项目的过程,其目的是促进互联网的发展和使用。”[9]“互联网治理工作小组”(WGIG)对于互联网治理的定义传达了两个高度相关且有政治意义的论断。首先,定义明确承认,互联网治理是一个“多利益攸关方”的过程,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主导。其次,这些行动体在互联网治理中各自发挥不同作用。这两个有争议的观点对于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相关的当代全球政治至关重要。[10]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还定义了网络治理问题,将他们分成四类:技术问题、互联网的具体问题、与互联网和其他现象相关的问题、与互联网相关的发展问题。[11]这样的分类说明,全球互联网治理涉及范围广泛,因此,本文将讨论范围限制在第一类,技术问题,这主要是源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技术治理是互联网存在的基础,因此成为考察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域。其次,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最有争议的“多方利益攸关方”治理机构的主要工作是互联网技术治理问题,从而为检验中国政府针对这种决策规范提供了最好的指向。
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一种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的应急制度,它根植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中央管理机构中。[12]ICANN本身是由一系列专业的组织,有时是附属机构来支持以促进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此外,因为互联网必须依赖传统的电信基础设施运作,国际电信联盟(ITU)、其他涉及到基础设施监管的电信管理组织和公司也在当代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功不可没。[13]最后,一系列的政策发展论坛协助制定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的相关政策。[14]但是,受篇幅空间所限,本文将思考论证集中在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机制的关键的几个组织,它们分别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及其附属机构网际网络治理工作小组(WGIG)、互联网治理论坛(IGF)。本文重点研究ICANN,因为它在当代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本文也将考察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和互联网治理论坛(IGF)探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及其“多利益攸关方”决策规则的可能性改革。
然而,与技术问题相关的全球互联网治理及其制度不仅仅是简单的各个组织机构部门的叠加总和。它是由一系列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形成的。[15]其中,对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的管理结构最为重要的是“多利益攸关方”管理规范和决策程序。“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指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共同解决特定议题。[16]这种风行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全球环境治理的观念,被积极应用到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这不仅因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互联网治理的历史参与,也因为国际社会内新兴范式的转移: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得益于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17]“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可能仅仅涉及拥有决策权的利益攸关方这个小团体的对话和争论,或许可以扩大到所有的利益攸关方共同做出决策;尽管未必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平等。[18]在正式制度化之前,各行为体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时受到的有区别的不平等待遇就一直饱受争议,事实上,正是这种争议促成了ICANN的创立。对许多利益攸关方来说,这显然还是有争议的。即便如此,绝大部分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组织明确地自我定位为“多利益攸关方”,尽管什么是适当的利益攸关方的角色这个问题仍有没有定论。“多利益攸关方主义”虽然备受争议,却已经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中根深蒂固。[19]
本文详细考察了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多利益攸关方”制度的主题、以及中国政府对此的立场和策略。
私营部门参与者被定义为名义上的私人的、盈利性的实体,而公民社会参与者通常指私人的、非盈利性实体。[20]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的、公益社团,遵守加利福尼亚法律,管理全球互联网的域名系统(DNS)和互联网协议(IP)地址系统。[22]它是对互联网名称及号码资源进行技术协调和政策发展的顶级管理机构,拥有对域名使用以及通过对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IANA)监督来分配IP地址的权威。[23]IP地址授予和域名使用的权利都受限于与ICANN政策签订的合约。[24]
通过提供集中化管理,ICANN确保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整体性的存在,避免全球互联网破裂或分散成无数的次全球网络。[25]最初,ICANN的权威来自它与美国商务部之间的一份合同。2009年,《承诺确认文件》取代了这份合同,取消了美国政府审查的专属权利,取而代之的是由更有广泛代表性的ICANN社团来行使审查权利。然而,虽然现在ICANN本身正式独立,在实践中仍受限于美国政府的权威。《承诺确认文件》包括承诺将总部留在美国,根据美国法律行事;这使得ICANN终究要服从美国法定管辖权。[26]此外,根服务器管理和IP地址的分配是由IANA来执行,其权力源于与美国商务部的一份合同,根据合同,IANA要依据ICANN政策来运行。[27]ICANN的历史和操作层面的法律因素以及美国政府对IANA的持续管控共同确保了美国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统治地位;成为激起其他国家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推动现存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因素。[28]
ICANN采用“多利益攸关方”模式来治理,支持由各不同利益攸关方组成组织,自我描述为“自下而上、共识驱动,多利益攸关方模式”。[29]这种治理模式的形成受一种哲学观念的影响,即互联网技术社团有助于建立互联网。美国在创建ICANN的时候,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这种哲学观念,只做了细微的修改,即赋予了私营部门领导权。[30]最终决策权归属于ICANN董事会,主要由各种各样的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多利益攸关方”团体组成。董事会通常根据ICANN的支持性组织、咨询委员会以及ICANN内部其他实体的报告来制定政策。ICANN的支持机构代表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相关的特定政策区域。地址支持组织(ASO)代表互联网地址分配的利益攸关方,国家代码域名支持组织(CCNSO)代表国家特定域名运营商,通用域名支持组织(GNSO)代表通用域名运营商以及其他商业和非商业实体。ICANN的咨询委员会的设计初衷是代表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的,包括代表政府的政府咨询委员会(GAC);代表根服务器管理员的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RSSAC);代表网络安全专家的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SSAC);以及代表个人互联网用户的普通会员咨询委员会(ALAC)。[31]
ICANN管理模式中与中国相关的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其将政府降级为顾问角色。[32]鉴于此,中国政府只是偶尔参与ICANN活动;对私营部门突出地位的不满以及认为ICANN是由美国控制的、因而是其扩大全球霸权的主要工具的观念阻碍了中国参与ICANN。[33]2001年,中国自愿退出政府咨询委员会(GAC),直到2009年才重新加入。[34]中国似乎已经决定,它需要参与政府咨询委员会(GAC)来推动其在国际化域名(IDN)政策中的权益。支持这一论点的事实是,ICANN和政府咨询委员会(GAC)开会讨论国际化域名(IDN)之后,ICANN正式批准国际化域名(IDNs)加入全球根。在中国重返ICANN之后第二次参加政府咨询委员会(GAC)时,通知政府咨询委员会(GAC),中国将第一轮申请快速跟踪国家代码国际化域名(IDN)。中国代表还在政府咨询委员会(GAC)2010年会上就国际化域名(IDN)政策发表了评论。
随着这些更直接的关注,中国似乎已经确定,参与政府咨询委员会(GAC)是必要的,因为这样中国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2010年3月,ICANN的首席执行官在访问北京时会见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主任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的代表们,并随后在2011年又到中国进行了一次更深入的访问。自此之后,这种参与模式不断加强。2012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部长就国际化域名IDN政策相关问题致信ICANN首席执行官。2013年4月,ICANN在北京召开常规会议,开设新的“全球参与办公室”。下文即将讨论到,中国政府的政策转变可能是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和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的不利所致,从而转向了更加传统的政府间实体,如国际电联(ITU)。[35]
然而,中国整体参与ICANN远比中国政府的参与更加广泛。即使在中国政府缺席的时候,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和私人参与者仍然持续参与ICANN。经常活跃在中国互联网技术社区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在1999至2001年期间担任ICANN地址委员会ASO理事。薛虹是ALAC的创始成员,并至此之后一直担任ICANN内部的职务。中国非政府行为体也参与到高级别的ICANN国际化域名(IDN)高级总裁顾问委员会中。该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向ICANN主席报告与国际化域名IDN相关事项,包括两名中国成员,其中一人是该委员会的主席。2011年,李晓东教授曾短期担任ICANN代表亚洲区的副总裁。2002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和中国互联网协会(ISC)共同在上海举行会议,都频繁向ICANN提交政策建议。事实上,早在2003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让其中的一名成员钱华林竞选ICANN理事会理事。[36]然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08年才加入国家代码域名支持组织(CCNSO)。除了这些机构,由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组成的中国互联网技术社团一直都在通过普通会员咨询委员会(ALAC)和通用名称支持组(GNSO)积极参与ICANN的政策过程。中国的非国家行为体一直在追求中文国际域名(IDNs)在ICANN中的利益,主要通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和中文域名协调联合会(CDNC)向ICANN提交申请这两种途径。[37]自2008年成立以来,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CONAC)负责管理中国重要的国际域名称(IDNs)——CONAC是一个正式的非盈利的公民社会机构,但直接隶属于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ICANN的政策和管理过程。[38]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参与ICANN反映出:不赞同私营企业在制定决策和设置政策中占据首要地位;认为ICANN是美国霸权的工具;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行为显然是出于对硬和软实力的考虑,中国政府不默许美国政府或非政府对互联网技术架构的隐形控制;不认同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或非政府行为者之间的任何不平等;[39]然而,中国一直有限度地与ICANN打交道。因为完全在ICANN管理之外来运营中国互联网将损害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目标、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的影响力以及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一个纯粹孤立的中国互联网将损害中国的竞争力,具体指抑制全球贸易和技术转让,并发出一个强烈的孤立主义的信号。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以及后来的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的出现,提高了这种期待,期待ICANN能够重建倾向于更多的政府权力的结构,这意味着中国即使不参加ICANN也能保持其影响力。中国重返GAC意味着它承认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和IGF没有达到重建作用,权衡利弊,不参加GAC只会意味着中国的权力减少,尤其是存在利益关系的与中文域名相关的政策制定。[40]以上这点,鼓励和促使中国政府重返GAC。还有一事证明这一评价,在中国政府不参与ICANN期间,中国对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参与ICANN持容忍态度,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意识到完全从这个组织退出将损害中国的利益,还很有可能损害中国的声誉。
(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关注的不仅仅是互联网治理,还试图探讨由于信息社会的出现而引发的全方位的问题,很明显一个主要原因是全球社会意识到互联网治理(GIG)需要一个世界峰会,因此成了最主要的优先工作任务。[41]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流程包括峰会之前的筹备阶段,即利益攸关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三方在内的筹备委员会共同开会决定峰会的议程以及其他与峰会相关的事宜。此外,每个峰会之前会召开区域会议,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中有一个与全球互联网治理(GIG)有关的重要元素——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一个创建于两个峰会之间的组织,专注于互联网治理。美国在日内瓦避谈此话题,因为它明显感觉到公开谈论全球互联网治理(GIG)会增加ICANN被取代的风险。[42]从一开始,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就被明确定位为“多利益攸关方”事务。[43]然而,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中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与ICANN采取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治理模式更像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将非国家行为体边缘化。[44]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中,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参与是被积极鼓励的,而许多国家却很不情愿这样做。[45]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过程。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第一阶段,中国代表出席了所有筹备委员会会议、区域会议和正式峰会。中国参与第一次峰会的筹备会议和实际峰会时,主要关注的主题是政府主导信息社会管理和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必要性,坚持认为峰会应该关注经济和技术,网络安全问题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总的来说,中国就全球互联网治理(GIG)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关注点非常明确——重建有利于国家技术管理部署的必要性。
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第一阶段类似,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中非常活跃,正是在这个论坛上,中国政府做出了对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多利益攸关方”立场的最有力的声明。除了第一次会议,在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四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每次都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即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应该主要由国家来主导。随着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的发展进步,中国更加坚决和强硬地谴责当前私营部门和美国控制ICANN;尽管中国容许私营部门或公民社会保留以顾问的身份角色参与相关活动。最终,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第三和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大致的改革框架,即:在联合国下创建一个政府间组织,承担ICANN目前的角色,但允许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以顾问的身份加入。当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完成审议后,发布了一个报告,同时给出了互联网治理的定义,提供了改革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的四条建议。[46]在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随后出版的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单册中,中国代表团团长胡启恒撰写了一篇文章来表明她的立场:四种改革方案中,以全球互联网理事会为首的模式1最合理。[47]此选项最接近于中国在WGIG的提议。然而,尽管WGIG建议了新的制度模式,它们并没有被采纳并付诸实践。
中国政府在参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第二阶段会议时,没有在日内瓦会议和WGIG上那么活跃,虽然在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总结陈词,重申其对WGIG的立场,专门提到政府占首要地位的必要性。中国也在正式峰会上对涉及数字鸿沟、国际合作、尊重文化差异以及加强网络安全等方面做了广泛但没有争议的陈述。然而,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已经在互联网治理工作组表达了鲜明立场,预计如果进一步支持对“多利益攸关方”改革会适得其反。以下事实可以支持这种解释: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比突尼斯会议派出了更多代表、更高调地参会。
中国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也参与了WSIS过程,虽然远不及政府声势浩大。只有一个中国公司(华为)参加了第一个峰会,但这已经让出席突尼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会议的中国企业增加到了四个,华为和中兴都派出了代表。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也出席了两个峰会,至少有四个组织出席了日内瓦会议,至少有五个组织出席了突尼斯会议。在这些公民社会参与者中,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ISC)最为知名、最高调,在互联网治理工作组会议上参与了关于垃圾邮件治理和政府在互联网管理中的角色的政策讨论;它完全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并认为政府应该在制定互联网技术标准中扮演主要角色。
中国参与世界信息社会峰会,特别是参加互联网治理工作组的贡献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政府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领域应对“多利益攸关方”管理的方法的信息。它清楚地表明,中国担心政府在ICANN中的附属地位和美国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霸权地位会对自身权利和地位产生间接的不良影响。[48]中国力求将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的重心转移到政府间机构。为了推进这个目标,中国与其他和自己有一样诉求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并通过倡导其立场、通过表达支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来壮大自己,中国的国际声誉在发展中国家间得到极大的加强和改善。接纳中国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参与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和声誉软实力。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互联网治理工作组中的行为表明了对“多利益攸关方”治理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但它明显更倾向国家主导。
(二)互联网治理论坛(IGF)
虽然已经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讨论过,包括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内的参会者一致同意,全球互联网治理讨论应该在一个新创建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中继续进行。类似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互联网治理论坛遵循相似的模式:在正式论坛和地区会议开始之前进行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参与的筹备过程,以便讨论和设定议程。[49]互联网治理论坛主要针对网络治理问题,但没有决策权;只能通过共识来做建议。正如下面所讨论的,政府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行为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后者支持ICANN、IGF只保留协商,而那些对ICANN不满的利益攸关方,则认为IGF应该发出更强的声音、做出更强硬的建议。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作为改革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机制的IGF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毫无实权、不起作用的机构。
像WSIS一样,IGF明确定位为“多利益攸关方”论坛。但“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形式略有不同。[50]IGF设有一个秘书处,负责管理论坛,包括决定IGF治理结构的过程。实际上,IGF由一个多利益攸关方咨询组(MAG)来组成的,包括40至60名来自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其中大约有一半成员是政府代表,四分之一来自私营部门,四分之一来自公民社会。多利益攸关方咨询组(MAG)与秘书处一起,管理筹备过程,组织IGF正式大会。在筹备过程中,组织结构较为松散,随后是多利益攸关方咨询组(MAG)会议、IGF区域会议以及进一步的筹备会议。在此过程中,正式论坛将拟讨论的议题按照主题来组织安排,多利益攸关方咨询组(MAG)选择专题发言人来主持IGF各主题会议。在此之后,IGF将向所有“多利益攸关方”开放会议。除了正式会议外,一系列非正式的工作坊和动态联盟会在IGF会议期间向所有感兴趣的利益攸关方开放。工作坊和动态联盟的研究成果之后将在IGF的相关会议上汇报或在IGF网站上公布。
像参与WSIS一样,中国政府也一直积极参与IGF并就全球互联网治理相关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广泛的建议,但其明显的关注点是加强政府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地位。在IGF第一次筹备过程中,中国联合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成功地倡导了多利益攸关方咨询组(MAG)结构,如前所述,巩固了政府在IGF中的影响力,对IGF的议程设置提出了建议,提倡在IGF范围内纳入更广泛的讨论议题。一位来自中国工信部的代表被任命为多利益攸关方咨询组(MAG)成员,一位工信部的代表一直在多利益攸关方咨询组(MAG)留任,除了2010年以外。在第一次论坛期间,中国政府的贡献仅限于认可保护国家互联网安全的重要性。第一次IGF没有把ICANN相关的治理问题列入日程,在2007年筹备阶段,中国代表与其他国家代表一起,成功补救了这一缺憾。在筹备会议的收尾阶段,中国表示不满,认为IGF不是“结果导向型”,并表明期待IGF能对全球互联网治理改革提出更多建议。在正式论坛上,中国政府代表作出评论:推动有利于政府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改革非常必要,如同在WSIS一样,中国还间接地提到了美国在现行体系中的霸权统治。除此之外,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以及互联网治理中的动态联盟原则等发展问题相关的工作上做出了贡献,重申了对世界互联网标准的支持,此标准是中国公民社会参与者在2006年IGF会议上提出的,明确强调发展一个安全、可信赖的互联网。[51]
中国政府在2008年筹备过程中不是很活跃,仅表示对现行日程的支持,重申中国对“多利益攸关方”治理的观点:在ICANN中,政府应该处于领导地位并被给予更多权利,并再一次间接提到当今互联网世界由美国统治。在此次IGF上,中国就多语种相关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球互联网治理应该纳入更多的政府参与,这也是对巴西号召的响应和支持。2008年,中国首次表态:对IGF缺乏进步表示失望,如果它不能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建议暂时废弃IGF。除此以外,中国政府参与讨论了发展问题、互联网安全问题、互联网域名管理中的在线纠纷解决问题等工作坊。有趣的是,世界互联网规范第三个版本受到推广,但不幸的是再也无法获得。在2009年筹备过程中,中国代表团明确表示,IGF已经失败,应该被废除,并用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政府间组织取而代之,解决美国控制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的问题。中国代表团还强调,安全和网络犯罪是重要议题,知识产权与传统图书馆资源的相关议题应该被纳入IGF。此外,中国政府评论到,利益攸关方在讨论内容限制的话题上应该非常谨慎,并表明限制内容是国家的权利。正式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团评论了新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本)的部署,并指出,它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完成。中国在最后陈述中宣称,IGF未能完成改革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任务,因此,不应该复审任期,重申支持联合国直接解决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改革的问题。
2009年互联网治理论坛之后,联合国开始复审IGF任期。中国外交官沙祖康作为代表出席世界信息社会峰会,随后担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他试图把全新的IGF转型为一个更多政府间的、结果导向型的机构。[52]作为一个“多利益攸关方”组织,各方对IGF的未来特征争论不休,联合国复审和一系列IGF论坛也在同时进行,这些汇聚在一起组成了一场关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前途的更大的联合国争斗。[53]2010年IGF筹备阶段,中国政府言辞谨慎地表示,IGF的活动应该继续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中进行、复审IGF任期的相关决策应该早日做出。鉴于联合国秘书长当时表示联合国大会将更新IGF,按照IGF利益攸关方多数人的意见,中国没有在更换IGF问题上的坚持己见也没有派出工信部代表出席2010年多利益攸关方咨询组(MAG)专家小组会。IGF正式大会上,中国代表阐述了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的重要性并表示中国将全力与世界合作共同解决互联网治理问题。中国政府似乎没有参与IGF2010相关的工作坊,工作坊参会者在两个场合都提到了这点。尽管中国政府反对IGF延期,但工信部代表在2011年重返多利益攸关方咨询组(MAG),出席了2011年IGF筹备进程的第二阶段,参加了其中一个IGF主要会议,并作为专家小组成员加入了言论自由相关的讨论和工作坊。2011年IGF上,中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在联合国上提出一个被多次提到的倡议:制定一个有关网络安全的政府间协议,协议中包含推进国家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首要地位的表述。[54]虽然一位中国外交部代表在IGF上承认了这点,但他的评论仅限于指出争议,并说明拟定的协议将不具约束力。有趣的是,2011年,没有进一步关于IGF或整个ICANN应该被政府间组织取代的言论出现。在2012年举行的IGF上,虽然由工信部代表和中国外交部代表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非常活跃,但并没有就“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改革的任何问题做出任何评论。在2013年筹备过程中,工信部代表强调关键的互联网资源——ICANN范围内的问题——应该被添加到主要议程中。
中国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代表也一直积极参与互联网治理论坛,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参与了每一届IGF的工作坊。更确切地讲,在2006年互联网治理论坛上,中国互联网协会(ISC)和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就垃圾邮件问题提供了政策建议,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还对国际化域名(IDN)政策讨论做出贡献,首次提出了世界互联网规范。2007年,一位中国互联网应急小组的代表发言表示支持政府的观点,认为单独一个国家控制整个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是不公平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报告了中国国内不依赖IP地址而发展起来的域名系统(DNS)。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ISC)秘书长对垃圾邮件和政府参与互联网治理的必要性做出了评论。除了2007年IGF正式会议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中国互联网协会(ISC)和其他中国组织参与了发展议题的工作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参与了关于全球互联网治理原则问题的动态联盟。2008年,中国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参与逐渐扩大,出现在不同主题的工作坊之中:互联网与残疾人、数字教育、发展与DNS管理中的在线纠纷解决等;中国互联网协会参与了IGF一个关于垃圾邮件和儿童色情的会议。2009年,中国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参加IGF有所减少,只有中国互联网协会(ISC)参与了IGF的一个讨论,中国互联网协会(ISC)副主席表示,IGF的重点应该放在跨国问题、尊重民族和文化差异的探讨上。2010年,虽然政府缺席,中国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却参与了大量的与互联网相关的国际法律问题、发展问题、互联网权利和原则问题、云计算问题的主题工作坊。这种不断参加工作坊的状态一直贯穿2011年和2012年。2012年,中国第一个民营代表被任命为多利益攸关方咨询组(MAG)成员,同时被吸纳为会员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郭良。
中国政府参与互联网治理论坛(IGF)提供了一个侧面,让我们能够大致了解中国在努力改革“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的过程。中国的举措始终围绕提高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影响力而进行。中国一直坚持有利于国家行为体的制度改革立场,但是已经适度调整行为来反思自身的局限性,通过国家行为体代理者或非国家行为体来最大限度发挥其影响力。IGF建立之初,中国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推动扩大国家行为体对多利益攸关方咨询组(MAG)的控制力,随后游说其他行为体将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囊括在IGF日程当中。这两个举动的结合增加了一种可能性:IGF向联合国建议ICANN应该被取代。然而,当IGF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时,中国明确表示了失望。然而,中国政府继续支持、至少是默许中国非政府行为体参与活动。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部分会对中国软实力造成损害。中国非政府行为体的参与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中国公民社会呼唤加强国家代表性和中国非国家行为体逐渐扩大在IGF的参与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总体而言,中国对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改革路径和方向是:期望将现行的私营部门主导的体制改革成一个更加传统、国家主导的体制。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的几个主要机构中,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赞同ICANN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并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互联网工作组(WGIG)和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中极力倡导更多的政府间权力介入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它积极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间机构来监管互联网,始终对现存的私营部门和美国政府控制ICANN、非国家行为体在WSIS、WGIG和IGF中占据突出地位表示不满。中国的态度很明确,坚持政府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主要地位,虽然它承认私营部门和小部分公民社会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中国对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的方式最容易从前文提及的中国国内的政治体制来理解。中国在此领域的政策立场和行为很可能表达了两点:一是源自国家治理的立场(认可非国家行为体在某些方面的治理是有价值的);二是吸引其他利益攸关方的策略。
然而,尽管非常努力,中国的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效果仍有待观察。这很大程度上归结于美国拥有更强大的硬实力。作为互联网的发明者,美国政府已经能够建立和巩固有利于自身以及美国和其他非政府行为体利益的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体制;尽管中国政府以国家为中心的改革得到全世界很多其他国家政府大力支持,软实力也是中国未能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确保其作用的重要原因。发达民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的支持广泛但态度分化,这让中国政府试图让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组织中边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在这些机构中追求其议程的主要驱动力量为中国政府获取了更大的影响力,包括获得互联网技术架构中更大的影响力,认同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主权平等。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和互联网治理论坛(IGF)成立前,中国政府原本准备参与ICANN,尽管对私营部门与美国的主导地位持保留态度,随后在评估了互联网治理论坛(IGF)未能纠正这种失衡后,中国重新参与ICANN,将其作为影响力的次优选择。中国对待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体制也呈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
中国政府允许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大量参与ICANN、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和互联网治理论坛(IGF),而且这种参与越来越多。中国默许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公民社会共同促进共享的利益。然而,这并不表明中国非国家行为体必然在互联网技术治理政策中拥有更多的影响力。中国已经能够分别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中获得支持,支持国家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占主导地位、支持消除美国政府单方面对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体制的权威。本文将讨论重点限制在中国政府参与几个关键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组织以及其改革现行“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的立场和潜力,应该认识到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以及更广范围的相关问题中的利益和参与的重要性。这种广泛的参与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尽管中国政府着重在纠正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领域中的权力失衡,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一直是一个相对的建设者角色。从整体上看,中国行为的驱动力和它在“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体制中面临的结构限制,共同导致它采取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角色、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倡导者角色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代表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的立场却几乎没有改变。至于中国政府未来在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领域的行动,据预测,它将继续坚持更多的国家参与,同时允许中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但很难迫使一个观念根深蒂固的由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的ICANN同意改革。
China and Technical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Beijing's Approach to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within ICANN, WSIS and the IGF
Tristan GALLOWAY HE Bao-gang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ninet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ngaged in a process of attempting to reform the multi-stakeholder, US government and non-state actor dominated, technical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regime. This paper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on Beijing's approach to this issue by providing a detailed empirical account of its involvement in a few core regime organisations. It argues that Beijing's reform approach is guided by its domestically-derived preferences for strong state authority and expanding China's global power, but that its reform efforts are unlikely to succeed based to countervailing structural hard and soft power factors.
Key words: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Internet regime, multi-stakeholder, Beijing's approach
(责任编辑:李晓晖)
作者简介
何包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主任。兼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大学政府系教授,曾任职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王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Milton Mueller, Ruling the Root: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Taming of Cyberspa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2), ch. 9.
[2] Daniel Drezner,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9, no. 3 (2004): 477–98, 486–91; Marcus Franda, Governing the Internet: The Emergence of an International Regim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1), p. 74.
[3] The terms “China” and “Beijing” are intended as shorthand to refer specifcally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t Chinese non-state actors, unless the context specifcally indicates otherwise.
[4] Robert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d Wang Hongying and James Rosenau, “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Asian Perspective 33, no. 3 (2009): 5–39.
[5] Warren Chik, “Lord of Your Domain, But Master of None: The Need to Harmonize and Recalibrate the Domain Name Regime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6, no. 1 (2008): 8–72; Park Youn Ju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s”, PhD diss., Syracuse University, 2008; Tso Chen-dong, “Computer Scientists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Issues & Studies 44, no. 2 (2008): 103–44; Xue Hong, “The Voice of China: A Story of Chinese-Character Domain Names”,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2 (2004): 559–91; and Hidetaka Yoshimatsu, “Global Competition and Technology Standards: Japan’s Quest for Techno-Regionalis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7, no. 3 (2007): 439–68.
[6] Liu Yangyue, “The Rise of China and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China Media Research 8, no. 2 2012): 46–55.
[7] Milton Mueller, “China and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A Tiger by the Tail”, in Access Contested: Security,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in Asian Cyberspace, ed. Ronald Deibert, John Palfrey, Rafal Rohozinski and Jonathan Zittrai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0), pp. 177–94.
[8] Run Hongqiang and Han Xia, “Hulianwang guoji zhili wenti zongshu” (Summary of International Internet Governance Issues), Dianxin wang jishu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Technology), no. 10 (2005): 16–19; Jiang Lixiao, “Shi xi hulianwang zhili de gainian, jizhi yu kunjing” (Analysis of Concept, Regime and Diffculty of Internet Governance), Jiangnan shehui xueyuan xuebao ( Journal of Jiangnan Social University) 13, no. 3 (2011): 34–8; Yi Wenli, “Zhong Mei zai wangluo kongjian de fenqi yu hezuo lujing” (Sino-US Disagreement and Cooperation in Cyberspace), Xiandai guoji guanxi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7 (2012): 28–33; and Liu Yangyue, “Quanqiu wangliu Quanqiu wangluo zhili jizhi: yanbian, chongtu yu qianjing”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Regime: Evolution, Confict and Prospects), Guoji luntan (International Forum) 14, no. 1 (2012): 14–9.
[9]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WGIG),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 WGIG, June 2005, at <http://www.wgig.org/docs/WGIGREPORT.pdf> [5 April 2013], p. 4.
[10] Richard Collins, “Trilateralism, Legitimacy and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Information Polity 12, no. 1 (2007): 15–28, esp. 23; and Kostantinos Komaitis, “Aristotle, Europe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Pacifc McGeorge Global Business & Development Law Journal 21, no. 1 (2008): 57–78, esp. 58.
[11] WGIG,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p. 5.
[12] Franda, Governing the Internet, pp. 45–65; Malcolm,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pp. 38–9; Milton Mueller, John Mathiason and Lee McKnight, “Making Sense of ‘Internet Governance’: Defning Principles and Norms in a Policy Context”, Internet Governance Project, Syracuse University, 2004, at <http://ccent.syr.edu/wp-content/uploads/2014/05/su- igp-rev2.pdf> [5 April 2013], pp. 1–22, 1–5.
[13] William Drake and Ernest Wilson, eds., Governing Global Electronic Network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olicy and Powe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5), Part 1.
[14] Malcolm,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pp. 38–9.
[15]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no. 2 (1982): 185–205, esp. 185–6; Mueller, “China and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p. 64.
[16] Minu Hemmati, Felix Dodds and Jasmin Enayati, Multi-Stakeholder Processes for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Beyond Deadlock and Confict (London: Earthscan, 2002), p. 2.
[17] Kof Annan, We the People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0), pp. 13, 69; Mueller, Ruling the Root, p. 69.
[18] Nancy Vallejo and Pierre Hauselmann, Governance and Multi-Stakeholder Processes (Winnipeg, MB: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4), p. 6.
[19] Franda, Governing the Internet, pp. 55–60; ICANN, “ICANN Leader says Multi-Stakeholder Model of Internet Governance under Threat”, The Internet Corport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 news release, 14 September 2010, at <http://www.icann.org/en/news/releases/release-14sep10-en.pdf> [5 April 2013];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About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website, at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aboutigf> [5 April 2013].
[20] Zhang Ye, “China’s Emerging Civil Socie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2003, 1–24, esp. 3–12, at <http://www. 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les/papers/2003/8/china%20ye/ye2003.pdf> [5 April 2013].
[21] Evidence of Chinese involvement in ICANN, WSIS and WGIG and the IGF is sourced from a reasonably exhaustive 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accessible respectively at <http://www.icann.org/, http://www.itu.int/wsis/ and http://www.wgig. org/index.html> and <http://www.intgovforum.org/> (except where otherwise indicated by footnote references). Research is inclusive of documents available up to 5 April 2013.
[22] ICANN, “What does ICANN do?”, ICANN website, at <http://www.icann.org/en/about/participate/what> [5 April 2013].
[23] IANA, “Introducing IANA”,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 website, at <http://www.iana.org/about/> [5 April 2013].
[24] Steve DelBianco and Braden Cox, “ICANN Internet Governance: Is it Working?”, Pacifc McGeorge Global Business & Development Law Journal 21 (2008): 27–44, esp. 28–30.
[25] Laura DeNardis, “Open Standards and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Law and Policy 13 (2009): 168–84, esp. 176.
[26] ICANN, “ICANN CEO Talks about the New Affrmation of Commitments”, ICANN website, 30 September 2009, at <http://www.icann.org/en/news/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30sep09-en.htm> [5 April 2013]; and International Shoe Company v. State of Washington, Offce of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 Placement, et al., 326 US 310 (1945).
[27]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IANA Functions Contract”,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2), at <http://www.ntia.doc.gov/page/iana-functions-purchase- order> [5 April 2013].
[28] Drezner,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p. 497.
[29]“Affrmation of Commitments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Article 8(c), ICANN website, 30 September 2009, at <http://www.icann.org/en/about/agreements/ aoc/affrmation-of-commitments-30sep09-en.htm> [5 April 2013]; and ICANN, “Welcome to ICANN!”, ICANN website, at <http://www.icann.org/en/about/welcome> [5 April 2013].
[30] Grace Ayres, “ICANN’s Multi-Stakeholder Model”, ICANN (2008), at <https://www.icann.org/en/system/fles/fles/icann- multi-stakeholder-model-14apr08-en.pdf> [5 April 2013], p. 2; and Jay Kesan and Anres Gallo, “Pondering the Politics of Private Procedures: The Case of ICANN”, I/S: A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4 (2008): 345–409, esp. 362.
[31]“Bylaws for Internet Corporation of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A California Nonproft Public-Beneft Corporation”, ICANN website, at <http://www.icann.org/en/about/governance/bylaws> [5 April 2013].
[32] Kesan and Gallo, “Pondering the Politics of Private Procedures”, pp. 390–401.
[33]“Comment: Internet—New Shot in the Arm for US Hegemony”, China Daily, 22 January 2010.
[34] Nick Thorne, “Notes from ICANN CEO’s Visit to China”, ICANN website, 5 March 2010, at <http://blog.icann. org/2010/03/notes-from-icann-ceos-visit-to-china/> [5 April 2013]; and Tso, “Computer Scientists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p. 132.
[35] Rebecca MacKinnon, “ICANN, Civil Society, and Free Speech”, RConversations, 27 July 2009, at <http://rconversation. blogs.com/rconversation/2009/07/icann-civil-society-and-free-speech.html> [5 April 2013].
[36] Tso, “Computer Scientists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p. 132.
[37] Chinese Domain Name Consortium (CDNC), “The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izing ccTLD Names”, ICANN website, June 2005, at <http://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idn-tld-cdnc.pdf> [5 April 2013]; Hong Xue, “The Voice of China”, pp. 583–5.
[38] China Organizational Name Administrative Center (CONAC), “Welcome to CONAC”, CONAC website, at <http://www. chinagov.cn/english/aboutconac/> [5 April 2013].
[39] Wang Fei-ling, “Beijing’s Incentive Structure: The Pursuit of Preservation, Prosperity, and Power”, in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d. Deng Yong and Wang Fei-Ling (Oxford: Rowman & Littlefelds Publishers, 2005), pp. 19–49, esp. 39.
[40]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Transcript of the 2009 IGF Taking Stock 1 Meeting”, 2009, at <http://www. intgovforum.org/cms/2009/sharm_el_Sheikh/Transcripts/Sharm%20El%20Sheikh%2018%20November%20Stock%20 Taking%20Part%20I.pdf> [5 April 2013], pp. 9–10; and Rebecca MacKinnon, “ICANN, Civil Society, and Free Speech”; Tso, “Computer Scientists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pp. 134–5.
[41] Victor Mayer-Schönberger and Malte Ziewitz, “Jefferson Rebuff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et Governance”, Columbi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Review 8 (2007): 188–204, 188–191.
[42] Marcus Kummer, “The Debate on Internet Governance: From Geneva to Tunis and Beyond”, Information Polity 12, no. 1 (2007): 5–13.
[43]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on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Res/56/183”, United Nations, 2002, at <http://www.itu.int/wsis/docs/background/resolutions/56_183_unga_2002.pdf> [5 April 2013].
[44] Kummer, “The Debate on Internet Governance”, p. 6.
[45] Collins, “Trilateralism, Legitimacy and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pp. 23–4.
[46] WGIG,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WGIG, 2005, pp. 13–6.
[47] Hu Qiheng, “Internationalized Oversight of Internet Resource Management”, in Reforming Internet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from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ed. William Drake (New York: The U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ask Force, 2005), pp. 200–1.
[48] Wang, “Beijing’s Incentive Structure”, p. 39.
[49] Malcolm,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pp. 355, 364–78.
[50] Mernance Forum (IGF), “The Multi-Stakeholder Advisory Group”, IGF website, 2013, at <http://www.intgovforum.org/ cms/magabout> , [5 April 2013].
[51] Winfeld and Mendoza, “Does China Hope to Remap the Internet in Its Own Image?”.
[52] Mueller, “China and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p. 185.
[53] UN General Assembly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mprove-ments to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A/67/65-E/2012/48”,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16 March 2010, at <http:// unctad.org/meetings/en/SessionalDocuments/a67d65_en.pdf> [5 April 2013].
[54] UN General Assembly, “Letter Dated 12 September 2011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ajikstan and Uzbekist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A/66/359”, United Nations, Disarmament Reference Library, 11 September 2011, pp. 3–4, at <https://disarmament-library.un.org/UNODA/Library.nsf/f44 6fe4c20839e50852578790055e729/329f71777f4b4e4e85257a7f005db45a/$FILE/A-66-359.pdf > [5 April 2013].
TOP1《WHOIS管理互联网:协议、政策和隐私》:WHOIS Running the Internet: Protocol, Policy, and Priva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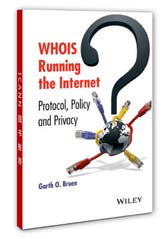
作者:Garth O. Bruen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John Wiley & Sons, Inc;2016年
WHOIS是“Who is”(谁是)这两个单词的合写形式。WHOIS数据库可以回答谁是域名或IP地址的负责人。通过使用WHOIS数据库,任何人都可以查询某个具体网站的注册信息,涉及域名持有人、域名注册商、注册地、创建和更新日期、联系电话、传真、邮箱等信息。然而,各国的隐私法律存在差异,欧盟在这方面的规定比较严苛,美国则相对宽松。各国在是否应该实名显示域名所有相关信息等方面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及其解决方式是关于互联网政策的较为核心的辩论和实践。在这个管理权过渡完成的关键时刻,ICANN正在制定第二代WHOIS规则,关于WHOIS方面的政策辩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本书从技术和政策的角度讲述了WHOIS的历史和现状。
TOP2《控制根:互联网治理和网络空间驯服》:Ruling the Root: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Taming of Cybersp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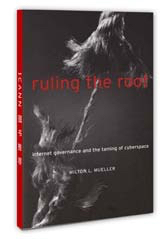
作者:Milton L. Mueller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MIT Press;2002年
米尔顿•穆勒的这本书全面记载了ICANN的前传和童年时代。他把互联网跟名称、数字、协议以及根服务器有关的一系列功能称为“根”。这是去中心化、非等级化的互联网架构中唯一具有中心化和等级化特点的内容。ICANN成立之时,美国市场接管一切的思维大行其道,克林顿政府从最早的时刻就给ICANN定下了私有化的目标。然而,ICANN成立之前,技术社群、商业力量、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已经围绕对根的控制展开过争斗。穆勒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记叙了一个驯服和体制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之后的ICANN机制,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TOP3《国际法对地理名称的保护和域名系统政策》:Protection of Geographic Name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ain Name System Poli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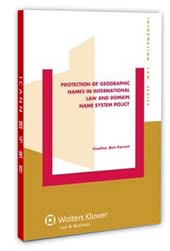
作者:Heather Ann Forrest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3年
巴西、智利围绕“amazon”这个名称跟亚马逊公司之间的争议由来已久。法国和ICANN在“.wine”这个顶级域的争议广为知晓。信息经济时代,一个域名有可能涉及到巨大的产业。哪些产品或战略资产具有特定的地理名称属性,在成为网络空间各种级别的名称之前需要特殊保护?按照各洲、地区、国家、城市的名称来分配域名是否合法?是否可行?这本书的作者承认,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处于提出问题的阶段,但是他仍然从知识产权、域名体系的扩张、不公平竞争等多个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
TOP4《互联网星系: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思考》: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es, and Soci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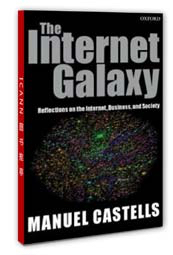
作者:Manuel Castells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年
在完成信息时代三部曲鸿篇巨著之后,卡斯特将自己的关于互联网的想法浓缩成《互联网星系》这本小书,记叙了互联网的简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层面。虽然只有第一章涉及到ICANN的产生,但是该书从中观的角度讲述了互联网的特性。黑客、隐私、数字鸿沟都有涉猎。本书衔接了卡斯特此前提出的网络社会理论,同时启发了他此后关于《传播权力》和《希望与愤怒之网》等关键著述。
TOP5《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放眼未来》:The World Summit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oving from the Past into the Fu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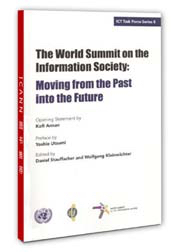
编者:Daniel Stauffacher和Wolfgang Kleinwächter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United Nations;2005年
这本书收集了关于互联网治理辩论的初稿,是联合国讨论互联网治理问题的核心线索的起源,主要涉及2003年召开的信息社会峰会日内瓦峰会,记载了各国领导人、商业力量、技术社群、民间团体围绕知识产权、数字鸿沟、言论自由、互联网治理等多个主题的发言和讨论。民间团体第一次作为一种合法的力量登上网络空间的辩论平台。对美国垄断互联网资源的挑战已经若隐若现,即将在第二次峰会爆发。习近平主席关于多边、民主、透明原则的论述也来源于日内瓦峰会的文件和宣言。(本期推荐人:徐培喜)
网络空间治理,是当前国际社会的热点话题。人们普遍认为,网络空间的快速发展与广泛运用,一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另一方面也带来诸多意想不到、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恰当的方式框定网络空间发展方向,使其继续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防止负面因素无限膨胀,已是普遍共识。时至今日,有关网络空间治理的争论“已不再是互联网‘能否或是否应该被治理’”,而是何种治理“最受欢迎”[1]。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在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上依然举步维艰,这与互联网本身所特有的一些技术属性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本文拟就这些分歧作一简要分析,目的是从中找出不同主张之间的可能契合点,为今后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寻求可行路径。
按照“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给出的定义,互联网治理是指“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根据各自的作用,开发和实施共同的原则、准则、规则、决策程序和方案,以规范互联网的发展与使用”[2],并不涉及互联网的属性问题。套用此概念,网络空间治理的范畴并不涉及网络空间的属性问题。然而,将网络空间视作不受主权限制的“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还是强调其主权特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直接影响着网络空间治理的方方面面,也是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弊端丛生的根源。[3]
坚持“全球公域”理念者强调,网络空间由遍布世界各地的电子设施联结而成,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进出,数据传输和人际沟通也不再受到物理障碍和政治国界的制约。这种全球特质“对民族国家构成了挑战”,[4]使得网络空间成为类似于太空、公海的“全球公域”,[5]或是类似于南极那样的“在主权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自然资产”。[6]其基本含义,是“不能被特定国家所控制,向所有国家、组织和个人开放,由于其存在超越了任何国家主权,必须通过国际条约或协定实施管理”。[7]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众多新兴国家,强调网络空间的主权属性毋庸置疑。无论是连接网络的物理基础设施,确保网络运转的计算机、路由器、交换机等设备,还是在网络中不断流动的信息,以及创造和使用信息的主体——人,都与传统的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所有政府在国际互联网治理领域应有平等的地位和责任”,国家拥有实施各自互联网政策的“主权权利”。[8]中、俄两国2016年6月签署的《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强调,“恪守尊重信息网络空间国家主权的原则……反对侵犯他国网络主权的行为”[9]。
两种主张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网络空间治理中无法绕过的话题。“多利益攸关方”“互联网自由”等广泛传播的概念,其逻辑起点都是对网络主权的全部或部分否定,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自由”同“网络主权”之间的冲突俨然已经开启了一场“数字冷战”。[10]不过,随着网络空间国家化趋势的发展,这种分歧至少在中、美两国间开始有所弥合。美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网络空间“部分受到主权控制”,[11]最多只能称为“不完全公域”,或是具有联合归属权但却缺乏完善规则的共同所有物。[12]曾任美司法部长助理的杰克•戈德史密斯也认为,互联网“反映了各个国家施加的影响”。[13]美国政府在近期的官方文件中也都避免将网络空间归类为“全球公域”,而是先后提出了“全球连接空间”(globally connected space)、[14]“共享空间”(shared space)[15]等术语。
要在“网络主权”问题上解锁,还必须形成更大的共识。一方面,这要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客观看待网络发展中国家的正当需求,接受适当的“权力让渡”,放弃追求、维护网络霸权的既有企图。另一方面,“网络主权”概念也有待进一步的细化、拆解,美国学者史蒂芬•克莱斯纳从四个层面加以解读的分析框架[16]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近期沈逸所提的“数据主权”[17]、郝叶力所提的“三视角”理论[18]等也都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笔者认为,或可尝试借用海洋的观念来看待网络空间,将其划分为完全归属一国主权管辖的“领网”、国家拥有部分权利的“专属经济区”和人类共用的“公网”,依据不同网络元件的不同性质划定其归属与政府权责。
治理首先要以恰当的体制机制为依托。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建立治理体系需要四个方面的“政治秩序”,即制定适应政策的职权、执行政策的法律规则、对违背法律规则者的惩罚机制和为掌权者提供制定决策、实施法规空间的管辖权。[19]其中贯穿着一个关键要素——“权”,即各种主体享有什么样的权力。在网络空间,该争论的核心在于政府权责,由此引发了在治理机制上的“多利益攸关方”与“多边主义”之争。
赞成“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多为美、欧等发达国家。他们认为,网络空间是在政府影响领域之外成长起来的,90%以上的基础设施由私营部门掌管,[20]公司、国家、跨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等各类利益攸关者的共同参与,是网络空间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的作用则被明显边缘化。这种模式走向极致,则是拒绝一切权威,以至于秉持“多利益攸关方”理念的互联网治理论坛(IGF),被认为值得肯定之处正是它缺乏决策制定权,因为这样它就不会做出错误的决策。[21]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互联网本身是分散的,但政府依然处于塔顶端,网络治理的主导权依然应归属于以政府为主体的多边机构。与前者相比,这种被称为“多边主义”的模式更强调“政府主导”特性,并以其高效性、易行性而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印度、巴西、南非(IBSA)多次建议,在联合国系统中成立恰当机构,以“协调和发展与互联网相关的、一贯的、完整的全球公共政策”。[22]2012年国际电信大会(WCIT)上讨论的新版“国际电信规则”,附有“所有政府应对国际互联网治理拥有平等作用和责任”的条款,遭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强烈抵制,但144个成员国中有89国最终同意签署。[23]
近年来,两种模式之争愈演愈烈,美国政府甚至在决定交出“互联网名称与编码分配机构”(ICANN)管理权时明确表示,只能将其移交给“全球多利益攸关体”,“绝不接受任何政府主导的或政府间国际组织获得管理权”[24]。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根本性矛盾。西方学者也认为,网络治理涉及技术标准、资源分配和公共政策3类要素,如果说前两者需要多种行为体共同决策的话,公共政策则是政府的传统职责范围。[25]在承认政府作用的前提下,两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有待协商的,只是在不同领域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主导权。
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必须认识到,“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之所以遭到抵制,是因为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看来,“在西方国家已经形成既得利益的互联网领域”,[26]现有模式仅仅有利于“北方国家”,他们自己则被排除在治理架构之外,其关切无法得到关注。[27]发展中国家强调政府主导的根本目的,是尽力争取在网络事务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正如时任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所说,“多边才能体现集体的力量”。[28]可见,“多利益攸关方”与“多边主义”之争,表面上看是对政府作用的分歧,实质上则源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和持续扩大。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增强网络实力,是弥合各方分歧,协力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的根本解决之道。
制定规则是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元素和最终途径,而其制定方式也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其核心,是网络空间能否适用既有规则的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行国际法体系的主要创建者,认为其在网络空间的适用并不困难。美国2011年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明确指出,“发展网络空间国家行为准则,并不需要创建新的国际法律习惯,也不需要废止现行国际规则。长久以来形成的用以指导国家行为的国际准则,无论是和平时期或是冲突时期的准则,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29]在早期,美曾以此为由,拒绝俄罗斯等国关于制定网络空间军备控制规则的要求,声称世界各国“还没有明智到坐下来建立新条约的程度”,因此只能依靠逐渐积累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找到在网络空间适用现有国际法的新途径。[30]其目的是秉持“先建设后谈判”的拖延策略,为自身网络实力建设创造尽可能宽松的环境。在近期,西方国家基于这一论调,迫不及待地推出尚不成熟的《塔林手册:国际法在网络空间战中的适用》,企图通过抢占网络空间战规则制定权,维护在网络空间的绝对军事优势。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网络空间是第一个由人建造的新空间,具有进入门槛低、行动隐蔽性强、难以溯源等与传统空间截然不同的新特点,现行国际法体系在其中难以适用。中、俄等国反复强调,应以其向联合国提交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为基础,以政府为主体,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协商,尽早就规范各国在信息和网络空间行为的国际准则和规则达成共识。该文件提出了维护信息和网络空间安全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是目前国际上就信息和网络空间安全国际规则提出的首份较全面、系统的文件。遗憾的是,中、俄等国的努力却被美国视为“旨在使政府有能力对网络信息的内容及流动施加控制”,[31]因而遭到有意的抵制与冷落。
与前两类分歧相比,这两种观点间的分歧更不显著。无论是创建新法还是适用旧法,都需要建立新的一套准则。近年来国际社会在网络规则制定方面的进展,无论是欧洲委员会2000年出台的《打击网络空间犯罪公约》,还是北约“卓越网络空间合作防御中心”2013年发布的“塔林手册”,都是重新制定一套法律的过程。在笔者看来,与其无休止地争论是否能适用旧法,不如将既有的法律原则作全面梳理,以考察哪些原则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哪些则具有先天缺陷,需要确立全新的法则。例如,“主权”原则的适用既有必然性又有必要性,否则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同推动制定网络空间国家行为准则”的共识,便会因政府管辖权的缺失而无法推进;反之,由于溯源问题难以解决,如将“自卫”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则有可能导致一国“基于怀疑”发起反击,无异于打开了网络战争的“潘多拉”之盒,导致国际法中禁止滥用武力的堤坝最终崩溃。[32]对于这样的传统国际法原则,就绝不可在网络空间加以适用。
网络空间治理的目标固然是多元的,但不同行为体出于各自的利益和关切,都会设定最优先目标。对美国而言,“网络自由”受到的关注度最高。互联网在设计建构之初,就将开放、互联作为首要考虑,这也使得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网络视作“自由”的代名词。借用普通民众对绝对自由的向往,美国政府一再宣扬其“互联网自由”理念。2007年美国会的《全球网络自由法案》、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的“网络自由”演讲,以及2010、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两次发表的“网络自由”演讲都反复表明,“全球连接自由”是美外交政策中的首要目标。[33]2011年5月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更加明确地强调“信息流通自由”的重大意义,将“网络自由”作为美国的政策方向,并对与其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大加抨击。
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家建构和身份认同,使得他们普遍将维护政府合法性、保持社会稳定作为更重要的任务。广泛普及的信息网络,既是这些国家达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的有力工具,也对他们的社会稳定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借助“推特”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因社交网站大量传播而加剧的伦敦“街头骚乱”,以及“推特”、“脸书”等社交网站在东欧“颜色革命”、中东“阿拉伯之春”和东南亚多国的政治风波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都给这些国家敲响了警钟。因此,他们多主张对网络实行一定程度的监管,要求在实施网络空间治理的过程中,要确保网络特别是网络信息安全。
这两者之间的分歧,既有理念与价值观上的差异,也有概念被恶意滥用而人为制造的矛盾。真正意义上的“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不仅不构成矛盾关系,相反是互为依托的。正如现实世界中,人们通过制定交通规则确保道路安全,基于道路安全保障自由驾驶一样,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信息安全”,实际上正是信息自由流动的根本保障。而他们所反对的“信息自由”,也只是不加束缚、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无限度自由,某些国家以此为工具达成干涉本国内政的政治目的。当前,抑制有害互联网言论的传播,已经成为包括若干西方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所推行的共同政策。2011年英国骚乱时期,卡梅伦首相在下议院指出,“我们正与警方、情报机构和业界密切协作,期望以此确定,在得知暴力、动乱和犯罪密谋的情况下阻止人们通过社会交媒体进行通信交流是否合适”。[34]“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互联网之敌报告2014》(Enemies of Internet)也显示,美国、英国“一直声称捍卫言论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民主国家,也在强化对网络内容的审查和过滤。[35]随着“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日益娴熟地利用网络进行宣传、筹集资金、招募人员,有效控制网络言论、防止网络恐怖主义泛滥,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为网络合作提供了新领域。
综上所述,当前各方在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上的诸多争议,有价值观和利益不同造成的根本性分歧,也有理解和表述差异带来的问题,有些是可以通过默契和利益平衡达成妥协的。[36]回顾历史,治理一词在国际关系中的广泛应用,始于1992年世界银行推出的《治理与发展》报告,基调是推动受援国政府采取措施,实现更好的发展。可见,治理是手段,发展才是目标。网络空间治理作为一种新兴事务,更是以促进网络良性发展为目标的探索。“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和“求同存异”的基本精神,在网络空间治理的实践当中依然具有指导性意义。与其在国际场合中拘泥于一些大而空泛的概念之争,不如努力将大争议化解为小问题,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实现突破,为网络空间的良性发展创造条件。
An Analysis on Critical Debates Regarding Global Cyber Governance
LV Jing-hua
Abstract: Despite the consensus about the necessity of global cyber governance,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obstacles in its process, including several critical debates on the nature of cyberspace, the governance model, the rule-setting principle and the aim of cyber governance. However, some of the different opinions are actually not as incompatible as imagined. It is both urgently necessary and practically possible to find common ideas and work together to enhance global cyber governance.
Key words: cyberspace; global governance; cyber sovereignty
(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吕晶华:籍贯河北石家庄。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学位。
参考文献
[1] Philip M. Napoli, Diversity as an Emerging Principle of Internet Governance, July 2008, p.5. http://www.fordham.edu/ mcgannon.
[2]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unis Agenda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5. http://www.itu.int/net/wsis/docs2/tunis/off/6rev1.html.
[3]鲁炜:《坚持尊重网络主权原则 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的体会与思考》,《求是》2016 年第 5 期。
[4] Daniel W. Drezner,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2,p.480.
[5] Sean Kanuck, Sovereign Discourse on Cyber Conflic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Texas Law Review, June 2010.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7756/is_201006/ai_n54718730/.
[6] United Nations, Glossary of Environment Statistics: Studies in Methods, series F, no. 67, United Nations 1997.
[7] Tara Murphy,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Commons, in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Summer 2010, p.30.
[8] Tom Gjelten, Behind the Cyber Disarmament’s Debate, in Army, March 2011, p.33.
[9]《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6年第 3 版。
[10] Min Jiang,China’s “Internet Sovereignty” in the Wake of WCIT-12,February 6, 2013.http://www.chinausfocus.com.
[11]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Pblic Affairs, 2011, p.143.
[12] Joseph S. Nye, Jr., Cyber Power, Harvard Kennedy School, 2010, p.15.
[13] Jack Goldsmith and Tim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Illusions of a Borderless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41.
[14]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ebruary 2011, p.5.
[15]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ebruary 2015, p12.
[16]网络主权可分为国内主权、独立主权、国际合法主权和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四类。前两者涉及各国政府对国内网络事 务的管辖, 是中、美等国共同认可的。 各方分歧主要体现在后两类主权上, 即是否将对方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 员,承认其享有独立处理网络事务的权利,可在不受外部干扰的情况下决定内部政治安排。具体内容参见: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沈逸:《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国际视野》,《中国信息安全》,2013 年第 10 期,第 39 页。
[18]《郝叶力:网络空间治理求同存异,“中国声音”获国际认同》,“环球网”2016 年 8 月 23 日,http://wap.huanqiu.com/MV8wXzkzNDQpMDRfMzcxXzE0NzE4ODQxMjA.
[19] Robert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 Rebecca Grant, Rise of Cyber War, a Mitchell Institute Special Repot, Mitchell Institute Press 2008, p. 16
[21] Social & Economic Factors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NSF/OECD WORKSHOP, JANUARY 31, 2007. http://www.oecd.org/internet/economy/37966708.pdf.
[22] IBSA Multi-Stakeholder Meeting o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Recommendations, 2011. http: //www.culturalivre.org.br/artigos/IBSA_recommendations_Internet_Governance.pdf.
[23]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Final Acts, World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Dubai, 2012,Resolution 3, p. 20. http://www.itu.int/en/wcit-12/Documents/final-acts-wcit-12.pdf.
[24] NTIA Announces Intent to Transit Key Internet Domain Name Functions, March 14, 2014, http://www.ntia.doc.gov/press-release/2014/nita-announces-intent-transition-key-internet-domain-name-functions.
[25] John Mathiason, Internet Governance: the New Frontier of Global Institutions, Oxon: Routledge, 2009.
[26][英]马丁 • 雅克著,张莉、刘曲译:《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年版,第 7-8 页。
[27] Internet Governance: Mapping the Battleground, a Report from Global Partners and Associates, 2013, p.4. http://apo.org.au/resource/internet-governance-mapping-battleground.
[28] “网络经济的未来——2014 夏季达沃斯论坛对话活动”, 新华网,2014 年 9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zhibo/2014dwslt_zb3/index.htm.
[29] The White Hous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 Prosperity, Security and Openness in a Networked World, May 2011,p.9.
[30] Phillip A. Johnson, Is It Time for a Treaty on Information Warfare? , in Michael N. Schmitt eds., Computer Network Attack and International Law,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2, p.439.
[3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ay 2013, p.37.
[32] Thomas Darnstaedt, Marcel Rosenbach and Gregor Peter Schmitz, Arming for Virtual Battle: The Dangerous New Rules of Cyberwar, in Spiegel Online, April 4,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expanding-combat- zone-the-dangerous -new-rules-of-cyberwar-a-892238.html.
[33] Speech of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January 21,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519.htm.
[34] Ronald Deibert and Masashi Crete-Nishihata,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Spread of Cyberspace Controls, in Glob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uly-September, Vol. 18, No.3, 2012, p.343.
[35] Enemies of the Internet 2014: Entities at the Heart of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March 11, 2014. http://rsf.org/en/news/ enemies-internet-2014-entities-heart-censorship-and-surveillance.
[36]方兴东、胡怀亮:《中美网络治理主张的分歧及其对策研究》, 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第一,“互联网+”立足于解决一些长期困扰消费者的问题,但客观上,也是在解决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促进产业的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最好手段。
第二,互联网行业不可能完全替代传统行业。“互联网+”是连接器、加速器,是数据管道、信息能源,帮助传统产业建立最大效率的连接,但是互联网行业在很多方面不能替代传统产业。产业融合提升了社会整体经济质量,并蕴含更多的经济机会,那些积极拥抱互联网又能深入到传统行业的新生公司,无论其来源背景如何,都将在产业融合的机遇中获益。
第三,“互联网+”是对传统行业基因层面和生态层面的改变。互联网行业里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一些商业模式、经营理念、运行方式、产品技术以及创新精神等,形成了所谓的“互联网基因”。“互联网+”,很大程度上,就是将这种基因注入传统行业,进行基因层面和生态层面的提升改造,产生大量全新的“商业物种”,以及新的商业生态和利益格局,并焕发出强劲生机。
第四,“互联网+”就是商业社会的“寒武纪”,我们这代人将见证众多新的商业物种的诞生。“互联网+”时代,产业融合不断催生新型业态,比如滴滴打车、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电视等,将不断涌现。商业物种的增加的积极意义在于,这意味着分工越细,生产效率越高,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社会化协作,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也能得到更多更充分的满足,并推动很多在传统条件下无法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第五,“互联网+”可能颠覆我们对生产组织、生产方式的认知。互联网让员工、合作伙伴和客户全流程深入参与,企业的运作方式、对成功的衡量手段以及绩效考核与奖励都要随之改变。未来的主流产业生态可能是以小团队、小企业紧密协调形成的集群,在互联的基础上,信息、材料、资金、人员在集群内快速流动,找到能充分发挥价值的最佳位置,发挥最大的能动性和生产力。
第六,“互联网+”将对公共政策不断提出新命题。“互联网+”正在改变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也必然会对既有法律、政府监管和制度设计能力提出挑战。法律政策环境是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保障,而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会推动制度创新。如何完善相关法律政策,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强调“互联网监管”的理念与思路。互联网监管强调的更多的是政府单方面的管理。我国目前互联网行业监管体系沿用了传统行业监管体系,主要强调市场准入监管,以准入为抓手,通过牌照等方式管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业态不断出现,并呈现出平台化、融合化等特征,既难以预见和穷举,也难以清晰界定和分类。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对互联网监管边界、监管目标和监管定位的认识存在诸多困惑与分歧。互联网业务多重属性日益突出,“齐抓共管”中部门间职责交叉大量存在,监管越位、缺位与错位问题不断。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进入传统行业后对传统行业和既得利益造成冲击,并与维护现状的法律制度发生冲突,使得“互联网+”面临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的困境。
面对互联网管理新局面,迫切需要转变思路与理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行业规章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种“包容性治理”的理念,对于因应“互联网+”带来的新局面非常必要。国际上“互联网治理”概念提出已久。2006年11月,联合国根据2005年11月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决定设立国际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互联网+”时代,我国需要实现由“监管”到“治理”思路的转变,并倡导“包容性治理”。具体而言:
第一,差异化监管。在监管过程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被监管对象本身的特点,尤其是面对新生“商业物种”的商业模式、经营方式等与传统不同,不能削足适履,强迫新事物符合旧的监管框架,而应在监管中鼓励创新,宽容试错。
第二,适度监管。凡事过犹不及,监管过度可能扼杀产业的创新动力,监管不足则可能导致市场秩序的紊乱,甚至危及产业的发展。由于“互联网+”进入传统行业后对落后生产力和既得利益造成冲击,并与维护现状的法律制度发生冲突,使得“互联网+”面临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的困境。若以工业时代的法律政策为准绳,今天很多没有实质危害性的创新事物,都难免带有灰色甚至“形式违法”的特征,此时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困境下,适度监管就成为“互联网+”治理的理性选择。
第三,柔性监管。近年来,寻求更多协商、运用更少强制、实现更高自由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很多国家都在考虑如何运用诱导的方式,促使监管对象能够自发地在竞争发展中注意风险的预防和化解,这促使了柔性监管手段的兴起和运用,使政府不但是执法者,而更像一个教练。
第四,内生性治理。与一味强调政府监管相比,“互联网+”更需要强调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和鼓励更好的商业模式,实现监管的目的。比如,出租车行业长期以来管制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服务质量和顾客权益,而打车软件的出现,提供了更优质、更廉价的管制解决方案。现在,无论是出租车还是专车,司机的联系方式、家庭背景等资料都被互联网详细备案,服务评价更为简单,投诉更有威慑力,司机改善服务的意愿更强,相比之下,延续至今百年的行业准入、专营制度显得笨重低效。内生性治理,就是在政策制定中主动发现、充分运用这种内生动力,实现治理的目标。
第五,多元合作治理。多元合作,强调治理不仅要包括政府管理,也更多包括行业自律、企业自治、消费者意识提高等等诸多因素。当然,企业的参与不在于承担政府职能进行相应管理,而在于发挥市场竞争的力量,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加强自治、自律和自觉。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平台责任制度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立法实践中,很多草案将原本由公权力机关享有的对违法行为进行认定、处理的职权,规定为互联网平台企业承担的义务(第三方义务)。比如,《广告法》修订、《食品安全法》、《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草案中,要求企业就其平台内的“违法行为”承担“发现-制止”的义务,否则需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
这种平台责任制度,固然可以降低监管成本和舆论风险,但会带来一系列后果。首先,行为是否“违法”,只能由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认定,企业不具备法定资格。其次,企业对他人采取“制止”行为,其后果很多时候与行政处罚大致相当,但是没有相应的程序和救济来保障用户的权益,即便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但是民事证据规则、证明责任等和行政诉讼中对相对人的保护也有很大差距。再次,违法行为认定标准复杂,平台缺乏专业人员、专业知识及技术手段,难以实现对于违法行为的有效认定,立法目的难免落空。按照该制度设计,监管机关可以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这样一个“抓手”,替代承担执法成本、法律风险和舆论风险,但必然对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对刚创业起步的中小型平台企业的冲击将更加明显。
第三方平台义务问题是当前各国互联网发展中普遍面临的问题,目前美欧日韩等国相关立法均未要求其承担极为严格的责任,仅要求其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即根据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而非赋予其直接监管的义务。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在互联网领域,也要努力形成政府、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用户、行业自律组织共同发挥作用的规则体系。“以网管网”,不是将管理责任由政府统管一切都推到互联网企业一方,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应当强调:1、善于利用互联网最新技术治网,搭建智能化监控系统,减少人力成本;2、善于利用社会化网络治网,引入多元合作的互联网治理新模式,开放参与渠道,共同发挥网民、互联网企业、行业自律组织以及政府的优势力量;3、提倡互联网思维治网,政府部门转变单向行政管理思路。
总之,应在立法层面建立科学合理、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平台责任制度,综合发挥网民、互联网企业、行业自律组织以及政府作用,多方参与,多管齐下,共同推进“互联网+”的发展。
(二)加强网络安全立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三个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提出要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立法。
国际层面,从2003年开始,美国相继发布其《网络空间国家战略》(2003)、《网络空间可信身份标识战略》(2011.4)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2011.5)。从欧盟来看,2005年,德国通过了其《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国家计划》。2006年,瑞典制定了其《改善瑞典网络安全战略》。2007年,爱沙尼亚在受到严重网络攻击后,于2008年发布了欧盟第一个广泛的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战略。目前欧盟已有10个成员国发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一些成员国正在制定其网络安全战略,部分即将发布。此外,部分成员国有非官方或非正式的网络安全战略。2013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其第一个欧盟范围的《网络安全战略—一个开放、可信、安全的网络空间》。此外,韩国、日本等国也纷纷发布其网络安全战略,阐述其网络空间的相关立场、主张及措施等。
我国目前尚缺乏网络安全的顶层设计,尚未发布《网络安全战略》。网络安全是“互联网+”时代的根本保障,我国也应尽快发布《网络安全战略》,加强网络安全顶层设计,完善网络安全相关立法,将网络安全问题法治化。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成为全球热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实践。在“国家主导,统一立法”的欧盟模式和“倡导自律,分散立法”的美国模式的影响及推动下,目前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目前没有制定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专门立法,散见于法律、法规、规章中,缺乏体系。此外,我国对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立法主要针对网络信息安全制定,其出发点在于网络安全。
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发挥大数据在“互联网+”行动计划中的作用,我国也应在立法中建立与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明确个人信息的监管机构与职责,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权利与义务,为大数据合理运用数据划清边界。此外,还应该切实提高个人信息保护的观念和意识,加强行业自律,推行行业个人信息保护宣言、建议、指南等。
(四)出台公共数据开放政策
大数据正成为继互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之后引起广泛关注的新概念,将像能源、材料一样,成为战略性资源。2013年5月9日,奥巴马正式签署并发布行政命令《政府信息公开和机器可读行政命令》(下称“行政命令”),为进一步推动公众创新活动、企业经济发展以及促进政府透明化和工作效率,政府将推动数据开放。作为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一部分,联邦管理预算局以及科技政策局同时联合发布了《数据开放政策》。2011年12月12日,作为欧盟2020数字议程的一项行动目标,欧委会通过了《公共数据数字公开化》决议。
纵观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开放政策,虽然历史不长,但发展十分迅猛,并且体现了以下几大特点:一,政府主动承诺,以政策和立法推动逐步开放数据;二,建立统一的政府开放数据门户网站,集中提供可直接利用的数据是通行做法;三,数据开放紧密围绕公共服务需求,民生类数据优先程度高。
我国至今还未推出相应的开放数据政策,而与开放数据相关联的数据所有权界定、授权、个人隐私保护等议题也都尚在讨论中。2015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明确表态,政府应该尽量公开非涉密的数据,以便利用这些数据更好的服务社会,也为政府决策和监管服务。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开表态支持数据开放。此前中国各级政府一些部门已在数据开放上有所尝试,但整体规则目前尚未明朗,如何界定数据的公共信息属性,是否构建统一的数据开放平台,以及数据开放过程中的透明化与公私合作关系,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也看作传统行业之一,那么它们本身也必然面临一个自身的“互联网+”的问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实现治理现代化,全面实行政务公开,推广电子政务和网上办事”,明确“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尽可能采用购买服务方式,第三方可提供的事务性管理服务交给市场或社会去办”。“互联网+”,不仅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持续推进民生改善的新途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互联网+政务”,可以助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针对目前电子政务普遍面临的信息孤岛、管理本位、应急响应不到位、利用率低等问题,可以移动互联网为平台,积极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深挖公共服务的创新潜力,在交通管理、在线审批、政务发布、舆情管理、内部办公、应急预警、污染举报等各类应用场景中为政府提供更加现代化、更加科学的政务管理手段,助力建设开放、透明、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互联网+民生服务”,可以助力实现智慧民生、信息惠民。以营造普惠化的智慧生活为目标,大力提升移动互联网在市民出行、看病就医、公共缴费、社保、旅游等民生领域广泛的普及应用,整合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升社会的整体效率和水平。
除了工具层面、器物层面的“互联网+”,公共部门不妨借鉴已根植于互联网企业灵魂中的“用户思维”,注重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用户体验”,据此设计、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并“快速迭代”,持续优化,以创新、合作、用户至上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赢得群众口碑。
因此,需要政策鼓励公共部门率先垂范,推动应用创新,深挖服务潜力。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充分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重视发挥智库作用”。
互联网企业智库诞生于互联网企业,根植于互联网行业,与行业实践紧密结合,能得到第一手鲜活的实践案例及经验。此类实践经验及案例是宝贵的研究资源,也是重要的决策参考。其次,互联网企业智库体制机制较为灵活。我国互联网企业智库成立时间不长,相比政府智库,体制机制较为灵活,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在“互联网+”时代,更容易捕捉瞬息万变的行业变化,迅速做出反应。再次,互联网企业智库在近年内也迅速完成了人才储备及专业训练,具备了建言献策的专业能力。因此,“互联网+”时代应积极发挥此类民间智库的作用,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吸收此类智库的研究成果,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Legislation and public policy of “Internet+” Era
SI Xiao
Abstract: As a whole the concept of "Internet+" which creates more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emerging formats means the innovative fusion between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t promotes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economic social fields. As well as other new concept, this concept is open and developmental. All walks of life are injecting and carrying out some deeper interpretations new content for this concept by practicing. No matter what the specific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are, "Internet+" was formally put forward on national level that means there is a common view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y. The basic, leading role and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Internet is rising. The innovative fusion between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industry will be the new point of economic growth. It will become the strategic emphasis, promo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mproving social management level and enhanc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under the new normal. "Internet+" opens a new chapter of the Internet on doing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Key words: Internet+; inclusiveness; policy; innovation
( 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司晓: 腾讯研究院秘书长、公共战略研究部总经理。
网络安全信息共享,顾名思义就是政府把关于网络安全的信息、情报、研判等分享给私营部门,同时私营部门将其受到威胁、攻击等有关信息报告给政府,以及私营部门之间互相交流与网络安全相关的信息。
美国被公认为当今世界网络技术和网络安全立法方面最为发达的国家,但近年来美国在网络安全立法上一直停滞不前。在第111届国会期间(2009—2010年),共有涉及网络安全的法案、决议案逾60件。在第112届(2011—2012年)和第113届国会(2013—2014年)期间均有逾40件法案、决议案。但直到2014年底,国会才通过四项法案。这也是顶着“互联网总统”称号的奥巴马自2009年就任以来,美国国会首次就网络安全通过了法案。
在这四项法案中,多是对既有法律的修正案、或者是对人员和机构等局部事项做出规定,唯一的一部综合性立法正是网络安全信息共享,以及建立个人数据泄露窃取事件的强制披露机制。原因是在美国,90%的关键基础设施为私人所有,美国法律又将这些私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责任放在设施所有人身上,而非政府。因此,美国政府增强基础设施安全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通过促进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公私合作,实现网络威胁的“群防群治”,同时借由事件强制公开,督促私人部门改进网络安全措施。这两个方面中,网络安全的信息共享是公认的重中之重。简单说来,美国《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2015》(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ct of 2015, CISA)主要是在法律上支持和规范了上述已经存在的信息共享制度。CISA授权国土安全部以新的“国家网络安全和通信整合中心”(National Cyber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s Integration Center,NCCIC),作为私营部门向联邦政府共享网络安全信息的主要接口。国土安全部随后将接收到的信息与其他相关联邦机构共享。此外,CISA要求国土安全部承担保护个人隐私和公民权利的义务,同时国土安全部必须提供一个自动化信息共享的机制。对私营部门来说,该法案最重要的影响是消除了组织机构之间自愿共享安全信息,以及与政府共享安全信息的各种法律责任风险。
在过去,大多数的组织机构对于维护自身的网络安全,抱着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高筑城墙,深挖护城河”相配合,组织机构的信息系统与其他组织机构的连接通道越少越好;信息系统的技术细节和安全防控布局要严格保密;一旦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必须严格控制分析、处置信息的扩散范围,越少人知道越好,更别提对外透露了。
许多组织机构满足于通过此种孤立的自我防御(即最大程度的“隔离”和“藏着、掖着”)的方式来追求信息系统安全。但这样的方式也导致了组织机构在开展安全防护工作时,只能依靠自己——极其局限的信息和情报、有限的人力和知识储备,因而无法有效应对网络攻击。
首先,孤立的自我防御导致的局限性,体现在防御和处置网络攻击、发现安全漏洞等方面。借用“杀伤链”模型,网络攻击可大致划分为七个阶段:侦查跟踪(reconnaissance)、武器构建(weaponization)、载荷投递(delivery)、突防利用(exploitation)、安装植入(installation)、通信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达成目标(actionson objective)。
真正的安全防范能力应该覆盖攻击者的每个阶段,安全信息共享可以让防御方在更早的阶段介入到防范工作中。例如,在实践中,许多网络攻击者对大量目标采用了相似的攻击工具和手法(即“杀伤链”前三阶段),因此通过共享网络安全信息,就能有效地分析、归纳得出关于攻击者、攻击工具和手法的信息和情报,从而为防御方在尽可能早地阶段地阻断“杀伤链”提供先机。
而孤立的自我防御下,由于掌握的信息和情报十分有限,组织机构往往只能在突防利用及之后的阶段,才具备检测、防御的技术手段和能力。显然,孤立的自我防御导致了防护工作的被动。
其次,孤立的自我防御导致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开展安全规划、部署等方面。缺乏相互沟通、相互借鉴,安全人员能看见、能分析的对象,只能是自家的系统,无法从其他组织机构经历的安全事件中获得宝贵经验,包括那些安全事件中涉及的漏洞、被攻破的系统的安全部署方案及采用的具体安全措施和产品、能够抵御攻击的安全措施等等。安全人员仅能从“小样本”中学习、改进,缺少从“大样本”中提炼出来的安全信息、情报、知识,安全人员无法准确评估哪些工具、技术、做法在应对特定威胁时最为有效。
极其有限、单薄、碎片的信息和情报,让组织机构的安全人员在决定购买、部署安全措施和产品时,只能依靠泛泛的一般性建议和教科书上通行的做法,甚至于道听途说和直觉,很大程度上困于“盲人摸象”的局面。
再次,孤立的自我防御无法应对快速变化的网络安全形势。一方面,网络和信息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在这样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单个组织机构的安全,越来越取决于其他与之相连的组织机构的安全,缺乏协同的防御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另一方面,近年来,网络攻守平衡逐渐被打破,攻击方的能力有大幅上升,例如分布式攻击(僵尸网络、DDoS)日益数量猖獗、漏洞黑市交易渐成规模、恶意软件和网络武器越来越复杂、网络犯罪组织化程度提高等。许多攻击必须在综合来自多方的信息后,才能被发现。因此,任何组织机构靠一己之力,已经无法对抗攻击。
协同式的安全,本质上是要汇集众智,以指导组织机构的每个安全决策和行为。因此,与孤立式的自我防御最大的不同,在于协同式安全非常注重对外的沟通和合作。如下图所示,组织机构内部除了监控自身网络、系统的部门,以及做出安全决策的部门之外,还专门设立合作部门开展对外的沟通合作。合作部门一方面把自身系统产生的安全信息和情报,与合作伙伴共享,另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将从外界得到的安全信息和情报,提供给决策部门参考、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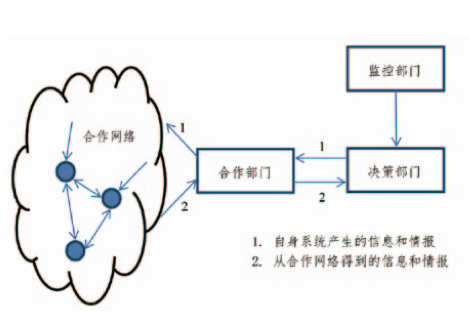
图1:合作式安全基本示意图[1]
形成与外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渠道、网络,能够给组织机构的安全防护带来什么样的好处?2014年10月,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发布了《网络威胁信息共享指南》(草案,编号:NISTSP800-150),以向社会征求意见。在《指南》中,NIST指出安全信息共享能够:
1.共享情景感知(Shared Situational Awareness):信息共享能够有效动员、发挥共享伙伴们集体的知识、经验、分析能力,因而能够增强所有组织机构的防御能力。共享网络中的每一成员能受益于其他成员的知识和经验。每一成员对共享网络的一点贡献,都可以提高整个共享网络对情景的感知和安全水平;
2.强对威胁的认知(Enhanced Threat Understanding):通过共享威胁情报,组织机构能获得对威胁环境更加完整的认识,从而能够根据威胁环境的实时变化,有针对性地设计和部署安全措施、检测方式等;
3.提升知识成熟(Knowledge Maturation):通过共享和分析,原本看似互不相关的信息和观测能相互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针对特定时间和威胁的指标,同时对指标之间的关系取得更深的认识;
4.提高防守灵敏度(Greater Defensive Agility):攻击方持续根据防守方的保护和检测方式,来修正攻击的手段、技术、过程(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TTP)。通过信息共享,组织机构能获得对攻击方TTPs的快速侦测、应对,使防御从被动变为主动;
5.改进安全决策(Improved Decision Making):通过信息共享,组织机构对安全态势获得了更完整、全面的认识。在做出安全决策时,更加高效,也更加自信。对单个组织机构来说,参与安全信息共享,能对攻击者有更多、更深的了解,缩短对网络攻击的反应时间;能够效仿别的组织机构部署的行之有效的安全措施,提高总体安全水平。[2]
美国学者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参与安全信息共享的组织机构,只需更少的投入,就能取得与没有参与信息共享的组织机构相同的安全水平。[3]原因正是,安全信息共享能够让组织机构聪明地做出投资决定,事半功倍。另一项针对金融机构的研究表明,随着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上升,安全信息共享能带来的好处就更多;同时,共享得越多,对安全的投资就越高效。[4]
事实上,除了提高组织机构安全水平,信息共享还能推动网络安全市场的健康发展。在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提出的“酸柠檬市场”中,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一方面买方难以分清商品的真正价值和好坏,另一方面卖方可以“安全”地夸大商品质量。此时,买方只愿意通过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来判断商品的平均质量,因此也只愿意付出平均价格。由于商品有好有坏,买方只愿意付出平均价格,就会使提供好商品的吃亏,提供坏商品的得益。于是好商品便会逐步退出市场。由于平均质量下降,导致平均价格进一步下降,真实价值处于平均价格以上的商品也逐渐退出市场。最后,“酸柠檬市场”就只剩下坏商品。
在很大程度上,网络安全市场中买卖双方间恰恰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例如,信息系统和网络没有发生安全事件,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分清到底是购买的安全产品和服务确实有效,还是因为没有被厉害的黑客盯上。缺乏安全信息共享,导致购买安全产品和服务的一方因“样本”信息过少,而无法准确地评估功效。网络安全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得不到纠正,就有可能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进而加剧买方对卖方的不信任。购买意愿降低,市场就会进一步萎缩,创新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对政府主管部门来说,组织机构间更大程度的安全信息共享,意味着有更多的安全信息和数据被“生产”出来,并开始流通。安全大数据得以成为可能。主管部门能借此在宏观层面,更全面地掌握威胁和安全防护方面的全局性情况,分析出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为在国家层面制定战略和行动计划、开展专项行动,有针对性地协调各部门、各行业进行防护工作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参与到安全信息共享中去,把自己掌握的情况通过共享网络做到快速、广泛发布,通过信息共享,达到调动、协调全社会实现实时的群防群治,提高网络安全治理的效果。
每一类的信息都具有潜在的用途。例如有些信息能够帮助政府主管部门或者组织机构评估所处的威胁环境,包括攻击者都有哪些、他们的规模和组织化程度、感兴趣的目标、希望达到的目的等。通过信息共享,综合大量的案例,并加以分析和跟踪,形成对攻击者行为模式、攻击成本的描述,最终形成攻击组织的画像(Profiling)。
有些信息经过共享、综合,则能够帮助组织机构重构单条杀伤链,分析攻击工具、攻击手法、攻击来源、攻击目标等特征。还有一些信息提供了应对某类威胁或攻击的指南。共享这类信息能够使组织机构相互借鉴,提高安全防护水平。2015年年初,美国微软公司发布《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和风险降低框架》(A framework for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risk reduction)。[5]在《框架》中,可供共享的网络安全信息可分为以下7类:
1.安全事件信息(incidents):关于成功的或未遂的网络攻击的细节信息,具体包括丢失的信息、攻击中使用的技术、攻击意图、造成的影响等。安全事件所囊括的范围从一次被成功封阻的攻击,到造成严重国家安全危机的攻击;
2.威胁信息(threats):包括尚未认识清楚但可导致潜在严重影响的事项;感染指标(Indicators of Compromise, IoC),如恶意文件、被窃取的电子邮箱地址、受影响的IP地址、恶意代码样本;关于威胁行为者(threat actors)的信息。该类信息有助于发现安全事件,从攻击中吸取教训,创造解决方案等;
3.漏洞信息(vulnerabilities):软件、硬件、商业流程中可被恶意利用的漏洞;
4.缓解措施信息(mitigations):包括修补漏洞、封阻或遏制威胁、安全事件响应和恢复的方法。此类信息一般以漏洞补丁、杀毒软件升级、从网络中清除恶意行为者的方向等形式存在;
5.情景感知信息(Situational awareness):此类信息包括对被利用漏洞、活跃的威胁、攻击的实时遥测,还包括攻击目标、网络状况等信息,能够帮助决策人员响应安全事件;
6.最佳做法信息(Best practices):关于安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部署的信息,包括安全控制、时间响应流程、软件漏洞修补等;
7.战略分析信息(Strategic analysis):综合、提炼、分析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以构建度量体系、描绘趋势、开展预测,帮助政府和私营部门决策者为未来的风险提前做准备。
《网络威胁信息共享指南》给出了安全信息共享网络的三种基本结构:集中式(centralized)、同侪式(peer to peer)、混合式(hybrid)。[6]
在集中式下,中心从端点接收安全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后,再将结果传回端点。一般来说,集中式的中心需要具备强大的信息存储、处理、加工、分析能力,才能满足信息共享网络的不断变化的需求。该模式的缺点是,整个信息共享网络依赖于中心作为安全信息交换枢纽,如果该中心发生信息处理延迟,甚至遭遇安全事件,整个信息共享网络的功能会大打折扣,并有可能完全瘫痪。
在同侪模式下,每个端点自主向其他端点推送网络安全信息,或直接向整个信息共享网络广播。由于不存在一个信息交换中心,因此同侪模式对各个端点的安全信息接收、分析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混合式则综合了集中式和同侪式。每个端点向中心发送安全信息的同时,端点和端点之间也建立直接的信息共享渠道。
构建安全信息共享网络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是自动化分享模式和人工共享模式的选择。人工共享模式下,组织机构指派专人负责安全信息的发送和接收、分析工作。该模式的缺点在于人的因素构成了信息共享网络的瓶颈,如人为导致的错误,无法胜任实时、持续性、高强度的信息发送、接收、安全配置更新工作等。
自动化共享模式则强制要求信息共享网络的各个端点采用统一的信息传输格式,安装用于收集安全信息的传感器,能够接收预警信息的监控系统,以及避免敏感安全信息泄露的安全机制。自动化共享模式克服了因人的因素造成的局限,但其高度的自动化却也导致其遭受网络攻击的风险。
上文介绍了协同式安全理念的兴起、安全信息共享带来的好处、共享的安全信息的分类,以及共享网络的基本结构和信息传递方式等,主要属于一种抽象式、理论化的描述。现在让我们进入到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去,探究如何建立一个有实效、可持续、有序的安全信息共享机制。归纳实践,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有四类信息共享网络:成员驱动型、数据驱动型、事件驱动型、风险驱动型。
成员驱动型:例如美国覆盖重要行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分析中心(ISAC),包括金融服务、通信、电力、应急服务行业、医疗和公共卫生、信息技术、海事、公共交通、教育、供应链、运输、水利以及房地产等。每个ISAC的成员主要来自于同一个行业。
数据驱动型:例如采用统一的传输格式或工具自动共享网络安全信息的网络。其中类型的典型是由美国电力行业的信息共享与分析中心(ES-ISAC)运营的网络风险信息共享计划(Cybersecurity Risk Information Sharing Program, CRISP)。在该计划中,ES-ISAC帮助参与成员在各自网络中安装传感器。传感器自动将加密后的数据传输到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PNNL)。PNNL在对数据开展分析后,对参与ES-ISAC的成员发出预警,分享缓解措施。在这个例子中,ES-ISAC帮助参与成员安装统一的传感器,这样就首先保证了各成员大致具有相似的安全事件发现能力;其次,所有数据均由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来统一分析,也就克服了成员分析能力不同的障碍;同时,ES-ISAC采用的是集中式的信息共享网络,且由政府部门下属的实验室作为网络的中心,中心对信息进行了“脱敏”处理,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遭遇安全事件的成员面临声誉和经济受损、泄露内部安全部署等风险。
事件驱动型:该类型的信息共享网络主要为解决特定的事项或问题而建立。网络中各成员的共同点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例如为解决千年虫问题而组成的信息共享网络。此类型的信息共享网络仅仅关注单一议题或问题,成员大小不一,所处行业各异,且组织较为松散,因此对成员的发现和分析能力要求不高,网络中共享的信息范围有限(主要围绕特定的事项或问题)。这些特征造成信息共享网络面临的障碍不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此类信息共享网络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风险驱动型:该类型信息共享网络围绕着特定系统或生态的安全研究而建立。共享网络中的成员来自与特定系统或生态相关。例如专门为智能汽车的联网安全而建立的信息共享网络,网络中成员可来自与智能汽车相关的方方面面。与事件驱动型信息共享网络类似,此类型信息共享网络面临的信息共享障碍不大,各成员之间分享某一系统或生态的漏洞、攻击方式等,共享的信息比较单一。其中涉及的主要风险是共享的信息可能泄露知识产权和商业信息,主动分享的组织机构可通过进一步自我审查,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该风险。
基于上述四类信息共享网络,我们看到从纸面上的设计,映射到现实中的制度建设,再到运行流程的信息共享网络,主要是要消除以下三类运行障碍:
障碍之一:成员的发现能力
显然,不能发现网络安全事件,后续的分析和共享也就无从谈起。如果信息共享网络中的成员发现安全事件的能力高低差距明显,将会直接导致大部分共享的信息,主要由发现能力强的成员单方面提供。长此以往,信息共享网络的价值和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在建立信息共享网络中,往往要对入网的成员提出具备一定安全事件发现能力的要求。
光具备发现安全事件的能力还不够。如果有成员考虑到共享的成本、风险等原因,刻意隐瞒发现的安全事件,不将有关信息共享出来,“搭便车”的问题还是没法解决。因此,信息共享网络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或是通过激励(incentives),或是通过强制(mandates)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障碍之二:成员的分析能力如果信息共享网络中的成员仅仅是把与安全事件有关的各种信息全部共享出去,而未加任何分析,显然会造成整个共享网络信息过剩的问题。面对大量的“杂音”,信息接收方需要自己开展过滤、分析,工作量大幅增加的同时,“收获”却寥寥无几。这样的信息共享网络终将不可持续。因此,许多信息共享网络会要求成员应该首先对安全事件作出分析;有些信息共享网络还专门列出指导分析安全事件的几类问题:
1.安全措施的影响:系统发生安全事件时使用了哪些安全措施,为什么这些措施不足以防御威胁入侵?哪些安全措施可能能够防御此次威胁入侵?安全事件发生后,系统对安全部署和防御做了哪些调整?
2.入侵发生的根本原因及第三方因素:系统的软、硬件、服务中的哪些因素(例如配置或漏洞)使得入侵得以成功?是否有第三方的因素使得入侵得以成功?
3.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及后续清理:安全事件造成了什么损失?(金钱、信息泄露、服务中断等)采用了何种止损措施?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对所有这些问题分析的结果都要共享出去。因为对其中很多问题的回答,往往包含了成员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私有信息。列出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发生安全事件后,成员应当试图从这些方面做出分析、得到初步答案后,再将部分结论共享给其他成员。至于哪些信息需要共享、哪些信息可以保留,主要根据信息共享网络的目的,以及信息共享网络成员间的相互约定。
障碍之三:共享的风险
共享网络安全信息,一定程度上是向外界透露关于组织的安全信息,存在各种风险。举例说明如下:
1.声誉和经济受损的风险:遭到黑客攻击,本来就是不光彩的事。防住了还好,没防住还要将有关情况共享出来,好比是家丑外扬。如果这些信息泄露到信息共享网络之外,全社会都知道了,组织机构的声誉将受重大损失,还可能造成股价的下跌;
2.被起诉或被主管部门问责处罚的风险:被外界知道没能防住黑客攻击,造成经济损失或者信息泄露,有可能被有关权利人起诉;
3.泄露内部安全部署的风险:别有用心的人可以从共享出去的网络安全信息中逆向推导,借此掌握组织机构的内部安全机制和部署;
4.泄露知识产权和商业信息的风险:共享出去的网络安全信息中有可能包含组织机构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信息;
5.违背顾客、用户的隐私保护的风险:网络安全信息中如果包含组织机构掌握的顾客、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通讯信息等,共享出去可能会导致顾客、用户认为组织机构违背信息保护约定,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6.与政府主管部门共享信息存在风险: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可能因组织机构没有尽到安全保护义务而问责或处罚;其次,顾客、用户不愿意政府部门掌握其信息;再次,共享到政府的信息可能受到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的约束,向社会公开;
7.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风险:例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组织机构共享网络安全信息的行为,有可能被当成垄断行为,引来反垄断机构的调查;
8.安全信息被二次使用的风险:安全信息一旦共享出去,就离开了组织机构的掌控;获得信息的一方会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无从保证;竞争对手会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更难以防范;
9.信息真实性存疑的风险:组织机构可能担心,即便自身克服这些风险,与其他方面共享了网络安全信息,别的组织机构会这么做吗?它们会不会故意提供错误的信息;
10.国家秘密泄露风险:政府向组织机构共享其掌握的网络安全信息,如果信息扩散范围失控,则有可能导致国家安全风险。这些客观存在的法律、声誉、经营方面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组织机构(或政府部门)更愿意对安全事件的信息藏着、捂着,因此阻碍了网络安全信息的共享。
Creating an orderly mechanism of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HONG Yan-qing
Abstract: In China,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is officially treated as one of the basic measures to address cyber threats. However, we still lack a systematic account on what benefits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would bring, how security model and thinking will have to change resulted from implementing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how to make information sharing work in practice, and what are the major obstacles. This article aims to fill in this gap. By providing responses to these basic questions, this article hopes to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of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so as to increase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it.
Key words: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collaborative security; basic model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洪延青:四川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士和硕士,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标准。
参考文献
[1] GuozhuMeng, Yang Liu, Jie Zhang, Alexander Pokluda, and RaoufBoutaba. 2015, Collaborative Security: A Survey and Taxonomy. ACM Computing Surveys, 48(1):1.
[2] 见 V. B. Chang, D. Kim, H. Kim, J. Na, and T. Chung, “Active Security Management Based on Secure Zone Cooperation,”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 20, no. 2 (2004): 283
[3] L.A. Gordon, M.P. Loeb and W. Lucyshyn, “Sharing Information on Computer Systems Security: An Economic Analysis,”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22, no. 6 (2003): 461-85.
[4] L.A. Gordon, M.P. Loeb and W. Lucyshyn, “Sharing Information on Computer Systems Security: An Economic Analysis,”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22, no. 6 (2003): 461-85.
[5]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45516
[6] 另见“Cyber Information-sharing Models: An Overview,” MITRE, October 2012,http://www.mitre.org/sites/default/files/ pdf/cyber_info_sharing.pdf
21世纪是互联网的世纪,也是太平洋的世纪。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国。[1]基辛格(2015)[2]认为,中美两国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会导致两国的竞争,还将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这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客观,理性,历史”的观察视角是关键。
首先,要求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基于不同立场与利益,对于中美关系有不同、甚至完全立的结论,这都不足为奇,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所能准确诠释。
其次,要求理性地看待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既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又远远超越了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对中美关系的研判,必然涉及对中美各自经济制度、政策、发展,乃至政治、文化、社会的综合研判,因而,中美竞合的主战场不在国际舞台,而在国内经济。中美外交军事竞合的背后是经济的竞合。
再次,要求历史地看待中美关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同盟到“9•11”之后的全球反恐,以及2008年之后应对全球金融海啸,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历来中美合作则双赢。
但是,随着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围绕修昔底德陷阱[3]的争论,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应加强合作,实现双赢的未来。基辛格、李光耀、蒙代尔、斯蒂格利茨、萨金特……无论是政治明星,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有人在。斯蒂格利(1999)[4]一直对中国经济前景寄以厚望。
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应加强合作,实现双赢的未来。基辛格、李光耀、蒙代尔、斯蒂格利茨、萨金特……无论是政治明星,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有人在。斯蒂格利(1999)[4]一直对中国经济前景寄以厚望。
美国《华尔街日报》(2004)[5]对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问卷采访显示,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看好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科斯认为中国将在75年后超越美国和欧盟,马科维茨认为美国的“自由市场”是最好的政策,其次是中国,格兰杰认为75年后的经济实力排序应当是美国、中国和欧盟,索洛认为中国按经济总值算第一,按人均第一是美国。对于观察者而言,世界头把交椅何时在中美之间交换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话题。但是,对于来自中国的学者,似乎并不关注中国是否超越美国,研究的重点落在中美是否成功携手实现和平共处。黄卫平(2012)[6]认为中美应该、且能实现双赢的未来。金灿荣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是绕不过的坎。[7]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难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竞争必然导致冲突。在此观点之下又形成了种论调。第一种论调是“中国崩溃论”,2001《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走俏欧美市场,该书断言“中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最只能维持5年。”十年过去了,所谓预言变成谎言。2011年章家敦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发《中国即将崩溃:2012年版》,断言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中国经济将陷入日本式持久经济衰退,甚至崩溃。第二种论调是“中国威胁论”,主张美国围堵、打压中国,通过缔结军事同盟,鼓动中国周边国家在南沙、西沙、钓鱼岛与中国直接对抗。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似乎也反映了这种论调。2009年国情咨文中提到四次中国“威胁”、四次中国“挑战”,2010年提到三次“挑战”、一次“威胁”,2011年提到三次“挑战”,2012年提到四次“挑战”、四次“威胁”。
对于中美关系并不需要统一认识,不同的观点恰好体现了21世纪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的特点。“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也不会造成真正的威胁——这些论调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已有30多年历史了。如果愈是在意它,愈是企图封杀它,那么这些观点就愈有市场。
中美关系难免不受到各种杂音的干扰。但是正如人类的理性最终会战胜感性,对于中美关系的理性态度一定会占据主流。中美关系从来不会随心所欲发展,三大因素共同决定中美关系的运行轨迹。即:(1)世界政治经济格局;(2)中美共享式发展;(3)中西文明在碰撞中融合。
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美苏两级冷战格局宣告结束。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了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格局,一方面越来越分散化、多极化,另一方面越来越紧密化、越来越全球化。前者是由于以中国为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后者是由于世界正在互联网化。进入21世纪以来,宽带、4G、移动终端、云计算、大数据共同颠覆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与商业模式,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新特点体现在:
(一)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冷战结束以来,以美欧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并形成以美国为单一引擎的单循环世界经济体系。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世界经济格局力量发展转变的起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剪羊毛”现象[8]被发展中国家普遍诟病,要求改变与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
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股灾及在阿富汗、中东持续的地缘冲突升级,从另一个层面让以中国为首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的新兴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助推器”、“推动器”。201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中,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比重达到51.6%,首次超过50%;2012年全球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占全球GDP总和第一次超过全球GDP的50%;2012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3年1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2013年预计全球GDP增长率为3.5%,发达经济体预计1.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5.5%,世界出现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不平衡,即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明显慢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再次冲击世界经济秩序,为了化解危机,1999年在德国柏林设立G20峰会,该峰会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十二个新兴经济体组成。G20峰会的成立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5年,美国GDP相当于资本主义世界的60%。2013年,金砖五国[9]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93%,其中仅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达到美国的54.6%。中国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储大国与贸易大国。
表1:金砖国家2013年GDP占世界总量比重

2016年6月7日,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今年1月份预测的2.9%下调至2.4%;新兴经济体国家预计增长3.5%,其中,2016-2017年中国增速预期分别为6.7%和6.5%,印度增长预计分别为7.6%和7.7%。由此可见,尽管增长放缓,但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超过全球平均经济增长1.1%,依然是全球经济重要的推动力。
(二)全球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互联网+”超越科网股泡沫陷阱成为新经济领头羊
1999-2000年,全球股市曾迎来一波疯狂的科技网络股行情,千禧之年庆典的余温还在,全球股灾就已经发生了。2000年3月10日,NASDAQ指数到达5048.62高点。随后,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最低跌至1108点。全球互联网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股市泡沫不能阻止互联网发展的步伐。当一部分人谈“网”色变之际,另一部分人却开始了互联网创业。以美中为龙头的互联网创新者、创业者正在行动。2015年美国《商业内幕》FACEBOOK、微软、苹果、IBM、谷歌等16家互联网科技公司入围全美最具影响力的前50家公司之列。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华为、阿里、京东、乐视、联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骨干企业。2015年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前20强排名,美国以11家占首席,中国以6家占次席。
美国互联网高科技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对2010年9月30日-2016年6月13日同期纳斯达克指数(图1)与道琼斯指数(图2)的走势进行比较显示:1、道琼斯指数从10318.68点上至17732.28点,上涨幅度为72%。纳斯达克数从2235.16点上涨到4826.37点,上涨幅度116%,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幅明显超过道琼斯数;2、鉴于纳斯达克主要覆盖美国互联网高技公司,两大指数同期涨幅的差异从一个侧面示美国互联网高科技行业的增长大大超过传统业的增长。

图1:纳斯达克指数走势(20100930-20160613)数据来源 : 新浪财经[10]

图2:道琼斯指数走势(20100930-20160613)数据来源 : 新浪财经
中国互联网高科技经济发展势头同样喜人。2016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态势暨景气指数报告》[11]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上市互联网企业总营收达7500亿元,同比增长46.6%。2016年一季度,中国互联网发展先行指数、一致指数、滞后指数分别为105.9、105.8、105.1,环比分别提升0.25、0.91、0.86个点。景气指数测算表明,中国互联网行业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截至2015年12月,全球网民数量达到31.74亿接近全球人口数的50%,中国网民数量达到6.88亿,历史性地突破了人口数的50%。[12]人类社会正在全面步入互联网时代。
对比科网股泡沫破灭前后两个阶段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在科网股泡沫破灭前,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在科网股泡沫破灭之后,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他行业的发展。互联网与其他行业结合,创造新的通讯方式、新的阅读方式、新的购物方式,及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互联网+”。
随着美国信息技术革命、德国工业4.0、中制造2025的推进,从工业文明到互联网文明人类历史第三次浪潮正在波澜壮阔地展开。在联网平台上将不同时代的文明、以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明重新洗牌与组合,将人类文明的“资源”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更有效的配置,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力、以及澎湃向上的推动力。人类文明正在进入互联网文明时代,互联网文明不是对人类既有文明的否定,而是“互联网+人类文明”,呈现创新与加速发展的态势。互联网不仅堪称技术革命,而且堪称文明革命。
综上所述,世界格局出现了新变化,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出现了互联网革命。国际大背景更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
中美经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旅游、文化交流对两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中美合作是双赢的选择
中美合作是双方民间、企业、政府利益最大化的选择。首先,从民众的生活观察,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使美国民众得到了很大实惠,降低了美国家庭消费成本,间接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沃尔玛商场等美国品牌也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次,从企业层面观察,美国进口中国产品拉动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中国市场也是美国企业海外利润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再次,从宏观经济观察,中美合作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促进了就业、增长、城市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中国购买美国国债,降低了美国利率,使美国深受其益。
(二)中美贸易投资互为依存
中美贸易依存度与投资紧密度日益上升。在贸易方面,2015年美国从中国、加拿大进口货物金额分别为4818亿美元与2951亿美元,中国已经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3]在投资方面,尽管中国从来都不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目的地,但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迅猛,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135亿美元,同比增长60%~70%。2015年,中国在美国的收购、新业务和扩张已经增加到逾150亿美元,比2014年上升近30%,创纪录新高。2015年底,在美的中资关联公司数量超过1900家,被中国相关公司雇用的美国人的数量上升了12%至9万人。[14]
(三)雁型模式与温特制将中美产业捆绑在一起
首先,中国通过雁型模式成为“世界工厂”。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的经济跑道上演着产业跨国转移的接力赛。参赛队员依次是:发达经济体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即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东盟四国,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中国、越南等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以阶梯式产业转移为特征的雁型模式中,引领雁阵的雁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美国手中夺过“世界工厂”桂冠的日本。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从日本手中接过“世界工厂”的接力棒。在东南亚经济体的生产体系受到重创的情况下,美国的订单落向了中国。而当时中国自身的生产能力不足以完成海量的订单,怎么办?华尔街发挥了金融的基本功能,外商直接投资纷至沓来,带来了资金、设备、技术,于是中国成为了新任“世界工厂”,从此嵌入全球产业链。中国过剩产能的形成、经常账户的顺差,以及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客观上也与美国垄断资本全球配置资源有关系。
其次,美国通过温特制成为全球产业的火车头。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标准为核心的温特制新型国际生产方式逐渐形成,温特制下的全球生产网络以跨国公司为载体,新产品一旦投入市场,必须依靠跨国生产体系,迅速完成全球市场扩张。20世纪90年代,美国按照温特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且政局稳定的中国成为该生产体系的委托加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 )基地,在温特制下真正掌握全球经济发动机钥匙的是美国,OEM是跨国公司的附属,生产什么要根据跨国公司的订单,如何生存要采用跨国公司的技术与标准,开始生产要依靠跨国公司的资金支持,生产出的产品要依托跨国公司的销售渠道。
(四)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
中美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文化体。中国承载着东方文明,美国承载着西方文明。两种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差异,同时也有着更多的共性。
虽然美国建国历史不长,但是,美国作为西方文化守望者与传承者,与上下5000年的中国文化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中美对自己的文化不仅具有自信,而且互为欣赏。在中国近代这段苦涩的岁月中,只有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与老牌西方列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愿意把赔款用于兴建大学。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共同打败了日本法西斯。
中美民间在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流。美国是海外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家。美国是中国学生海外留学与游学的首选目的地。
《2016国际游学白皮书》显示,美国是最受中国人青睐的游学目的地国家。在参加过国际游学的人群中,51.2%的中国人选择美国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在尚未参加过游学,但有意愿游学的人群中,也有57.9%的中国人将美国作为自己的首选目标。
迄今,中美已经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民间交流渠道。其中,2010年正式成立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是中美合作的重要平台,2016年6月7日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共签署12项合作协议,达成涵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妇女及青年等领域共计158项成果。
综上所述,中美合作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产业结构互补、经济互为促进是中美合作的基础,文化交流与民间往来是中美合作的润滑剂。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合作的基础坚实,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5]建立以来,战争来都是新兴国家与传统国家竞合的宿命。随着世纪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大国之间能否打破修底德魔咒,这不仅考验着两国政治领袖的智慧而且也是衡量中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标准。
(一)西方传统的文明观倾向冲突论
冲突论认为竞合的结果必然导致战争,战是政治的继续。主要包括如下三种类型的冲突。
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冲突。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话,成为了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他强调,国家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殖民与对外扩张的动力,把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是现代国家的特点之一。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共同构成国家利益的有机整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全面的国家利益观。
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冲突。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反苏说,被称之为铁幕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公开攻击苏联,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呼吁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
再次,是文明的冲突。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6]一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美苏冷战以来,决定世界格局的是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还有非洲文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决定世界的走势。
(二)中国传统的文明观倾向和平论
与西方冲突论截然相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认同“自然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先哲们就阐述了和谐与和平的理念。《论语》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老子提倡“道法自然”,主张社会和谐。
董仲舒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在此基础上成的治国理念,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从自然和谐到社会谐,到国家和平,再到世界大同”的发展史,“求存异,和平共处,和谐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治国理念的现代表达,这也构成了当代中国处国际事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内涵。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尊重文化多样性四项原则。[17]这四项原则分别是,一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二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三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四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习近平主席引用了“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形象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论。综上可知,中西对于文明冲突的研判不同。
西方的冲突论与中国的和平论之间存在差异,中西文明碰撞过程也是文明交融的过程。尽管难以预期碰撞持续的时间,但是,可以断言,西方冲突论与中国和平论点碰撞的结果必然是人类理性占据上风,和平论取代冲突论成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普世价值与准则。
之所以得出如此肯定的结论,是因为西方精英阶层对于冷战的认识回归理性。1989年在苏联解体之前,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并预言西方会在冷战中胜出,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最终形式和最高阶已经得到历史的确认。“历史的终结”不仅被随后的历史发展所应验,而且成为西方对冷战理论总结的共识。
对于福山“历史的总结”,在西方一直存在争议。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瓦希(2011)[18]认为,历史终结论完全是一种傲慢和轻率的反映。郑永年(2015)[19]认为,历史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历史是终结不了的,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并在世界各地酿成灾难后无法收拾。
值得庆幸的是福山的思想也发展了翻转。近20多年以来西方经济连绵不断的危机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强烈反差促使西方理性的学者反思。2012年福山用《历史的未来》修正了《历史的总结》的观点,他认为支撑自由民主的中产阶级正在衰落,西方在意识形态上走进死胡同,呼吁反思西方自由主义,批判所谓自由市场与小政府的理念,改革社会和政治体制。
从“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的未来”也反映了西方知识阶层对西方民主的反思。这种反思不是对西方民主的否定,却能破除对西方民主的迷信,引导西方民主制度回归理性、包容发展的轨道,这种转变在国际关系领域必然推动冲突论向和平论靠拢。
世界因素、中美因素、文明因素共同确定了中美关系运行轨道。随着中美经贸合作、文化往来不断深化,中美关系升级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命题被提了出来。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20]2014年11月,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再次从6个重点方向阐述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原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代表着用新思维、新眼光、新角度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国际舞台是国家利益博弈的舞台。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也是中美双方博弈的过程。博弈的结果与策略的选择有关,策略的选择与对角色的定位有关。对于21世纪互联网时代中美两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博弈分析的结论是:
(一)中国对在中美关系的角色有着清晰的定位
“不冲突、不对抗”的核心是和平,“相互尊重”的本质是平等,“合作共赢”的要点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冀望新型大国关系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明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破修昔底德魔咒,抛弃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相互猜疑、对抗、冲突的宿命,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和平共赢的新路。
(二)美国对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存有模糊
与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清晰角色定位比较,有时显示出对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视,有时又做出不利于中美长期稳定合作的事情,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态度暧昧,甚至不积极。美国官员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极少主动谈到“新型大国关系”,而且含义与中方所表达的似乎也有所不同。这种差异耐人寻味。[21]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认为,美国接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种说法不重要。[22]
显然,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在政策上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国内对抗论有市场,单边主义色彩突出,未放弃拿意识形态分歧说事;在亚太事务中,鼓动菲、越在南海问题上纠缠不休,怂恿日本非法盘踞钓鱼岛,这些都表明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依然未放弃山姆大叔惯用的“胡萝卜”+“大棒”。“胡萝卜+大棒”政策针对小国或许有效,针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必然无效。
(三)互联网有助于防范中美擦枪走火
中美都是互联网大国。截至2015年,中国网民超过人口总数一半,美国网民接近人口总数85%,互联网将中美每个角落广泛的连接起来,汇集各方言论与智慧。虽然网络言论难免夹带民粹主义与极端倾向,但是网络的普及化利大于弊。中美贸易、投资、金融、文化、教育、旅游被网络更密切地连接在一起,形成维护中美合作共赢的正能量,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互联网一方面消除了因信息闭塞导致产生法西斯主义与专制集权的土壤,另一方面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引起大国冲突的概率。
当前,美国掌握着几乎所有互联网核心技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市场,中美两国在互联网领域合作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在互联网时代,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多层次、广泛的沟通交流渠道。虽然中美由于国情不同,两国在互联网安全等问题上存在认识分歧,但是,正如路易斯所表示,美国需要意识到现在的互联网是世界的互联网,需要新的全球管理,而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在网络空间,彼此尊重对互联网治理模式的选择,这是中美网络合作的方向。
基于对中美在中美关系中角色定位的判断,尝试建立中美大国博弈模式。在此博弈模式中,用中美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代替博弈的策略。
表2:中美大国博弈三种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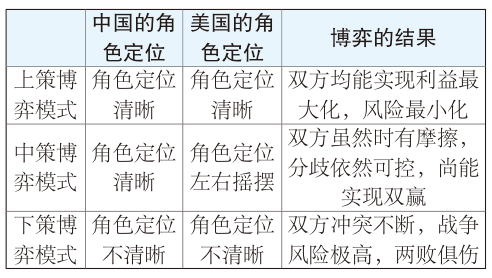
中美博弈存在三种模式,但选择何种模式是“既定”而非“随意”,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当前中美博弈选择的是中策博弈模式。这虽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不是双方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却是现实的选择。双方摩擦与分歧难免,却可控。在贸易、投资、金融、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能谋求共享式发展。
其次,中美博弈从中策博弈模式升级到上策博弈模式。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这种转变不仅需要政治家的智慧,需要扩大双方共同利益,需要加强沟通与协调,更需要调整好心态与推动文明的融合。没有时间句号的漫长过程其实佐证这种理想模式不过是国际关系中的乌托邦。尽管如此,理想总是一把标尺。如果美国也能像中国那样清晰定位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那么,双方一定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随着美国在中美关系中角色定位的日渐清晰,相信中美关系能更加平稳、更加健康。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关系依然长期看好,大有潜力可挖。
再次,中美博弈从中策博弈模式滑落到下策博弈模式。对于中美关系,中国的原则是“上不封顶、下要保底”。“上不封顶”就是说中美合作越多越好,“下要保底”就是说两国不能有冲突,不能打冷战,不能打热战,更不能打核战。加之,由五千年文明滋养起来的、致力于和平的中国,文化中没有侵略扩展的基因,中国清楚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与目标,就是想让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好一点、世界和平更多一点。对于美国而言,英国丢掉世界霸权的案例摆在面前,两强对抗必然两败俱伤。恰如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以战败告终,
利的一方英国也大伤元气,被迫将世界霸主拱让位美国。在战与和之间,理性选择是后者。此,中美关系断然不会滑落到下策博弈模式。
中国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策略,对内注意防范民粹主义泛滥与激进思想横流,对外回避中美矛盾,也不激化中美矛盾,采用更加灵活多变的策略应对中美之间的竞合与博弈,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中美要建立管控分歧的机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与利益不尽相同,分歧存在难以避免。有分歧的中美关系,反而是真实的中美关系。有了分歧并不可怕,关键是中美应以负责任大国的理性态度看待分析,勿让小的分歧酿成大的冲突,以务实的态度建立中美对话沟通协调机制与管控机制,坚持求同存异,中美两国关系就能避免受到大的干扰。
第二,中美要倡导换位思考的文化。一方面美国应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勿对中国的人权、民主妄加指责与干涉;另一方面中国应冷静看待中美关系的不和谐杂音,美国国内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对于部分政客在中美关系中的极端言论,不仅没有必要针尖对麦芒,反而应以“有容乃大”的大国气度化干戈为玉帛。另外,也应给予美国在历史转折点上有更多的思考与准备时间;同时,要坚信推进中美合作与友谊的理性力量最终会成为主导中美关系的主流。
第三,中美要不断扩大双方共同利益。深化两国在气候变化、发展、反恐、防扩散、网络、反腐、维和、执法、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扩大中美对话机制,夯实中美合作民间基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双方共同利益必然要求减少对抗,加强合作。
第四,中美要加强在互联网空间治理的合作。在21世纪互联网时代,中美关系可以划分为现实空间下中美关系与互联网空间下中美关系两个层面。互联网的普及,一方面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让中美民间声音能通过网络抗衡个别政客的极端言论;同时,互联网+中美坚实的民间合作与互信基础也减少了中美发生冲突的风险,因此,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推动中美经济合作,以及稳定中美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扩展中美网络空间的合作领域。
第五,美国要扮演好“火车头”主角。虽然美国经济面临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领跑世界经济的“火车头”。首先,从GDP总量看,2011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9.98%,日本占8.36%,德国占5.18%,英国占3.54%,美国则占到21.51%。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虽然相对于2009年的24.6%有所下降,但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从人均GDP看,全球70亿人,中国和印度总共25亿,消费不到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13亿人口,消费3万多亿美元),而美国虽然只有3亿人,消费却达到了11万亿美元,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再次,从技术创新看,未来世界的创新依然要依赖于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一批伟大的互联网高科技公司正以永无止境的创新精神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
第六,中国要扮演好“稳压器”角色。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实力快速提升,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压器”。同时,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致力于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主动承担起与自身水平相称的国际经济责任: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与20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等,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倡导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如上政策建议的形象表述就是,中国不谋求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致力于同美国携手加强和完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实现中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的最大化。缔造中美双赢的未来与全球共赢的未来是大概率事件,道路曲折,前景可期。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接受美媒采访: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国.中国广播网[EB/OL].(2012-02-13)[2016-06-16]
http://china.cnr.cn/gdgg/201202/t20120213_509156819.shtml
[2]基辛格.中国和世界秩序[J].经济导刊,2015(6):100-105.
[3]修昔底德陷阱的提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多半会走向战争。
[4]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构想中国第三步改革——斯蒂格利茨看中国的经济走势[J].中国经济信息,1999(18).
[5]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看好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新浪网[EB/OL].(2004-11-03)[2016-06-15]http://
news.sina.com.cn/o/2004-11-03/08114123693s.shtml
[6]黄卫平,丁凯,赖明明.双赢的未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7]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3):50-68.
[8]国际金融资本势力先向某国投入大量“热钱”,炒高该国的房地产和股市,等泡沫吹大后再将热钱抽走,该国股市、房市暴跌,引发经济危机。
[9]英文单词为“BRICS”,特指新兴市场,分别代表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南非(SouthAfrica)的首个字母。
[10]纳斯达克指数走势.新浪网[EB/OL].(2016-06-14)[2016-06-14].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IXIC.html
[11]道琼斯指数走势.新浪网[EB/OL].(2016-06-14)
[2016-06-14].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DJI.html
[12]中国互联网行业景气指数报告发布:中国互联网行业仍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新闻网[EB/OL].(2016-06-08)[2016-06-14].http://www.chinanews.com/cj/2016/06-08/7897807.shtml
[13]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信办网[EB/OL].(2016-01-22)[2016-06-14].http://www.cac.gov.cn/2016-01/22/c_1117858695.htm
[14]美国自主要贸易伙伴进口额.商务部网[EB/OL].(2015-01~12)[2016-06-14].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48097
[15]去年中企对美投资创新高逾150亿美元遍布全美.中金网[EB/OL].(2016-06-10)[2016-06-14].http://news.
cngold.com.cn/20160610d1702n72482641.html
[16]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定,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奠基石,是近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
[17]亨廷顿,周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2012.
[18]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会上的讲话.新华网[EB/OL].(2014-09-24)[20
06-1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c_1112612018.htm
[19]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徐向梅等译.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82-83.
[20]郑永年.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金融时报中文网[EB/OL].(2015-12-07)[2016-06-14].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137?dailypop
[21]习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华网[EB/OL].(2013-06-10)[2016-06-1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
[22]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提法为何不积极.大公网[EB/
OL].(2014-10-23)[2016-06-16].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watch/2014-10/2799687.html
[23]美媒:美国对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态度暧昧.参
考消息网(2014-12-14)[2016-06-16].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4/1214/596314.shtml
The Internet age Chinese American win-win future outlook
LAI Ming-ming HUANG Wei-ping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the Internet is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of china-us relations, pay more attention its direction.New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 econom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fusion of three major factors in the collision, laid the basic path of win-win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t the same time, analyzes the three modes of the game.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sino-us relations is the main points of the clear their orientation, to play a role of "eng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will play a role of "stabilizer", the Internet for stabil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us relation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constantly expand the cooperation areas of the network space,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to create a win-win futur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win-win future.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 Game, Win the future ; The new power relations
(责任编辑:李晓晖)
作者简介
赖明明:经济学博士,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经济学、互联网经济、网络空间治理。
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富布赖特高级学者,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中国早期接入互联网的时候,我是中国科协的副主席。当时计算机学会挂靠在计算所,而计算所的上级是科学院,我是主管这个领域的。当时的院长让我做计算机学会的理事长,说这个学会很重要,又挂靠在科学院,勉为其难你也得做。
1989年8月26日,经过国家计委组织的世界银行贷款“NCFC”[1]项目(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论证评标组的论证,中国科学院被确定为该项目的实施单位。同年11月组成了“NCFC”联合设计组,这是国内第一个示范网络。
在招标、评标的时候,我主管的学科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组织了很多的人,关起门来干了很长时间,他们很努力、很辛苦。我们的标书、答辩只比清华和北大多了0.7分。当时我很紧张,现在讲究关系,这0.7分很容易地就被人家抹掉了。我就赶紧去找计委的副主任张寿。[2]我说张寿同志,我们这个招标可是在计委正式的主持下进行的,这个招标分数算不算?张寿说你放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要是讲人情什么的,我讲不过来,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有人情、都有背景,我跟谁讲去。有了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当时是NCFC项目管委会主持人。管委会的组成,是计委和科学院协商的。回想起来,我还要感谢当时教委的领导。我们牵头,清华、北大肯定是非常不服气的,我都看得出来,就差0.7分,凭什么你们科学院牵头?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千万不能打架。作为科学院,我们一定得承认他们的强大,承认他们的优秀,虽然科学院领先了,但是我对他们非常尊敬,一个一个的去拜访。在成立NCFC管委会之前,我拜访过教委主任朱开轩,[3]他对我说:“你放心,我们的学校没有中标,他们的心情确实不好,但我们会顾全大局,一定会尊重牵头单位。你们的责任很大,要对国家计委负责,要对世行这笔贷款负责,所以你放手干,管委会决定了就干,不必事事来教委汇报。”这个项目本来是跨部门的项目,是科学院和教委两个正部级单位之间的事情,要讨论NCFC的工作怎么做、钱怎么用等,如果要在两个部门之间扯皮太困难、效率太低。所以,朱开轩主任授权NCFC管委会来决定跟这个项目有关的事情,这对我们牵头单位是最大的支持。
然后,我又去拜访了两个大学的副校长,清华大学参加管委会的是梁尤能[4]副校长,他说,你不要有顾虑,虽然我们的技术队伍很不服气,但是我们一定会在管委会里团结合作,大家一定要把这任务搞好。梁校长这样的表态,我就放心了。所以后来NCFC工作一直非常顺利,大家团结合作,非常愉快,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摩擦。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都能够摆在桌面上公开讨论,钱怎么用,都向大家报告。
NCFC项目如果是学校主导的话,我想我也会来做这件事,因为当时科技界对互联网要求确实非常迫切。像我们科学院的高能物理所,跟西欧核子研究中心(CERN)有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5]记录下来的数据是海量的,双边要交换这些数据,怎么传递呢?都用X.25[6]那个包交换,等于是一种打长途电话的费用,贵得不得了,给他们的那些科研经费,差不多都交了邮电部的电话费了。所以他们的要求非常迫切,一定要采用计算机直接联网。
1993年国家计委下达的国家示范网络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清华、北大校园网,还有科学院中关村地区的40几个所,这三个校园网都完成,主干网也连上了,就在等候验收了。
NCFC项目有420万美元世行贷款,是计委向世行借的钱,另外500万人民币是计委匹配的,加在一块有5000万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
那时计委接到很多的报告,包括科学院、清华、北大,还有很多学校,都提出要购买超级计算机。计委考虑都买不行啊,干脆我们出钱,跟世行借钱,买一个大机器,然后大家都联网,来共用这个机器,大家都联成网,连到一个计算中心。当时的任务书里并没有考虑接入互联网。
但是由于巴黎统筹会[7]不肯卖给我们高性能的计算机,而我们的技术队伍不能停下来等着做工程,怎么办呢,能不能用国际联网来解决?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我是代表,还有一个局的代表,两个学校,总共6个方面的十来个人一起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应该国际联网。
可是任务书里没有涉及国际互联网,就得自己拿钱,因为任务经费是不能动的。科委的冀复生司长[8]说可以出,大概300万,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代表师昌绪[9]先生(后来换成了陈佳洱[10]先生),表示可以匹配,大约是200万。我就说,剩下不够的由科学院兜底。
接着就去跟邮电部商量,首先是国际互联网这条线要邮电部的卫星通信线提供,这条线是通过北京郊区的一个天线传到卫星上,再传到美国,那时还没有海底光缆。我找朱高峰[11]副部长谈了两次,说这个国际联网是国务院批准的,我们又不盈利,租用信道不能要那么多钱。朱高峰副部长还是很开明的,为我们破例开放了。
联网的事在美国遇到了障碍,我们找了很多人,包括美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我给他写了信要他帮忙。他说已经尽了很大努力。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下面管网络国际合作的斯蒂芬•戈德斯坦[12]来信也说,“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确实有一些技术以外的障碍,所以我们还在努力。”如果美国对我们很开放,让我们直接进入,也就不用报批,现在这事情卡在技术以外的障碍上,要是和美国官方交涉,没有政府做后盾不行,我就跟周光召[13]院长提出,科学院要赶紧给国务院起草了一个报告,强调互联网是科技进步和国际合作不可少的。
恰好就在我4月10号去美国之前,主管科技的宋健副总理的批文来了,邹家华也批了意见,还有其他一些领导。我要利用赴美开会以外的时间,去办这件事。先是找了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主任尼尔•莱恩,⑧他说这个事要找斯蒂芬•沃夫,⑨他是自然科学基金会管国际合作的,当时没有在华盛顿。后来找到了斯蒂芬•戈德斯坦,他管网络国际合作,当时尼尔•莱恩也在场。我向他介绍了我们这个NCFC,就是两个大学还有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的科研项目,我们有许多国际合作,需要互联网。尼尔•莱恩回答说可以啊,我问需要不需要签署一个什么文件,他说不需要。
至于尼尔•莱恩为什么爽快地同意,我想可能跟当时美国互联正处于商业化前夜有关。美国互联网的三个阶段分别由国防部、NSF和DOC——商务部来管,1994年尼尔•莱恩一定知道,自然科学基金委管这个互联网已经管不了多久了,马上要交商务部,等到商业化后,科学院总会进来的,还不如先让科技界的进来。很快,我们团队的技术带头人钱华林[14]就告诉我:通了!这一天是1994年4月20日。
1994年引进来以后,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cn设在什么地方。当然不是理所当然放在科学院,但我跟科学院的人说,要好好争取,认真研究这个域名怎么管理,做好技术方面的准备。
钱华林对国际上这些组织比较熟悉。有个APNIC,[15]是管亚太区分配IP地址的,他就出主意,把他们一个直接跟我们沟通的、管IP地址的人请来。我知道,.cn服务器到底设在哪儿,最后要报告APNIC,APNIC才能把根服务器上面中国的.cn的服务器的地址、IP地址确定下来。来的人叫戴维,他说,条件是在中国没有人提出异议,没人跟你抢才行。当时的互联网管理就是这样,非常民主,不是看有无政府批文,而是看你有没有技术条件。
我觉得科学院那个队伍确实不错,我们有条件。所以我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把科学院的一个计算中心给重组了,使之变成一个以网络服务为核心的所。大家商量,也都同意把这个计算中心改组,建立中国科学院的网络信息中心[16]CNNIC,科学院党组也同意这个意见。改组工作,在1994年到1997年之间就完成了,组建了一支很年轻的队伍。我跟他们讲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不是科学院一个随随便便的所,你们这个所不是以研究为核心的,而是以服务为核心,你们服务的对象就是这个网络,是互联网。
这个队伍为.cn管理做了很多准备,还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权威们的认可。接下来,我把中国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的准备情况,人员队伍,为.cn服务器所做的技术上的准备等等,打了报告,报告给新成立的电子部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吕新奎,[17]提出要为国家来管中国的顶级域名.cn服务器。吕新奎亲自来看了看,觉得可以,加上对科学院的信任,批复同意科学院意见。
我还考虑到CNNIC来管.cn,一定会有很多行政上的事情得协调,我提出要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邀请一些企业、科技界、学者、政府主管部门等参加,企业主要是电信,有何德全、曲成义等学者,政府部门就请邮电部来当委员会的副主任,我担任主任。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一是沟通,二是协调关系。CNNIC这帮年轻人很能折腾,带头人毛伟很有开创性,他邀请了一些法官,做了域名仲裁委员会,这是一个创举。他没有先去找司法部,而是先从愿意为互联网做些事情的人开始,邀请了一个年轻的法官来参加,又找了一个年轻的法学家,然后逐步扩充,发生域名纠纷的时候,就开这个仲裁委员会。如果有纠纷,仲裁委员会一判,两边就不用上法院了,省了钱,也省了时间。我非常鼓励他们干这类的事情。如果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和障碍,工作委员会可以赶紧向邮电部报告来协调解决。后来邮电部变成信息产业部的时候,还是派人担任CNNIC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那个时候国信办还没成立。
后来,中国的域名成为一个产业,大概有几万人就业。我现在还觉得由科学院来管,对中国比较好,得益的是中国,这跟国际上的做法是一致的。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电信超前发展的政策,给互联网的普及扩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政府对互联网的政策在经济领域还是很宽松的,所以能够让那么多民营企业就起来了。所以说到这20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政府给了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这很重要;然后有这些创业的年轻人,他们是我最喜欢的、最敬佩的一群人。我们毕竟只是一个铺垫,真正来舞台上唱戏的是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在舞台上演这么精彩的戏,你这个舞台搭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能够把互联网在中国搞得这样火的,不就是这些企业家吗?
再往后,信息产业部调整以后成了CNNIC的领导部门。我就对毛伟说,我说你一定要主动跟他们汇报工作,不必通过科学院。后来他们就搞得很好,毛伟直接跟信息产业部汇报,他们派人来看,还提出具体意见,比如这个跟安全攸关的事情机房的安全措施还不够,供电没有两路供电,没有什么紧急应急措施,需要改造。他们关系一直很融洽,这是我感到最快乐的。
我还想说一下我们是一个团队,各人干好各人的事,我干的主要是上层关系协调,像保证NCFC合作单位和平共处、什么时候到美国交涉,这是该我考虑的。后来有人对我说,你做得真不错。我说我不过是在其位谋其政,该我做的事我都好好做了,没有因为我的糊涂而丧失时机,我该推的时候往前推了一把。这些人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见证人,亲身的参与者。
后来有人说起1987年王运丰[18]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那是当时兵器部的计算所自己需要,找到了德国Karlsruhe大学[19]的措恩[20]教授来帮助,发了“跨越长城、走向世界”那封邮件。可是科学院高能所的吴为民[21]在1986年已经发了第一封电子邮件,主要是跟CERN在讨论怎么交换数据。2003年我参加WSIS[22]会议,德国一个叫Zorn[23]的教授做的报告题目就是“互联网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也提到“跨越长城”的邮件,这些和我们后来做的事没有一点关联。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国际上已经组织起来了很多的互联网组织了,首先就是ICANN,[24]每年开那样规模的大会。我们总感到在国际场合,要去说话很单薄,需要一个全国的协会代表中国互联网企业界、科技界去说话。
我记得跟清华的吴建平[25]商量,是不是也该成立一个这样的协会?他说胡院长,你来牵头。作为科协[26]的副主席,我就跟科协讲了这个事,科协说我们主管的是学会,不是企业协会,企业协会必须是产业部门来抓的事。后来我写了一个报告,找了几个工程院院士,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们写了一封信给科协,科协同意了。我们接着跟信息产业部沟通,说科协愿意跟你们联合发起成立中国互联网协会。那个时候,信息产业部也有这个想法,主管领导来找我,说协会请你做理事长。我说还是找一个企业家吧,我们是科技界,不懂这个。可是人家很坚持,谈了好几次。我问院长周光召,他说,要是他们主管部委真的让你干,你就干了吧。当时科协的党组书记张玉台[27]也说,启恒,你就应该干,你干比企业家好,人家会认为企业家不公正。我一想,也是啊。这理事长一做就做了12年。2001年的时候,有一次在国外开会,外国朋友提出说希望ICANN大会在中国开一次,我马上就接受了,我说我们很愿意做一次东道主。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个会不属于科学院的范畴,它归口信息产业部,而信息产业部要开这么大的国际会议,必须部党组讨论,还得报外交部等才能开,这跟科学院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黄澄清[28]立了大功,为了开成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他和当时的信息产业部主管领导都出了很大的力,才把这个会开成了,规模很大,超过千人参加。

图1: 2007年王旭东部长,胡启恒院士,谭铁牛副秘书长一行莅临CNNIC视察指导工作

图2: 2013年度的“互联网名人堂”入选嘉宾合影
我觉得我很幸运,一路上碰到这些人都特别友好,特别支持我,所以很顺利,眼看着互联网长大。开始时互联网名声并不好,被称为洪水猛兽,电视上老是骂互联网,而且是专家,说家长们啊,你们可要注意,让你们的孩子远离网络。如果真让我们的孩子都远离网络,中国就会跟世界拉开更大的距离,肯定会落后。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完全转变了。
(本文根据访谈整理,文字有删减,完整版已经口述者确认。感谢赵婕、刘伟、冉晓燕、胡冰、黄恬、孙雪、杜运洪等人为本文所做贡献。欲了解完整版,请关注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口述历史》系列丛书。)(责任编辑:李晓晖)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The 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
[2]张寿,生于1930年,江苏常熟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第一副校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信息中心主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等。逝于2001年10月1日。
[3]朱开轩,1932年11月生,上海金山人。高级工程师。曾任中纪委驻国家教委纪检组组长,国家教委主任等。
[4]梁尤能,1935年4月出生,四川达县人。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
[5]北京谱仪(BES),是一台大型通用探测器,安放在BEPC储存环南端的对撞区,正、负电子束流在谱仪中心发生对撞。是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大型粒子物理实验装置,由多种子探测器组合而成。
[6] X.25,是一个使用电话或者ISDN设备作为网络硬件设备来架构广域网的ITU-T网络协议,是第一个面向连接的网络,也是第一个公共数据网络。
[7]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8]冀复生,科技专家。曾任《信息技术快报》执行主编,中国驻前联合国的科技参赞,科技部(科委)高技术司司长。
[9]师昌绪,1920年11月生于河北省徐水县,材料科学家。曾任金属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逝于2014年11月10日。
[10]陈佳洱,1934年10月出生,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家,加速器物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等。
[11]周光召,1929年5月生,湖南宁乡人,著名科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副会长,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等。
[12]尼尔•莱恩(NealLane)
[13]斯蒂芬•沃夫(StephenWolff)。
[14]钱华林,1940年12月生,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早期从事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和整机的研制。是中国互联网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15]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Asia-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APNIC)。
[16]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网络中心,CNIC),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科研事业单位。主要从事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建设、运行与支撑服务,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科学工程计算的研究与开发。
[17]吕新奎,1940年9月生,江苏无锡人。曾任中国电子总公司副总经理,电子部副部长兼国家信息化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信息产业部前副部长,CETC(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主要创始人。
[18]王运丰,著名的武器专家。曾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华洪堡学者协会会长。中国互联网的先行者。逝于1997年4月29日。
[19]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Universitaet Karlsruhe)。
[20]维纳•措恩(Werner Zorn)。1987年9月20日,他帮助中国从北京向海外发出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的内容为“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21]吴为民,1943年生,华裔物理学家,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ALEPH组组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研究室副主任等。
[22]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orld Summit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简称WSIS),是一次各国领导人最高级别的会议,与会的领导人致力于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数字革命的潜能造福人类。
[23]维纳•措恩(Werner Zorn)。
[24] 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98年10月。
[25]吴建平,生于1953年10月。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专家委员会主任、网络中心主任。
[26]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由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地方科协组成,组织系统横向跨越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学科和大部分产业部门,是一个具有较大覆盖面的网络型组织体系。
[27]张玉台,1945年9月生,山东郯城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等。②黄澄清,曾任邮电部办公厅副处级秘书,中国工程院办公厅处长,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处长等。
[28]胡启恒:模式识别专家。历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模式识别及机器智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从事模式识别研究工作。
溯源是一门回答问题的艺术。溯源能力差会削弱一个国家的信誉、效率,最终危及其自由与安全。
溯源是逐步展开的。譬如,破案会先从报案电话入手调查。警官会保护现场,询问目击证人法医专家尝试去发现和分析物证,把受害者身发现的子弹与犯罪现场留下指纹的枪支进行比对。这一过程尽管常常充满戏剧性,但它确实是一个讲方法、有顺序,以及形成固定流程的程序。
在网络安全领域,围绕溯源一直存在争论。[1]目前,数字领域的溯源受三个假设主导。第一个假设是溯源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2],它源自根本性的技术架构[3]和互联网的地理分布。[4]因此,只有在技术上重新设计互联网才能根本解决这一个问题。[5]类似的看法在有关法律问题争论中亦占上风。[6]第二个假设是对溯源持二元论观点:在给定情况下,这一问题要么能解决[7],要么解决不了。[8]溯源要么能找到真凶,要么只是找到一个仿冒的IP地址,混乱的网络日志或其他毫无用途的痕迹。[9]第三个假设是能证明责任归属的证据十分广泛,主要挑战就是找到证据本身,而不是分析、提炼和展示。[10]上述观点均很普遍,它们是直观的认识,也没有错——但它们却有局限且不充分。溯源的本质在过去10年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相对目前已有的研究而言,真正实现对网络事件的追溯已经变得更为微妙,更加普遍和更具政治性。[11]
本文提出并探讨3个问题:第一,溯源与技的关系问题,如果溯源不是技术问题,那它是么?第二,溯源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标准溯源,如何区别高质量溯源与低质量溯源?第三,溯源与证据分析的关系问题,如果证据不明、且模棱两可,那么怎样进行整理和分析?
为了描绘出一个理想的溯源,引用了Q模型。[12]在技术上,这个模型能帮助分析人员提出所有相关的问题,帮助他们思考并把调查放在一个大背景下进行。[13]在操作上,模型有助于把技术与非技术信息整合到一个竞争性假设之中。这包括从不同层面提出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从细微的技术问题到更全面和解析性的操作问题。战略上,模型有助于用恰当的估算语言提炼出溯源的精髓并陈述出来。这种表述可能会形成带来严重后果的政治决断。
这个模型,第一部分是概念:用通用术语讨论模型、提出几个重要的区别和动力,说明溯源是一个过程。第二部分是实证:利用近期的几个事例列出溯源的步骤。第三部分将探讨Q带来的众所周知的问题,沟通面临的挑战,溯源的局限以及如何把结果转化成行动。结论部分则再次评估几个一直存在却始终没有答案的观点,思考追踪网络攻击的局限。
本研究旨在为参与溯源的所有相关方提供一个概念和实际操作的图景,从取证调查人员、情报分析者、国家安全官员、管理高层、政治领导到撰写网络安全和网络入侵文章的记者和学者。
溯源过程中的每个层级都面临不同的分析挑战,需要专门的数据和专业知识,还需要各自对成功溯源的看法。每个层级的分析人员都要向其他级别通报并进行调整。尽管溯源过程有始有终,但这个周期不必遵循专门的逻辑或时间顺序,原有的假设会与新发现的细节相矛盾,新发现的细节又会带来新的猜想。然而,不同层级有不同的任务并独立进行分析,哪怕它们相互关联。通常情况下,所谓的“危害指标”启动溯源过程。这些指标带来了各种特定的技术问题。只有事实收集得足够多,更多的问题才会被提出。溯源的启动偶尔也从操作或战略层开始。有时候一起事件的“第一知情者”会是技术层之上的人员。借助未经鉴定的情报源,或者更宽泛的地缘政治背景——有时候甚至会是直觉——在用技术指标标注前、甚至事件发生前,分析者就确定了可能发生的恶意行为。溯源还会采取另一种方式:战略和操作层分析会启发后续的技术分析,或反之亦然。
溯源需要大量的技能。网络威胁的复杂程度非常高。通过溯源分析来应对和揭露它们的架构需要一个明确的分工。例如,一个反病毒专家团队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某个恶意软件的安装过程进行反向工程研究,控制工程师则侧重分析针对某个工厂的定向有效载荷的设计特点。震网病毒如此复杂,企业侧重从不同方面对它进行分析,如传播机制、指挥与控制装置或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有效载荷。[14]在战场上,一个完整的战术行动的地位低于战役考虑,但它又很重要。对不同方面进行分析需要大量各异的技巧,这种专业化是网络和军事行动中已被广为接受的基本原则:没有指挥员会派拆弹专家去负责分析叛军网络的筹资情况或爆炸装置的来源;F-16飞行员不会自己选择目标;导弹工程师不制订核战略。网络攻击情况下,最起码的期望就是组织一个超越小规模的专家群来进行溯源。
溯源全过程的总目标常常取决于已遭受或可能造成的损害。在事件频发但调查人手不足的情况下,遭受或可能遭受损害的总量常常决定了追踪恶意行为所投入的资源。如果一次入侵事件并未造成显而易见的损失,某个公司甚或政府部门可能启动一次昂贵的调查。因此,缺乏对后果的认识甚至在全面启动调查前就中止了溯源。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不可避免。
战术目标主要是掌握事件的技术细节,即怎么发生的。操作层的目标是认识攻击的来龙去脉和攻击者的身份,即事件是什么。战略层的目标是掌握谁对攻击负责,评估攻击的原因、重要性及恰当的应对方式,即回答“是谁”和“为什么”。最后,沟通也有自身的目标:把劳动密集型取证调查的结果公布出去是溯源过程的一个成部分,它不应被忽视。事实上,公布溯源本意义重大:攻击者可能中止行动,改变战术或开回应指责,进而促成受害者的进一步回应。
细节是关键。但细节也会使人困惑。从技人员流向操作层和战略层的信息必须经过加工理。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被理解和发挥作用。针某一入侵,技术分析能产生大量的数据,常常括被利用的漏洞、有效载荷机制、指挥-控制结构、目标数据、反向工程分析以及被攻击网络的原始数据。部分,也有可能大多数技术分析可能彼此没有关联。操作层和战略层并不觉得一些相关联的技术细节有多重要,就像取证调查人员不关心地缘背景一样。
确定性存在差异。随着信息从技术层面流向操作层及战略层,遇到的问题开始变少但更全面。因此,随着分析由技术人员转向政府部门,有关溯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增多。根据法医取证能够回答入侵的机制是什么的问题。动机是什么的问题则需要提出假设以及随之而来的验证。[15]技术取证的关注点相对狭窄和具体,能够找到答案。操作层提出的相互竞争的假设可能源自大量人力进行的取证结果,但却未得到可供使用的技术和非技术证据的充分支撑。战略层的结论也并没有比技术取证高明多少,可能只是对大量假设与判断的整合。[16]接受过培训的资深决策者是管理这些问题的关键。
接下来是“光圈”。溯源过程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情报圈称为“光圈”的问题:能够确定调查目标的情报源范围,类似于照相机的调焦。情报来源的增多可以提高溯源的质量。另外,随着溯源进程的逐级深入,大光圈变得更重要:在单纯的技术层面,对专门的事件划定范围(设定光圈)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有条件限制。某个入侵产生的数字证据取决于它发生的背景。网络刺探使用的代码几乎不暴露攻击者的动机。在操作、尤其是战略层面,其他情报来源将能描绘出更全面的图景,例如拦截那些指挥或组织者电话通讯或电子邮件。全源情报的重要性、更的“光圈”,是解释为什么那些拥有高水平情部门的国家比一些能力强大的私企能更好掌控溯源进程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国对国计算机网络入事件“月光迷宫”(Moonlight Maze)说明了源情报和“大光圈”的价值。1998年,[17]外国谍把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以及一些国防承包商和大学作为攻击目标。入侵者窃取了从头盔设计到大气数据等信息。调查开始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不知所措。1999年初,国防部开始支援调查。计算机网络防御联合特遣部队(JTF-CND)的情报人员“竭尽所能”,从执法部门获得的数字证据开始,但随后调用了信号情报、人力情报,甚至是一些可疑建筑物的过顶卫星图片记录以审查它们近期是否安装了通讯设备。最终,情报源得到的情况远远超过对入侵的数字取证,成功地确定“月光迷宫”造成的数据泄露源自俄罗斯政府。[18]
在追溯网络入侵时,单独的个体值得重视。如果找到的证据能够把入侵指向某机构中的某个人,这一溯源十分有效。从众多国际事件、尤其是军事事件中,可看出鲜明的对比:被标识的武器系统,身着军装的士兵,事件发生的地点常常说明入侵背后机构的身份。某个特殊的军事目标,例如叙利亚的实验核设施可能会遭到空袭。通过分析地缘政治背景、飞机型号或飞行路径——除了确认飞行员本人,叙利亚或第三方能够确认实施袭击的F-15战机来自以色列空军。识别一个军事机构首先不需要确认个人和较小的作战单元,这在网络行动中则完全不同。
溯源的终极目的是指出某个机构或政府而非个人。但与标识、军装和地理位置不同,单个行动人员可能是恶意行为与机构之间最强有力的联系者。单凭这种个人关联并不足以带来高质量的溯源。然而,明确地指出一个机构首先需要把范围缩小至个人,然后再回放到机构或部门。这一系列行动取决于可掌握的“光圈”。个人的联系如果能与来自其他渠道的指标相契合,则证据将得以显著强化。
洞察力也很重要。先入为主、预判、偏见以及心理和政治倾向都有可能影响溯源,其中又涉及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从内部看,各层级的分析员和管理者大多会从各自角度提供预期的结果和解读证据。机构设置的原因将使内部报告会被忽略,这一问题也因此被放大。一个综合性的事例能够说明这一结论:假设沙特阿拉伯政府发现了“正义之剑”,该组织声称在2012年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发动了名为“沙蒙”(Shamoon)的网络攻击,其一部分成员来自位于沙特的什叶派激进分子。在逊尼派属于少数派的国家,对什叶派的偏见可能使沙特的调查人员会假设这个组织受雇于伊朗政府,即便手中的证据无法证明这些什叶派沙特公民得到德黑兰的支持。国内偏见越大,犯下严重错误的风险就越高。
所谓溯源质量就是要“问对问题”。模型的每个层级都有一系列能推进本层级进程的具体问题。每个层级所含问题的答案就是向下一层级推进的起点。一个团队对整个过程的整体把握越好,溯源的质量就越高。这个过程是动态和非线性的:每个案例都不同,因此在调查中,任何固化的流程或线性的“清单”都是有问题的。[19]接下来将逐层讨论这个过程,从战术性的技术开始,逐渐向战略性考量深入。如果可能,每一方面的描述都将附有对实践案例的简短说明。[20]
技术层常常是调查的起点。它广泛且深入,给相关人员带来重要挑战。这需要分析者以一种高效的团队工作来回答关于计算机代码、网络行为、语言和其他更多技术问题。在许多案例中,技术证据都是溯源过程的基础。发掘这些证据并不总是充满荣耀的行为,而是生死攸关。
危及安全的指标很有可能开启一项调查。损害指标是指网络侵入或恶意行为的技术指征,常被简称为技术术语IOCs(Indicators of compromise)。无论是通过广泛的自动扫描还是计算机异常行为报告,这些攻击迹象都能被发现。对大量计算机进行深入、个别和常规的证据分析对于网络管理者而言成本过高。IOCs能够成为帮助进一步缩小调查范围的有用工具。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将这些指标划分为原子的(atomic)、行为的(behavioural)和计算的(computed)三类。[21]
所谓原子指标(atomic indicators)是指离散的数据碎片,无法再进一步分解,否则将会失去其证据价值。通过原子指标本身能够查明恶意行为。一般包括IP地址、邮件地址、域名和文本碎片。计算类指标与这些数据碎片相似,但其中又包括一些计算成分。例如“哈希”(hash,也译作“散列”),一个从输入数据中获取的特有签名,如一个密码或一个程序。只要输入不变,一个散列的值就不变。在网络计算机运行的程序散列可能符合已知的恶意程序散列。行为指标是行为和其他指标的结合,在一些案例中,既可揭示恶意行为,也可用于指认过去曾实施过类似行为的具体人。从社会工程学角度看,一项行为指标可能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具体意图,如向低层雇员发送邮件以获取网络接入点,然后通过网络输特定恶意软件,与其他计算机建立未经授权远程桌面连接。关注计算机网络防御的机构收上述三种攻击指标和定期监测其网络和计算机一旦发现攻击证据,更多的技术问题接踵而至这些问题会根据技术指标(indicator)、敌对为(adversary)和威胁(threat)排出先后顺序
几乎所有攻击者都必须克服一个挑战:进入。[22]任何一个攻击者都必须具有在非授权系统执行代码的能力。这种代码利用系统漏洞,为攻击者提供更高的访问和执行授权。传送这种代码的通用方式不是利用技术弱点,而是利用人的弱点:鱼叉式钓鱼攻击,通过发送社会工程类信息欺骗使用者。著名的针对安全公司RSA的攻击就是始于一封发送给低层雇员的邮件。这封邮件的标题是“2011年招聘计划”,足以诱导有些雇员将其从垃圾邮件夹中恢复并打开其附件。附件是一个包含着恶意软件的Excel表格,能帮助攻击者进入系统。通过这个“登陆点”,他们能够通过网络进入到更具价值的计算机。[23]这种事情非常普遍,甚至用于实施更高级的攻击,[24]调查者关注他们以获取可能的溯源线索。与钓鱼活动相关的,除了技术数据,如邮件来源,还有社会数据,如语言错误和目标选择的老练程度。另一种进入方法是利用被远程接入软件感染的USB驱动器。攻击者或某个同伙,或某个不知情但使用了被篡改的U盘的员工有可能把它插入计算机中。还有更多实施侵入的纯技术手段。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水坑攻击”(watering-hole attack)。这种方式要求攻击目标可能会访问的某个网页——如外卖餐厅网站这样正当网站,[25]当目标雇员访问该网址时,网页浏览器中的漏洞会破坏他或她的计算机。许多侵入技术通过控制网络基设施,操控和破坏对合法网页的访问,发动所谓“中间人攻击”(man-in-the-middle attack),是在攻击者不能完全控制某个网络结点但仍能植入数据,发动“旁观者攻击”(man-on-the-side attack)。[26]
寻找目标的过程能够揭露或破坏侵入者的类型。针对信用卡信息和其他易于获利目标的攻击往往指向有组织犯罪。针对产品设计的攻击会指向从事经济间谍国家的一些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针对政治和军事战略细节的攻击则指向情报机构。技术层能够提供具体的与攻击有关的证据,帮助行动层推断。如通过观察侵入者在被破坏网络中不同计算机间的动向,调查者可观察攻击者在寻找什么。通过重建攻击者发出的具体指令,调查者能从被感染机器的存储记录中看出攻击者有无具体企图,或仅仅是在进行泛泛的搜寻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有时代码还包含着搜索词:2014年,一个有名的“毒蛇”(Ouroboros)行动,就包含了搜索词“北约”和“欧盟能源对话”。[27]对攻击目标的分析还有助于搞清攻击者的组织架构。攻击者所调用的资源可作为一个指标,判断其对目标价值的估算。如果一个攻击使用了许多超过必要程度的资源——如果低水平的间谍活动使用了一个高级的rootkit攻击,这就表明实施该行动的不大可能是一个能有效评估攻击目标的团伙。还有一个类似的“实施过度攻击”的指标:一些攻击者可能会对同一目标用同样方式进行多次攻击,甚至是在一次破坏已成功实施之后。这种没必要的投入可能表明攻击者代表着一个大型组织,目标混乱不明。这种针对大量目标的“喷射”式攻击还可能表明攻方内部破坏实施者与工具开发者间有分工。[28]
大部分恶意行为的实施依靠基础设施,在拒绝服务攻击案例中,它就是依靠向目标计算机发送大量无用信息来达到瘫痪的目的。其他一些恶意行动的案例,基础设施常常被用作“跳板”或向被感染机器发送代码指令(技术行话称之为命令与控制,command-and-control)。为了用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心怀恶意的一方会在破坏行动中多次重复使用同一个物理数字基础设施。因此,把不同行动与潜在的不同团体关联起来,对于溯源过程来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攻击者获得基础设施的方式不同:有的能控制一台计算机,在不被机主察觉的情况下把它变成僵尸网络(bot)的一部分;有的是通过服务器提供商合法租赁服务器,然后用它来作恶;或者攻击者本来就掌握着一些基础设施。攻击者操控基础设施的手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接下来的问题。比如,租赁来的基础设施,如虚拟机和服务器,可通过服务商公开获取更多的注册和日志信息。分析对方掌握的基础设施可获得地理位置等线索。一些情况下监控对手基础设施能获得新的分析线索,有助于未来行动。因此,一些精明的攻击者正在想方设法更好地掩藏他们的基础设施。
计算机代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模块化。出于效率的考虑,攻击者往往避免重新编写代码,而是会重复使用相关软件来完成整个行动中的基本任务。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这个软件常常直接植入目标网络,但事后会被调查者加以分析。攻击者使用的软件常常有着自己的签名和特点,能够为确认侵入者及其同伙的身份提供线索。不同案例这种分析的效果也有差别。一些被打包成模块的代码在攻击中的使用频率很高,但对确认具体攻击者却不是很有用。而其他一些像震网和Duqu恶意软件中使用的代码,是如此深奥而复杂,对确认攻击者身份很有价值。[29]在一些调查中,研究者有理由确定是同一个人编写了震网与Duqu的代码,因为两种恶意软件共享的一些关键模块和代码不是能轻易得到的。[30]
分析入侵者生活模式是调查获得突破的重要部分。为了效率的最大化,所有机构都有固定的日程和办事程序。黑客组织也不例外。时间和其他行为模式能够为确认其位置和身份提供线索。例如,众击公司追踪了某攻击行为的实施者,判断其位于俄罗斯,因为大部分“编辑时间”——即软件被打包使用的时间,就是俄罗斯的上班时间。[31]生活模式虽易造假,却被广泛用来证实调查者的推断。
恶意软件中的语言指标也能提供溯源线索。这里的语言主要分为两大类:被攻击者选中用来表达具体事务的文字,如变量、文件夹和文件的名字,以及通用配置参数。在复杂的“伪旗”行动中,二者相对容易伪装。然而溯源过程中语言分析仍十分有用。例子很多,最近,卡巴斯基发现名为“面具”(Careto)的恶意软件。软件开发者把间谍设备中的两个主要模块的一个命名为“面具”。按照惯例,此次行动的命令与控制服务器散布于很多国家,其中大部分位于非西班牙语国家,如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捷克、新加坡和美国。但语言指标却提出了相反的论断。[32]第一个指标是一些子域,冒充西班牙报纸而实际上却可能被用来实施网络钓鱼(虽然也会被伪装成英国和美国的报纸)。[33]第二个指标是计算机设置数据暗示代码是在西班牙语界面的计算机编写的。第三个指标是一些俚语的使用,俄斯研究者们怀疑:“在非西班牙母语者中很见”。[34]他们还给出了三个俚语使用的例子:复使用“Careto”一词,它是“脸”或“面具的西班牙俚语;设置文件的一个密钥被命名“Caguen 1 aMar”,很有可能是“Me cago en la mar”的缩写,卡巴斯基认为这应是西语“f-”;文件路径c:\Dev\CaretoPurebas3.0\release32\CDllUninstal32.pdb中包含的“pruebas”一词,西语意思是“测试”。
错误常常有启示作用。一些失误能够直接暴露攻击者试图隐藏的信息,如一个人或文件的名字,一个真实的IP地址,一个旧邮件地址,或是某个代码的注释。近来有两个突出的例子。第一个是“丝路”(Silk Road)网站,它以非法买卖毒品闻名,其运营者在网页上推销其非法运营活动和在网上寻求技术帮助时使用的竟然是同一个用户名。寻求技术帮助的帖子还留下了真实姓名和邮件地址,这些都为调查者提供了明显的线索。[35]第二个例子是黑客组织“匿名者”的领导人之一Hector Xavier “Sabu” Monsegur。他曾经忘记登录“洋葱”(Tor)服务器而进入受FBI监视的“匿名者”聊天系统,从而导致真实IP地址泄露。[36]这两个人都因此被抓获。即使这些错误并没有直接揭示相关信息,但它们仍很有价值。如在常用的命令中频繁出现一些打字错误能为复杂分析提供一般线索。正如“大拇指原则”(亦称“经验法则”),组织在本质上更为官僚化,拥有经验更丰富的运作者和标准化程序,其犯错的可能性比单独行动者要小。[37]
讽刺的是,秘密行动也能被揭露。任何行动中,行动者会在速度与隐蔽性之间有取舍,而这种取舍会留下清晰的痕迹。反侦察行动——用以避监测和事后调查的措施——都是百密一疏和耗费功夫的。攻击者使用的反侦察手段会暴露他的意图,对报复的恐惧和精明程度。一些反侦察为很普通,相对简单,直接关系到任务的成功与否。比如:攻击者在将盗窃数据偷偷绕过自动防御系统(用来监测是否存在有价值的文件离开网络)传出之前,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密。其他一些反侦察行为则更复杂和少见,如使用工具修改日志文件中的时间要保留,给随后的调查增加难度。攻击者的谨慎很难衡量。但是观察它们试图隐藏行迹的行为能提供很好的洞察角度。
一些国家将其行政部门、军队和情报机构置于法律监督之下。这意味着信息收集,尤其是破坏性行动必须得到法律部门的批准,而法律部门常常会约束这些行动。有时候借助技术分析,能明显看到这些限制措施,为溯源提供线索。对于震网,前反恐和网络安全官员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提到,他“强烈感觉到该行动是由华盛顿的一支律师团队操控或管理”,因为它的目标确认程序有意将间接损害最小化。[38]
溯源过程的行动层旨在合成不同来源的信息,包括来自技术层的信息,非技术分析和地缘政治背景信息。行动层的分析功能在于提出竞争性假设来解释事件。
分析计算机网络漏洞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溯源中,分析破坏某个具体网络所需能力是一条有用的线索。如对伊朗核设施的震网攻击具有极高的人力密集特征。恶意软件的有效载荷需要极充分的具体目标信息,如控制发动机转速的变频器的细节,这些信息往往很难搞到;再如伊朗纳坦兹核电厂IR-1离心机的具体技术参数;以及有助于了解机器构造的共振系统临界输入频率等。[39]震网使用零日漏洞的数量前所未有,约有4-5种,并首次使用针对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常用来控制工业机器)的rootkit攻击。[40]这些特点极大地缩小了目标的范围。其他一些准备还包括目标侦察和有效载荷测试。震网再一次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攻击改编了复杂的目标系统以获取动态效果。这需要提前测试。[41]测试环境必须使用IR-1离心机。这些机器很贵且难以获取。不用说非政府行为者,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政府具备测试震网的能力,更何况编写和部署这一病毒。这进一步缩小了可能性。
计算机攻击的范围有变化。对一个目标的多起攻击可能是相互孤立的;也可能是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更大规模攻击行动,针对更多受害者,可能长期持续并影响更广泛的区域。这种多阶段打击行动常常被称为高级持续性威胁(APT)。黑客组织从一个行动到另一个行动,常常运用相同的战术,针对基础设施和一般目标,因此对某个APT的理解在溯源过程中常常带来重要启发。判断一系列不同种类的事件是否构成一个APT,取决于方法论。而在安全界,各方所采取的方法大相径庭。因此,一个公司或一个情报机构对一项攻击行动的总结可能有差异。[42]
一些攻击分多个阶段。不同阶段可能针对不同受害者,这会妨碍对攻击行动的重建。换句话说,一种攻击行为可能仅仅是实施更大,更复杂破坏行动的步骤之一。大规模攻击的构成会明显不同,这就使得将这些碎片化信息综合在一起十分困难。如2011年对安全公司RSA的攻击是大型攻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其本身又是一个多阶段行动。这种行动损害了RSA出售的、广泛应用于政府和商业部门的SecureID系统。据报道,其后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入侵正是利用了被破坏的SecureID。[43]一个更加精心策划的分段攻击案例是DigiNotar事件。一个自称为“Comodohacker”的伊朗黑客首先黑进DigiNotar,一个荷兰政府所属的认证授权系统,用于认证网页服务器。他破坏认证授权后立即颁发大量假证书,假冒成谷歌和其他网站。这些证书让他能够截取近30万对此毫无察觉的伊朗用户发出的加密邮件。[44]
攻击会发生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攻击会发生与事先计划所不同的变化,能提供有关不断演进的政治与技术现实和目标的线索。震网再一次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案例。正如控制系统分析专家拉夫•兰纳(Ralph Langner)在分析震网时所指出的那样,破坏离心机的软件有不同的变种。[45]这些变种的攻击方式不同,并会在不同时间被释放。2010年7月主软件被发现后,回顾分析揭示,这种开创性攻击工具的第一版早在2005年11月就已被发现。最早版本的传播机制不同,不携带任何微软的零日漏洞,主要针对的是西门子417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s),后来的版本则对该控制器基本无效。[46]这种战术的变化意味着攻击者优先目标和环境的变化。
事件的地缘政治背景能够成为一个警告。事后分析表明,具体事件的地缘政治背景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如2007年在爱沙尼亚或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期间发生的DDOS攻击。[47]但这些案例可能只是例外。分析一项入侵活动的地缘政治背景要求对特定行为者及其组织所处的具体区域历史和政治知识有所了解。以2012年夏公布的高斯病毒(Gauss)为例,该行动以黎巴嫩金融机构为目标。[48]观察者推测其目的在于揭露真主党的洗钱活动。[49]那些无人承认的、目的性强的网络破坏,地缘政治分析尤其能有效锁定嫌疑目标的数量。技术人员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无法进行这种分析。
雇员和承包商代表着一个机构的最强实力,但同时也是最大风险。威瑞森公司(Verizon)于2013年发布的事故报告证实,内部威胁和失误是机构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经确认,在超过1.1万起事故中,个人被作为优先选择的突破口。[50]损失最大的攻击之一,即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沙蒙病毒就是由内部人员发动的。[51]少数几起已知的针对工控系统的攻击事件中,内部人员是最常见的因素。如2000年3月澳大利亚皇后岛马奇河(Maroochy)供水系统被破坏事件[52]以及同年发生在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Gazprom)的管线事故。[53]大量控制系统事故都由内部人员造成,即使是那些从未公之于众的事故。当一项恶意攻击要求很难获得的极专业技能时,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外部因素,但要多考虑一下内鬼的可能性。
在战略层面,领导者和顶级分析家们应致力于综合行动层获取的问题答案,形成有意义的结论。当领导者和高级分析者能有效质疑前期分析,查明细节并找到替代性解释时,溯源过程的战略析才能做到最佳。
网络攻击的后果并不都是相同的。其所造成损失是识别网络破坏最重要的辨别性特征。相于现实世界的物理攻击,网络攻击的损害总是以阻止和衡量。损害往往可分为四类:第一类直接且迅速的影响,如降低服务器的正常运行时间,影响文档的可用性、数据的完整性甚或是破坏硬件,如上文提到的针对沙特阿美石油的“沙蒙”攻击。此次攻击破坏巨大且立竿见影,3万个工作站同时受到影响。[54]第二类是直接但滞后的影响。震网对伊朗核离心机的操控破坏其构造,使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即使不是几年也是几个月)不断出现机械故障。[55]第三类是是间接但迅速的影响,如对声誉的破坏和信心的丧失。如对易趣网的大规模攻击,1.45亿消费者记录被破坏。[56]第四类是间接且滞后的影响,如知识产权的丧失,一旦被竞争者获取即可能丢掉市场竞争力。总之,网络攻击的后果越不直接和滞后,就越难衡量。
攻击带来的后果可揭示攻击者的意图,特别是在行动层进行恰当的综合分析之后。根据“大拇指原则”(经验法则),破坏总是试图将直接影响最大化,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然而信息收集则尽量避免造成直接损害,以躲避监测和在未来收集更多的情报。当然,受害目标的种类也能为意图分析提供线索,因为不同攻击者会选择不同的优先打击目标。
设想的后果并不总和实际造成的后果一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攻击者意图明显,但并未如愿。2012年阿美石油公司遭受攻击时,管理层推测攻击者的真实意图是操纵其石油生产控制系统,但显然没有成功。相对应的另一种情况是攻击切实带来了损失,但攻击者本意并非如此。计算机系统是复杂的,攻击者可能不清楚网络的布局,他们开展侦察时可能会造成一些无意的破坏。因此,分析者们必须结合其他领域的分析来评估损失。某次导致较小损害的网络攻击会是一个警示,很可能是一项未成功的、旨在破坏重要战略网络的行动,也可能仅仅是一个侦察活动带来的无意破坏。
理解网络攻击的来龙去脉很难,但十分重要。了解对手的动机和行为有助于避免未来的破坏。这种战略分析从定义上看是非技术的。比如,它依靠来自行动层基于地缘政治背景下提出的确凿信息和分析。以此为背景,分析还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的优先选择,无论这些选择是商业性的、军事性的或经济性的。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就能分析出网络攻击意欲何为。它还能为对手的未来行动提供线索。如果一次意图明显的行动失败了,理解它为什么会失败以及对方接下来可能会采取什么措施来纠正这一失败,有助于减少攻击带来的破坏,有利于有效应对。
网络行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新领域,会出现许多“先例”。分析这些先例和预测未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新的方法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一个趋势的开始。一些攻击也许揭示新的可能性,如震网中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组件对工控系统的控制。一些攻击可能很引人注意但重要性有限,如2012年秋天劫持数据中心对美国银行发起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这是一种新的技术手段,但不具有更强的战略重要性。[57]确定一个事件能否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先例能够帮助溯源和后期的应对。
验证溯源过程的结果是重要的。所掌握的证据和初步结论需要查验。取证专家能获取最切实的证据,如日志文件和代码。行动分析家根据其他资源继续这一工作。在战略层,决策者和高级分析人员一道查明来自下层做出的竞争性假设,最终推动整个溯源过程。对分析进行严格的测试能暴露经不起推敲的假设,想像的缺乏和思维定式。对附加细节、替代性解释的分析与探查,可能需要对整个过程细节性知识的把握。本文的分析和提出模型意图促进这种探查。如果事件特别重要,还可选派一支红队回顾整个过程,或是对原有团队的工作进行重审。丘吉尔有句名言:“调查总是正确的。”[58]
就溯源结果进行沟通是溯源过程的一部分。面对复杂的场景,高级官员和政治家只掌握溯源过程中的很小一部分,对公众而言,了解的则更少。信息披露的比例将决定外界(包括政治领导人,技术专家社群和普通大众)如何知晓一个机构的工作。溯源各过程的特点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各过程的沟通。情报曝光会损害情报源及情报搜集的方式。是否公开溯源结果难以决定,官员们常常过于谨慎和三缄其口。这么做的原因有很多。然而,对那些深陷秘密文化、不相信直觉的人而言,更多的公开性能带来三大重要好处:更多的细节交流意味着可信性、溯源和防御能力的提高。
第一个好处:公布更多细节将提升信息发布人和信息本身的可信度。
第二个好处:公布更多细节将提升溯源本身的质量。当一个案子及其细节公之于众时,溯源的质量就可能提高。印象最为深刻的案例也许是对震网的多层面和高度创新性综合分析:不同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对此恶意软件进行剖析,形成了大量侧重不同方面的极详细的报告。[59]溯源市场得到大力发展:见诸于世的最有用和最详细的溯源报告由公司而非政府发布。本文研究中使用的证据与案例几乎都来自这些公司报告。情报机构已从事溯源工作几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然而它们的工作相对封闭,创新的动力来自秘密而非公开的竞争。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情况的一个结果就是:公开并不意味着整个溯源过程的结束,而仅仅是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反过来又会催生新的证据和分析,进而要求调整相关的评估和对外行动。
第三个好处也是最重要的好处:公开更多细节有利于更好地综合防御。就结果进行沟通并不仅针对个案,而要提升综合安全。比如,讨论某次破坏活动所使用基础设施的细节能让其他网络管理者采取专门的防御措施。公布恶意程序新的病毒特征也有类似作用,因为他们能被其他管理者下载或加载到自动入侵监测系统。即使没有具体的好处,对攻击者所用新技术的细节性讨论也能为其他案件的调查者们提供有利信息。按高价提供威胁指标和更好的防御是网络安全公司的商业运营模式。政府如何应对这种发展态势无疑是一个公开而重要的问题。
公开结果常常影响攻击行为本身。随着更多溯源报告的出现,研究特定攻击者对意料之外的曝光采取何种反应已成为可能。比如,2014年2月10日,卡巴斯基公布的“面具行动”报告中对西班牙语入侵设置进行了分析,“1小时”后该行动就销声匿迹了。[60]2012年5月,关于火焰病毒(Flame)的报告公布,侵入者在近2周后停止了行动。[61]行动消失的方式能提供更多的溯源线索,比如行动的取消是否够专业,能否保持高水平的行动安全性。如果行动取消缓慢也许表明该行动的取消需经过大型官僚机构或组织的授权。当Duqu被发现时,其运行者忘记粉碎文件,这些文件虽然被删除但可恢复,从而使得行动的更多细节被揭露出来。[62]卡巴斯基公布的几个攻击行动都是在公布后消失,一些结束的比其他更快,一些结束的比其他更顺利:“红色十月”、“小公爵”(Miniduke)和“冰雾”都在2013年全部消失。[63]尤其是后两者,卡巴斯基的报告并没有确定嫌疑攻击者甚至没有指出嫌疑国,攻击者仍撤退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卡巴斯基报告公布前两周,2012年5月14日,火焰病毒的操控者开始拆除其精心设计的命令控制设施,这表明攻击的高度复杂,甚至可能是一种预警。[64]
公开交流最终反映出溯源是渐进的而非绝对的。安全公司和政府在操作中应注意一点:使用评估可能性的词语。情报分析先驱舍曼•肯特(Sherman Kent)于1968年写道:“在情报机构,正如在其他行当一样,评估是在你不知所措时应做的事情”。[65]评估性语言是“事实与判断的混合”。这种事实与判断的混合特别适用于网络安全领域。估计是有意以一种易受攻击的方式进行表达,从而公开接受批评。一份报告对于其知识的有限性和评估的表达越诚实,其整个分析的可信度越高。因为正如肯特所言:“情报评估是接下来最好的事情”。[66]
本文的研究介绍了一个追溯网络攻击的系统模型,并提出了三个核心观点:第一,溯源是一门艺术:没有单纯的技术方法可能程式化、计算、量化或全自动实现溯源,无论这种技术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高质量的溯源取决于各种技巧、工具以及组织文化:合作顺畅的团队、能力突出的个人、丰富的经验以及从一开始就出现的、难以描述的“有问题”的感觉。第二,溯源是一个微妙的、多层次的过程,而非一个能简单回答的问题。这个过程要求谨慎的管理、培训和有效的领导。第三,溯源依赖于政治风险。某个事件带来的后果越严重、造成的损失越大,政府在确定攻击者时可投入的资源和政治资本就会越多。在对某次攻击所采取的所有响应,包括执法、外交或军事手段中,溯源是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即首先需要明确攻击者是谁。政府决定如何开展溯源,以及溯源到何种程度就足以采取回应行动。
我们对实际溯源的分析引发了对网络安全争论中的一些共识性观点的怀疑。第一个观点,包括罪犯、间谍到破坏者在内的攻击人能够掩盖他们的踪迹,在网上能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而逃避追踪。[67]但溯源不仅仅是可不可能的问题,很久以来它已取得了成功。攻击者不能假设能掩盖真实身份制造破坏,而且还能侥幸逃脱处罚。即便溯源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但它原则上是可以管理的。
第二个迂腐的观点,互联网剥夺了国家的权力而且把这个权力转移到了非国家行为体、私人机构和罪犯手中,技术使得大家平起平坐。[68]对溯源而言,事情则正相反:只有国家拥有把光圈打开得足够大、准确追踪到最复杂行动的能力。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信息的泄露并未阻止它们,讽刺的是,对那些倾向于高估这些部门能力的局外人来说,曝光反而增强了它们溯源的可靠性。
第三个常见的观点,工业化程度最高、彼此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最脆弱,不发达且不怎么脆弱的国家拥有优势。[69]溯源再一次反证了这一逻辑:政府的技术能力越强,拥有的人才与技术越多,国家隐藏自身秘密行动、揭发其他国家及作出响应的能力越大。
本文分析可能挑起的另一个争论是互联网是一个攻方占优的领域。[70]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入侵者相较防御者拥有结构性优势,这一优势根源于互联网的技术架构。守方在所有时候都不能做错,攻方只需做对一次就成功。溯源再一次证明这是错的:入侵者只需犯一个错误,防御者的取证分析就能发现被遗漏的线索来揭露整个行动。
然而,进一步研究溯源的局限性很关键。第一个突出的局限性就与资源、尤其是技术和能力有关。溯源的质量是关于可用资源的函数。即使国际网络安全市场快速成长,老道的取证技巧以及复杂行动中的组织经验仍然稀缺。溯源过程中掌握的资源越少,它的质量就最难以保证。第二个重要的局限性是时间:溯源的质量是可用时间的函数。即便对最专业、拥有最好资源的团队、企业和部门而言,在有限的时间里分析一次精心设计的行动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一些重大的案子中,当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在高压下做出决定时,政治局势的发展远远快于溯源进展。溯源所能得到的时间越短,其质量也越低。
第三个重要的局限性是敌方的行为:溯源质量是关于敌方老练程度的函数。现已公布的为令人信服的证据获得之前,一些操作人员曾过错误,或者没有考虑到使用某些方法可能影取证。老练的攻击者往往老谋深算,最大程度掩盖并扰乱他们留下的痕迹。这需要运用多种源来揭露证据,从而使溯源更困难。但敌人会错误使溯源看到一线曙光。完美的网络攻击就像完美犯罪一样难以捉摸。然而,敌人越是老练,溯源花费的时间越长也越困难。
未来溯源仍将保持其独特性。1999年以来,网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互联网本身没有变化,它根本架构的变化也很缓慢。因此,溯源本身也不会出现太大变化——但是它会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在演变。一方面,溯源正在变得更容易。更完善的入侵侦测系统能实时发现攻击,能更快地调用更多数据。适应性更强的网络将提高攻击行动的成本,能消除不确定因素,节省出资源以更好地识别高级攻击。网络犯罪增多,能推动执法部门、甚至是不友好国家间执法部门的合作,这也能使国对国的间谍行动更难以隐藏,政治成本更高。
但同时溯源也正变得更困难。攻击者能从被公开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强加密技术使用的增多也给取证制造了更多问题,制约了大规模数据的搜集。过度的夸大和危机将阻碍微妙的沟通。溯源疲劳症开始出现。事实上,由于没有出现重大的后果,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不怎么担心被抓个正着,一个宽松的后果可以忽略不计的规则正在出现。讽刺的是,比起公开问责的自由民主政府,非民主国家可能更不担心被抓。因此,讨论也回到文章的起始点:溯源过程是一个技术——政治问题,是由国家决定的,通过投入时间、资源、政治资本以及战胜敌人的努力。
溯源面临的核心局限同样展现了本文的局限。一些最成功的溯源仍然不为人知,被一些国家封锁。未来,政府部门或安全公司将开发出更的工具,或者把这些公诸于世,由此为溯源打一个新的视角。一些信号情报能力可能已经为溯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甚至那些很少甚至不犯错误的极其高明的敌人理论上也可能被发现。本文并未得益于公众并不了解的进展和能力。然而,文章的分析在很长时间内将能自圆其说。自1998年第一次重大的国对国行动“月光迷宫”被揭露以来,溯源最核心的变量始终保持不变。
本文旨在实现两个目标。第一目标是提高官僚部门工作的质量。时间给高质量的溯源带来高压,尤其在利害攸关时。模型是为了确保质量,使溯源更高效和有弹性:我们详尽的图表能帮助公共部门和国会的高层领导理解证据是如何收集的,能够提出更确切的问题,能够发现判断上的偏差,进而能证实和完善他们的观点。与此同时,模型使得各层级的分析人员能够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各司其职。第二个目标是:提高公共讨论的质量。让人失望的是,较大范围的网络安全辩论质量不高。这包括在世界一流的新闻媒体中有关的技术报道。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学者的论述显然都受到源自技术细节及其局限性的影响。我们希望Q模型将有助于提高大家讨论的水平。(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托马斯·里德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网络安全问题专家,战争学系。著有《机器的崛起:控制论失落的历史》(Rise of the Machines: The Lost History of Cybernetics)。
参考文献
[1]该领域早期的贡献,参阅戴维•惠勒(David A. Wheeler)和格里高利•拉尔森(Gregory N. Larsen),“网络攻击溯源技术”(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国防分析中心,2003);理查德•克雷顿(Richard Clayton),“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与可追溯性”,《技术报告》Vol.653,(剑桥: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2005年);苏珊•布伦纳(Susan Brenner),“光速:对网络犯罪、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溯源与响应”,《刑法与犯罪学期刊》,97/2(2007),第379-475页。早期的案例研究可参阅克里福德•斯托尔(Clifford Stoll),《布谷鸟蛋》(纽约:双日出版社,1989年)。
[2] “溯源可能是最大的难题”,P.W.辛格(P. W. Singer)和艾兰•弗里德曼(Allan Friedman),《网络安全与网络战》(纽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3页);另可参阅,戴维•贝茨(David Betz)和蒂姆•斯蒂文斯(Tim Stevens),《网络空间与国家》(阿德菲系列,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劳特利奇出版社,2011年),第75-76页。
[3]例如,可参阅W.厄尔•博伯特(Earl Boebert),“对溯源挑战的调查”,“制止网络攻击委员会”编,《制止网络攻击研讨会纪录》(华盛顿特区:国家学术出版社,2011年),第51-52页。另参阅马丁•利比基(Martin Libicki),《网络威慑与网络战》(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市,兰德公司2009年),第43页。
[4]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和蒂姆•吴(Tim Wu),《谁控制了互联网?无边界世界的假象》(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5]麦克 • 迈康奈尔(Mike McConnell),“如何赢得我们正在失去的网络战”,《华盛顿邮报》,2010 年 2 月 28 日。
[6]参阅马修 • 韦克斯曼(Matthew C. Waxman),“网络攻击与使用武力”,《耶鲁国际法期刊》,2011 年第 36 期, 第 421-459 页, 第 447 页;尼古拉斯 • 查哥里亚斯(Nicholas Tsagourias),“网络攻击, 自卫与溯源问题”,《冲 突与安全法律期刊》2013 年第 17 期,第 229-244 页。有关溯源对使用武力讨论的必要性,参阅马尔科 • 罗西尼(Marco Roscini),《网络作战与国际法中的使用武力》,(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3-40 页。
[7]美国前国防部长莱昂 • 帕内塔(Leon Panetta)在“无畏号”航空母舰上曾发表了一段著名的演讲:“在解决阻遏网 络敌人更复杂的问题——确定攻击起始的难题——方面,(国防部)取得了重大进展”。帕内塔“对企业高管发表 的国家安全中网络安全的讲话”,纽约,华盛顿特区:国防部,2012 年 10 月 12 日。
[8]戴维 • 克拉克(David D. Clark)和苏珊 • 兰多 (Susan Landau),“解开溯源难题”,“制止网络攻击委员会”编《制 止网络攻击研讨会纪录》,(华盛顿特区:国家学术出版社,2011 年)。另可参阅杰森 • 希利(Jason Healey),《一 个激烈竞争的领域》(华盛顿特区:大西洋理事会,2013 年),第 265 页。
[9]罗伯特 • 内克(Robert K. Knate),“解决溯源:迈向网络空间的问责发展,谋划应对网络攻击的未来”,华盛顿特区: 第 111 届国会技术与创新附属委员会听证会,2010 年 7 月 15 日。
[10]在入侵分析方面最有影响的文章似乎都假设证据自己能说话,持这一观点的人们并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与非技术人 群沟通上。其中最有影响力和有用的文献是“钻石模型”,参阅塞尔吉奥 • 卡尔塔吉龙(Sergio Caltagirone)、安德鲁 • 彭德格斯特(Andrew Pendergast)和克里斯托弗 • 贝茨 (Christopher Betz),《入侵分析的钻石模型》ADAm86960(汉 诺威,马里兰州:网络威胁情报与威胁研究中心,2013 年 7 月 5 日),以及“杀伤链”分析,参阅埃里克 • 哈钦斯(Eric M. Huntchins),迈克尔 • 克洛佩特(Michael J. Cloppert)和罗翰 • 阿敏(Rohan M. Amin),《在分析敌方行动和入 侵杀伤链基础上受情报驱动的计算机网络防御》(马里兰州贝塞斯塔:洛克希德 • 马丁公司,2010 年)。
[11]参阅博伯特,“对溯源挑战的调查”, 第 41-54 页。 要想参考更全面的研究, 可参阅埃米尔 • 卢波维奇(Amir Lupovici),“溯源问题与‘暴力’的社会建构”,《国际研究视点》,2014 年,第 1-21 页。
[12] Q 有几层含义:首先它暗指问题,这是溯源的关键。Q 还与舵手相关,即负责发出信号和驾驶的海军军官。‘cyber’ 的词根是 κυβερνώ (kyvernó),意指“操纵”。
[13]这个模型有意不设计成一个流程图或清单的样子。在与操作人员的几次专题讨论后,大家都清楚任何一种线性的描 述都不能真正反映出独特性和调查者面对案件的多样性。
[14]大致情况可参阅乔恩 • 林赛(Joe R. Lindsay),“震网及网络战的局限”,《安全研究》22/3(2013),第 365-404 页。
[15]一些形式的犯罪存在例外。证明趋利的动机要比政治动机容易得多。
[16]接受过较为理论性和正式培训如有数学背景的员工可能倾向于程式化解决网络安全问题。这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 理论抽象会掩盖见地的缺失。 受到高度质疑的程式化和人为精确的案例, 可参阅罗伯特 • 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和鲁门 • 伊利耶夫 (Rumen Iliev),“测定网络冲突的时间”,PANS111/4(2014 年 1 月 28 日 ),第 1298- 1303 页。数学公式是入侵分析中广泛使用的模式之一,所谓的“钻石模型”要求的精确度十分夸张。参阅卡尔塔吉龙、 彭德格斯特和贝茨,《入侵分析的钻石模型》。
[17]想大致了解“月光迷宫”,参阅亚当 • 埃尔克斯(Adam Elkus)在希利主编的《一个竞争激烈的领 第 152-163 页。
[18]本文作者与 JTF-CND 以及 FBI“月光迷宫”调查小组的一些前官员进行了访谈,华盛顿特区,2014 年 9 月 -11 月。
[19] 2014 年夏天举行的系列公私部门小组研讨会上,分析人员普遍对线性“清单”提出怀疑。
[20]本文没有足够的篇幅详细介绍这些案例,因此作者为每个案例都提供了最权威的参考来源。这些来源有些是学术出版物,但大多数是企业报告。
[21]埃里克·哈钦斯,迈克尔•克洛佩特和罗翰•阿敏,《在分析敌方行动和入侵杀伤链基础上受情报驱动的计算机网络防御》(马里兰州贝塞斯塔,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10 年)。
[22]拒绝服务攻击是例外,它们通过向计算机系统发送大量基础性且常常是无意义的数据使其中断服务。
[23]乌里 • 瑞弗纳(Uri Rivner),“对一次攻击的剖析”,RSA,2011年4月1日。
[24]根据维基解密曝光的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电报,“2002 年以来,(美国政府)机构受到社会工程式网络攻击”,“数 以百计的(美国政府)和拥有安全授权的国防承包商系统被入侵”。布雷恩•格罗(Brain Grow)和马克•霍森鲍尔(Mark Hosenball),“特别报道:在网络间谍对抗中中国领先”,路透社,2011年4月14日。
[25]尼科尔•帕尔斯(Nicole Perlroth),“隐藏在通风管道和自动售货机的黑客们”,《纽约时报》,2014 年4月8日,A1 版。
[26]例如,“此次‘旁观者攻击’(MITM)是针对谷歌邮件的安全套接层(SSL)吗?”,谷歌产品论坛,http://bitly. com/alibo-mitm+; 还可参阅赛斯•舍恩(Seth Schoen)和伊娃•戈尔佩林(Eva Galperin),“伊朗针对谷歌的中间人攻击表明授权认证存在危险弱点”,电子前沿基金会,2011年8月29 日。亦可参阅尼古拉斯•韦弗(Nicolas Weaver),“近观美国国家安全局最强大的互联网攻击工具”,《连线》,2014 年3月13日。
[27] “Epic Turla 行动”,卡巴斯基实验室,2014年8月7日。
[28]源自2014年夏天作者对多名系统操作员的采访。
[29]参阅考斯汀 • 拉伊乌(Costin Raiu),“走进 Duqu 的命令与控制服务器”,在2012年5月4日于波士顿召开的SOURCE大会上的演讲。
[30]赛门铁克公司有关 Duqu 病毒的报告指出,“Duqu 与震网共用大量代码;然而二者的有效载荷却完全不同。Duqu 不是用来破坏某个工业控制系统,而是用一个具有远程进入能力的程度来取代它。Duqu 的编写者得到了震网的源代码,而不仅仅是编辑过的版本”,“W32. Duqu”,第 1.4 版,赛门铁克,2011 年11月23日。
[31]作者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访问德米特里•艾尔帕洛维奇(Dimitri Alperovich),2014年9月15日,另可参阅《全球威胁报告》,众击公司,2014年1月22日,第18页。
[32]《揭秘“面具”》,第1.0 版,卡巴斯基实验室,2014年2月6日,第46页。
[33]例如,elpais.linkcom[dot] net/and elespectador.linkconf[dot]net,同上,第34页。
[34]同上,第46页。
[35]纳特•安德森 (Nate Anderson) 和赛勒斯•法里瓦尔(Cyrus Farivar),“联邦政府是如何击溃恐怖海盗罗伯茨的”,Ars Technica网,2013年10月3日。
[36]约翰•莱顿(John Leyden),“致使 LulzSec首脑萨布落入美国联邦调查局手中的一个小小失误”,Register 网,2012年3月7日。
[37]丹•维尔顿(Dan Verton),《青少年黑客的忏悔》(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38]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um),“卡珊德拉综合症”,《史密森尼杂志》,43/1,(2012年4月),第 12 页。
[39]伊万卡•巴尔扎什卡(Ivanka Barzashka),“网络武器有用吗?”,《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期刊》,158/2(2013年4/5月),第48-56页,第51页。
[40]金姆•泽特(Kim Zetter),“数字侦探是如何发现史上危害最大的恶意软件震网的”,《连线》,2011年7月11日。
[41]威廉•布罗德(William Broad)等,“以色列测试蠕虫被认为在推迟伊朗核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纽约时报》,2011年1月15日。
[42] 2014年春夏期间,作者在多伦多、伦敦和华盛顿与多名分析家进行交流。
[43]克里斯托弗•德鲁(Christopher Drew),“失窃数据被追踪到对洛克希德的攻击”,《纽约时报》,2011年6月3日。
[44]对该事件的详细描述,可参阅汤姆斯•里德,《网络战不会发生》(牛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29页。
[45]拉夫•朗纳(Ralph Langer),“震网的秘密孪生兄弟”,《外交政策》,2013年11月19日。
[46]杰夫•麦克唐纳(Geoff McDonald),利亚姆•欧默奇(Liam O’Murchu),斯蒂芬•道尔蒂(Stephen Doherty)和埃里克•钱(Eric Chien),《震网0.5:遗漏的关联》,第1.0版,赛门铁克公司,2013年2月26日。
[47]罗纳德•戴伯特(Ronald J. Deibert),拉法尔•罗霍金斯基(Rafal Rohozinski)和西端雅史(Masashi Crete-Nishihata),“网络空间的旋风”,《网络安全》43/1(2012年),第3-24页。
[48] 《“高斯”病毒》,卡巴斯基实验室,2012年8月9日。
[49]参阅大卫•萨马(David Shamah),“新病毒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对真主党发起的数字空袭”,《以色列时报》,2012年8月13日。
[50] 《2014年数据破坏调查报告》,威瑞森公司,2014年4月22日,第23页。
[51]吉姆•芬克尔(Jim Finkle),“独家报道:沙特网络攻击怀疑是内鬼所为”,路透社,2012年9月7日。
[52]吉尔•斯莱(Jill Slay)和迈克尔•米勒(Michael Miller),“从马奇河供水系统被破坏事件中学到的教训”,来自E•格茨(E. Goetz)和S•谢诺依(S. Shenoi)(主编)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第253卷(马里兰州波士顿,斯普林格出版社,2008年),第73-82页。
[53]拉夫•朗纳,“震网的秘密孪生兄弟”,《外交政策》,2013年11月19日。对震网的详细讨论,可参阅金姆•泽特《倒数至零日》(纽约:皇冠出版社2014年)。
[54]克里斯托弗•布朗克(Christopher Bronk)和埃尼肯•提克(Eneken Tikk),“针对沙特阿美的网络攻击”,《生存》杂志55/2(2013年4-5月),第81-96页。
[55]拉夫•兰纳,“震网的秘密孪生兄弟”,《外交政策》,2013年11月19日。对震网的详细讨论,可参阅金姆•泽特《倒数至零日》(纽约:皇冠出版社2014年)。
[56]安德烈•彼得森(Andrea Peterson),“数据被破坏后,易趣要求1.45亿用户更改密码”,《华盛顿邮报》,2014年5月21日。
[57]尼科尔•帕尔斯(Nicole Perlroth)和昆廷•哈迪(Quentin Hardy),“官员称银行黑客攻击是伊朗人所为”,《纽约时报》,2013年1月8日。
[58]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暴风前夕: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纽约:罗塞塔出版社2002年),第415页。
[59]要想全面了解,可参阅金姆•泽特,《倒数至零日》(纽约:皇冠出版社2014年)。
[60] 2014年10月8日,作者在巴塞罗那采访考斯汀•拉伊乌,亚历克斯•古斯德夫(Aleks Gostev),库尔特•鲍姆加特纳(Kurt Baumgartner),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个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1]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2]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互联网,因此更要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支持力度。”[3]这些都体现了中央和国家及高层领导人对互联网创新的重视和其发展价值的高瞻远瞩。互联网创新对我国网络安全、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都具有现实作用,因此客观、科学、有效评估互联网创新以反映我国互联网的创新现状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推进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发展和“双创”工作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关于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数的研究综述
1、互联网行业的创新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众多学者纷纷从互联网产业对经济发展影响、外资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影响、互联网产业组织状况、移动互联网产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如侯合银等(2000)从统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互联网产业对整个国民经的调味品作用;阳洁(2002)从经济学分析了联网产业风险投资的利弊;刘茂红(2011)围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分类、组织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王有为(2011)从技术、商业模式、市场和社会信息化背景等多个维度,分析中日两国移动信息服务业的异同,总结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成功要素。
而具体到以产业创新系统视角研究互联网的学者则较少。目前主要有,我国中科院卢涛等人和华南理工大学陈彩虹等人分别利用产业创新系统和技术创新系统理论对物联网产业和移动物联网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
移动互联网创新系统研究。陈彩虹等(2012)利用技术创新系统的功能动态性分析框架从数据业务前景,终端、基础网络和应用的发展,操作系统应用平台和应用销售平台,中国市场潜力和特殊性,产业资本和风险资本的投入等5个诱导机制,中国产业链不完善,网络带宽、资费,知识产权等创新环境,手机安全等市场监管,人才缺乏等多个障碍机制对知识的创造和扩散、影响发展的方向、创业行为、市场形成、合法化、资源流动、正向外部效应等多个功能的影响等方面实证分析了我国移动互联网创新系统功能的动态性变化,为技术创新系统的功能动态性分析框架提供实证依据,同时为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分析提供理论参考。[4]
综上所述,互联网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其创新发展的要素和机制也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当前研究多将互联网视为一个整体,侧重研究其作为技术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或侧重研究互联网产品、业务或市场行为,而对互联网产业创新理论仍处于初级阶段,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对创新机理和创新模式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当前随着互联网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科学化评估互联网创新能力的研究需求日益紧迫。
2、关于创新指数研究的综述
国内外对创新能力指数的研究颇多,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指数成果。宏观层面有国家间的创新能力研究和对比,如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以国别创新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5]、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以中国创新发展能力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创新指数研究》[6]等。这些国家级的创新指数在指标选择上也具有相对的宏观性、整体性,细分化特征不明显,但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可借鉴意义。中观层面的有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创新发展指数,也有以具体行业为研究对象的创新发展指数,如广东省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指数》[7]以及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国家海洋创新指数》[8]等。相比于国家级的创新指数,城市间或行业间的创新指数的指标体系更具象化。微观与中观的界限有时并不很明确,但相对于中观其指标体现更加细化、范围更加具体,如中小企业创新指数、[9]高校创新指数[10]等。
3、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数的创新
文献研究表明,国内针对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数的可引用研究成果几乎没有。综合以上各类创新指数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宏观还是中观和微观,对于创新指标体系的建立都遵循创新环境、投入、产出和绩效的经典布局。[11]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研究也会遵循这样的思路,但是互联网行业有更加鲜明的行业属性。如互联网创新的草根性更强,传统形式的教育投入不能直接代表互联网创新能力;互联网创新的方式很多,技术、商业模式等,论文不是重要的考量方式;互联网创新的受众很广泛,几乎是所有网民用户和企业。正是因为互联网行业创新具有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所以构建的指标体系需要有别于传统的创新体系,又要能够反映互联网行业创新,且能够获得数据。这是本次互联网创新指数具有创新的地方,也是具有挑战的突破。
互联网行业是当前全球最热门的领域,互联网被赋予了很多的创新角色,其自身具有创新性,且依靠互联网行业也可以带来创新。即互联网行业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互联网行业是指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基础,利用网络平台提供服务并以此获得收入的行业,狭义的是指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信息和服务而获得收入的行业。本论文研究的是狭义概念下的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情况。这主要是基于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基础性和重要性特征,它的创新发展对支撑“互联网+”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的内涵不仅仅在于对行业数据进行统计测算,我们希望通过最终数据来反映互联网行业各创新层面的发展现状,以数据的增长或降低来寻找其背后的原因或问题,为以后的创新调整提供参考。同时,我们还希望在这套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正或创新,能够构建出更多的指标体系,以此辅助各种层面的监测和研究,对未来的发展形成周期性的成果,为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指数是反映研究对象发展的参考值,作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可以为不同领域的用户比较直观和清楚了解某一领域的发展提供帮助,具有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但不具有完全指导公共政策制定或修改的功效。
对于互联网创新的理解和定义是构建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标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想法、概念,到策划产品,再到用户需求和市场回报,还包括很多他的外围因素。互联网行业创新是指根据外部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互联网行业将自身及相产业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并引入产业内部,以术创新为基础,组织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等创新行为为主要内容,使互联网行业竞争力断增强的过程。由此可认为,所谓互联网行业新系统就是指,以互联网市场需求为动力,以互联网企业为主导,以相关知识和技术共享为核心,通过产业内部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并引入互联网行业体系,推动互联网行业不断创新发展,从而使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有机系统。
本文基于创新链这条主线,结合周围的生态进行了一级指标的选择,最终确定了6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创新动力基础、创新社会环境、创新经济价值、创新资本动态、创新活跃领域和创新成果效益。其中,创新动力基础是考虑互联网创新依赖用户和企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新的成果需要用户体验;创新社会环境是互联网创新的客观外在条件;创新经济价值表明企业的创新成果被社会认可的程度,是创新经济利益的体现;创新资本动态反映了社会资本对互联网创新的关注和参与热度;创新活跃领域反映了当下互联网行业具有创新活力的细分领域,代表了互联网的热点;创新成果效益体现了互联网创新活动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效果影响。
鉴于选取指标的覆盖性、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了18个二级指标,构成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数的评价体系。通过对这些指标数据的测算,希望可以反映互联网行业的创新现状、质量和能力及问题。指标架构体系如表1:
表1: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标体系权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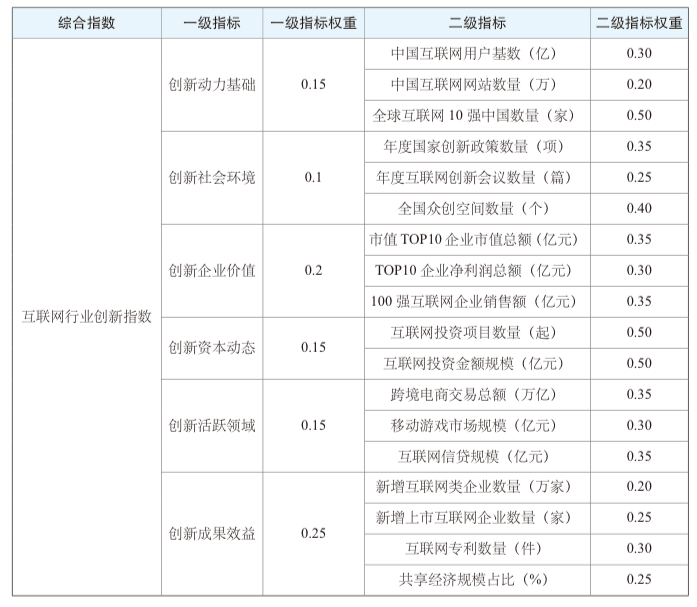
1、确定指标评价权重
权重的合理分配是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科学评价的关键,因为各个指标不同的权重会导致不同的评价结果。目前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12]主观赋权法的各指标主要有专家根据经验和主观判断得到,如德尔菲法、功效系数法等,其缺点是忽视了评价指标数字特征本身所蕴含的信息以及易受专家的知识、经验、偏好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客观赋权法的各指标权重是由各指标在被评价对象中的实际数据决定的,如变异系数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其缺点是仅仅以数据说话,忽视了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有时会出现权重系数不合理的现象。本文的权重初始分值是以问卷的方式征询了近20位业内专业人士获得,包括互联网企业管理者(创业者)、互联网发展研究人员、互联网法律专家以及政府互联网管理人员等。后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了反复修改和调整,最后形成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标体系。
2、综合评价模型与评估算法
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评估采用标杆分析法。此方法是国际上采用比较广泛的一类评估方法,原理是:给被评估对象确立基准值,并以此标准衡量所有被评估对象,从而发现不同时间段的差距。
(1) 原始数据采集路径方式
本互联网创新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18个二级指标,其原始数据主要有以下来源:政府官方机构、互联网领域行业机构、互联网企业财务报告、业内专业研究机构等。该18项三级指标都是硬数据,需要逐一采集,没有单纯依靠专家打分评估的指标数据。
(2) 数学模型和评估推算演示[13]
评价模型是评价指标与评价目标之间逻辑关系的数学表达式,某项指标数值越大,同等情况下对创新指数的贡献率也越大,即评价目标与评价指标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
通常指标的增速或发展速度是以基期年份指标值作为基准进行比较的。在某一指标体系中,如果按照通常方法计算各指标的增速后进行加权平均,由于可能存在某些指标增速过高(或过低)的情况,这样就会造成指标增速之间不可比(即增速过高或过低的一些指标的作用掩盖了其他指标的作用),从而造成整个指标体系失真的现象。因此,必须采用对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增速的范围进行控制的方法。一种较好的方法是将指标增速的基准值设定为该指标的两年平均值,这样计算出来的各指标增速的范围可以控制在[-200,200]的区间内。本指标中,18个指标都是正指标。
(2-1)各指标相邻年份的增长速度计算方法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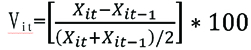 ,其中i为指标序号,t为年份,t≥2014。
,其中i为指标序号,t为年份,t≥2014。
(由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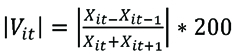 而|Xit-Xit-1|≤|Xit|+|Xit-1|,对于Xit的>0和
而|Xit-Xit-1|≤|Xit|+|Xit-1|,对于Xit的>0和
Xit-1>0,有|Vit|≤200)。
合成各级指数和总指数的算法
(2-2)指数合成方法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计算二级指标的加权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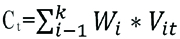 ,其中Wi为各指标对所属领域的权重,k为该领域内指标的个数为年份,t≥2015。
,其中Wi为各指标对所属领域的权重,k为该领域内指标的个数为年份,t≥2015。
第二,计算定基累计发展一级指标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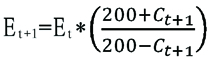 ,其中t为年份,t≥2014,E2014=100。
,其中t为年份,t≥2014,E2014=100。
在计算指标体系中的某一个指标的定基发展速度时,如采用这一方法,其结果与通常方法一致,即指标当年的定基发展速度等于该指标上年的定基发展速度与当年发展速度的乘积除以100,当年的定基发展速度等于指标当年值乘以100与定基值之比。这是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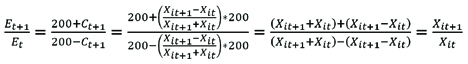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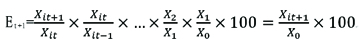
第三,计算定基累计发展总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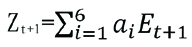 ,其中t为年份,ai为各项一级指标对总指数的权重。
,其中t为年份,ai为各项一级指标对总指数的权重。
表2: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测算结果(2014-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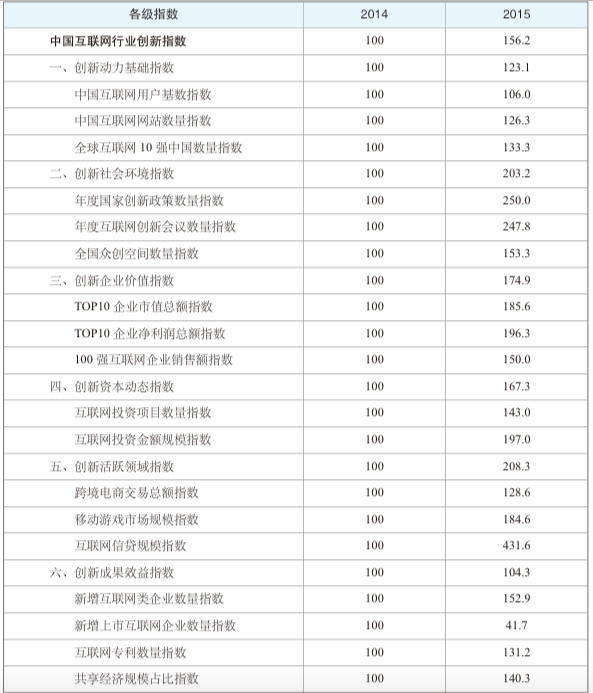
根据以上提出的互联网行业创新指数的体系指标数值和评价模型,我们测算出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为156.2,2014年创新基数为100。
1、创新动力基础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动力基础指数为123.1,增长平稳。用户是创新的动力基础,随着我国网民用户数规模增长进入瓶颈期,国内市场增量变小,互联网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行业创新的新课题。进入全球TOP10的互联网企业又增加了1个,TOP20的数量达到了12个。这些互联网企业是国内创新的代表,也是走出去发展的典型,它们的成长能够为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提供可参考的标杆和动力。
2、创新社会环境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社会环境指数为203.2,增速极快。近两年,我国相继提出了“互联网+”战略、“双创”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行动,专项会议和配套的政策文件为整个互联网行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极优的政策环境。政府的支持态度传递到民间表现在与互联网创新相关的会议数量明显增多,全国各个地方都在积极部署互联网创新工作。政府和民间联动达到了“1+1>2”的效果,为互联网创新提供了好的氛围,值得肯定。
3、创新企业价值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企业价值指数为174.9,增速显著。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它们创新的成果体现在其经营效益指标增长和投资者或机构对其成长能力的认可评价。2015年互联网上市企业的经营指标整体表现出色,企业销售额和利润均有较高的增长。排名前十的互联网上市企业市值多比2014年有明显增长,证明市场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保持认可和有信心。
4、创新资本动态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资本动态指数为167.3,增速明显。资本具有逐利性,看重创新能够给它带来的高收益,它们的表现是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表征。指数表明,2015年我国社会资本在互联网领域的活跃度很高,投资了很多初创型或成长型具有创新模式的企业。虽然有一些企业最终会在市场的竞争中消失,但是资本愿意为企业的创新试错也表现出了市场对创新的容忍度提升,这本身就是有利于创新的表现。社会资本的活跃也与政府创新政策的支持有关。
5、创新活跃领域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活跃领域指数为208.3,增速极快。此次选取的跨境电商、移动游戏和互联网信贷三个领域分别属于电子商务、网络游戏和互联网金融领域更加具有创新特征的代表。网贷在2014年兴起,2015年集中爆发,增长速度远高于成熟度较高的跨境电商和移动游戏。由于跨境电商正面临这新的管理措施,会对它们的创新发展带来新的影响。网络信贷在创新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良案例,出现了诈骗集资等恶劣行为,估计管理层会对这一创新领域进行规范,创新发展的速度会回归到理性范围。
6、创新成果效益指数解读
201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成果效益指数为104.3,增速较慢。创新的成果效益最被大家关注,从专家的权重打分中可以看出它被赋予的权重最高。但是,尽管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政策和资本的助推下表现异常热闹,在事关具成果效益的指标方面表现相对冷清。创新成果益中四个指标的指数值中有一个小于100,说2015年我国互联网行业新增上市企业数量已比2014年少。但新增互联网企业的指数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表明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到了新的问题,创新的主体不能被更广泛的资市场接受。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共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仍可圈可点。
本文从六个方面构建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运用标杆法测算了2015年的创新指数。结果显示,将2014年中国互联网创新能力指数设定为基数100,2015年的创新指数为156.2,增速明显。表明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能力保持着积极上升的良好态势。根据一级指标的指数可以看出,创新社会环境和创新活跃领域指数的增长热度偏高,创新企业价值和创新资本动态指数的增长适度,而创新动力基础和创新成果效益指数的增速缓慢。说明我国互联网行业当前的创新能力生态仍不均衡,政策刺激程度比较高,一些新出现的创新领域在监管政策不明确的条件下短时间内过于火热,一些利用创新进行非法行为的现象和伪创新情况仍集中存在。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也面临着企业创新不但要坚守国内市场,也需要走出去做大全球化市场的现状。企业自身需要走出去,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高的认可、在产品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国外用户。创新成果的提升仍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我们认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能力发展会保持良好的上升态势,但要避免陷入对政策的过分依赖和政府利用资源主导,而应由政府引导并在提供好的公共服务措施前提下同步做好监管预案,让社会资源积极主动和简便高效参与到互联网的创新进程中。
论文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指数的提出是一次创新,一些细节仍值得探讨。如关于创新活跃领域指数的设计,该指标是体现创新的重要参考,但是由于每年的活跃领域都会发生变化,对指标的连续性带来挑战。我们也初步提出了解决方式:第一,在后期的指标采集过程中可以继续加入新的活跃领域,保留原有的创新指标,但通过降低权重的方式减小其对新指标的干扰;第二,设定一个具体标准值,当新的创新领域指标值符合要求时引入,同样当原有的创新领域指标值不符合条件时删除。
作者简介
黄澄清:硕士,北京大学EMBA毕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兼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通信学会互联网应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化部进口游戏审查委员会委员。
张静硕士,北京化工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互联网治理,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特色的网络治理演进历程和治网之道——中国网络治理史纲要和中国路径模式的选择》、《即时网络时代的传播机制与网络治理》、《基于网络舆论场的微信与微博传播力评价对比研究》等。
谢程利(通讯作者)博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部主任助理。
参考文献
[1]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全文),http://www.caixin.com/2015-10-29/100867990.html
[2]习近平:支持互联网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创新主体产业主体,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4-20/7840897.shtml
[3]多措并举,促进互联网企业持续健康发展,http://www.qstheory.cn/wp/2016-04/26/c_1118736085.htm
[4]陈彩虹,朱桂龙,许治 . 中国移动互联网创新系统功能动态性分析 [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12,32(4)
[5]《国家创新指数 2014》发布,http://www.most.gov.cn/kjbgz/201507/t20150708_120616.htm
[6] 2014 年中国创新指数为 158.2,http://www.gov.cn/xinwen/2015-12/30/content_5029478.htm
[7]广东省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创新指数》http://www.cssn.cn/skyskl/skyskl_cgzp/201603/t20160304_2897657.shtml
[8]刘大海、王春娟、李晓璇、冯磊 . 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构建与评估研究 [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 年 12 月第 24 期 32 卷, P114-119
[9]曹萍,陈福集 . 基于 ANP 理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模型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2):667-71
[10]卢方元,张利平 . 高校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J]. 科技管理研究,2010(5)51-53
[11]宋卫国,朱迎春,徐光耀,陈钰。国家创新指数与国际同类评价量化比较 [J]. 中国科技论坛,2014 年 7 月第 7 期, P5-9
[12] Ding JD, Qiu JP. An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Indicator Weigh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s [J]. Scientometrics,doi:10.1007/s11192-010-0268-7
[13]马克 •E• 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版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index of China's Internet industry
HUANG Cheng-qing ZHANG Jing XIE Cheng-li
Abstrac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is a major opportunity for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t is bound to profoundly affect and reshape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ative princip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index system of China Internet industry, from the foundation,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novation of economic value, innovation capital dynamic and active innovation field and innovation benefit .
This paper uses AHP method to evaluation the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net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 China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some new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value and innovation capital enhanced one another's ability; innovation power base and innovation benefits developed bothsteady.
Key Words: Innovation of the Internet; innovation ability; index system
( 责任编辑:钟宇欢 )
TOP1:《自由与权威的斗争》
《科学与工程伦理》2015年10月发表英国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教授玛利亚罗萨莉亚•塔迪欧的文章《自由与权威的斗争》。作者认为,信息社会正面临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斗争,表现出来的是网络安全与公民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个人权利被清晰界定,并且不能从信息时代个人福祉中分割,才能在网络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保持平衡。随后作者分析了个人福祉,界定了个人可以自我主张的权力,并提出了如何在个人权利和网络安全之间达成平衡的建议。
TOP2:《太空,网络安全的最终前线》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网站2016年9月发表戴维•利文斯通和帕翠西亚•刘易斯研究员的研究论文《太空,网络安全的最终前线》。论文指出,卫星和其他数字关键基础设施一样非常容易受到网络攻击,会对地面的关键基础设施带来重要的风险,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危。
TOP3:《网络空间,恐怖主义和国际法》
《冲突与安全法》杂志2016年夏季号发表戴维•菲尔德的文章《网络空间,恐怖主义和国际法》。文章认为,互联网一直就被认为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但国际社会并没有就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制定相应的国际法。文章分析了国际法与恐怖主义的网络攻击,网络行动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结论——当恐怖主义在网络空间中成为全球性危机时,国际法的前进是最不明确的。
TOP4:《加密和主权》
英国《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杂志(Survival:GlobalPoliticsandStrategy)2016年10月号发表BenBuchanan的文章《加密和主权》。文章指出加密技术的广泛使用打破了国家安全与隐私之间的平衡,给执法机关和情报机关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今后加密问题将会在法律、应用数学和国际关系三个领域引发很多问题。
TOP5:《国际网络接触:保护关键基础设施》
《乔治城国际事务论坛》2015年第10期发表哈佛大学贝尔福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玛丽莎•哈撒韦的文章《国际网络接触: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作者认为,关键基础设施面临的风险在增加,而应对的手段则很有限。美国定义了16类关键基础设施覆盖了能源、交通、金融等很多领域,但现在需要重新定义以便集中精力保护最核心的网络基础设施。(本期推荐人:鲁传颖)
TOP 1:《网络战:信息空间攻防历史、案例与未来》
作者:[美]保罗•沙克瑞恩(Paulo Shakarian),亚娜•沙克瑞恩(Jana Shakaria)著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金城出版社第一版(2016年9月1日)
译者:吴奕俊等
本书选取了最为熟知的经典网络攻击案例,进行了手术式的详细解剖,让我们可以超越故事进入到网络攻击的实际操作之中,的确有着教科书般的精细。毕竟,网络领域的战争在本质上是一场技术战。两位作者一位都是网络安全专家,一位是现任西点军校计算机学助理教授。一位是网络战独立研究学者。本书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作者有机融合理论与实例,涵盖了从个人、组织机构到国家的网络安全问题,细致阐述了网络空间的生存之道。全书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既可供信息技术与军事人士研读,也是普通读者的必读佳作。当然,对于非专业人士,尤其是期望欣赏网络战的各种传奇故事,本书就显得有些枯燥。可惜与英文版相比,涉及中国相关的整整一章内容没有呈现,不能不说是遗珠之憾。要看这一章大家还得读英文原版。
TOP2: 睡鼠说:个人电脑之迷幻往事平装
作者: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第1版(2015年7月1日)
译者:黄园园
坚守30多年不退却,约翰•马科夫堪称骨灰级的科技记者,贯穿整个PC革命和互联网革命。最近他的兴趣点是人工智能(新近出版了《与机器人共舞》一书)。如今,无论是互联网还是PC的历史书写,都被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商业成功学主导,心灵鸡汤成为主菜。但是,史实并非如此。“受益于个人电脑产业带来的数不胜数的便利之处,人们却淡忘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个人电脑产业的奠基人并不是那些企业家,而是一名政治激进分子和一群普通电脑玩家,而他们的初衷只是分享信息而已。”反主流文化浪潮是PC乃至互联网诞生的真正母体,显然,马科夫的这本个人电脑史别有思想,富有启蒙价值。
TOP3:《成为乔布斯》
作者:布伦特•施兰德、里克•特策利合著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中信出版集团第一版(2016年10月1日)
尽管销量巨大,名震一时,但是真实的乔布斯不在生前授权由沃尔特•艾萨克森撰写的《乔布斯传》中,而更在这本《成为乔布斯》。为什么本书得到包括CEO库克以及设计总监乔尼•艾维在内的乔布斯的密友们认可,作者Brent以一个交往25年的老友的身份向我们揭开表象之下有血有肉、更加温情的乔布斯。但是,谁能说好朋友的视角就是最真实的?当然,比起读完感觉不同之处还是很明显的,艾萨克森是传记专业户,但是本书作者却是长期跟踪苹果的资深科技记者,属于业内行家,对技术和业界的各方故事都比较了解。更重要的当然还是作者对乔布斯是有感情的。不过,与诸多乔布斯传记相比,本书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新发现新爆料,很多故事都已经耳濡目染,即使是描写乔布斯的缺点方面,你也一样觉得挺混蛋的。因为艾萨克森的传记是乔布斯钦点的,如此成功,本书摆出与其对抗之势,更多还是出于市场营销目的。
TOP4:《第四次革命: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
作者: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版(2016年4月1日)
译者:王文革
继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神经科学革命之后,人类迎来的自我认知的第四次革命——图灵革命,整个世界正化身为一个信息圈,每个人都生活在云端,人类已不再是信息圈毋庸置疑的主宰。人类进入超历史时代,并引爆人工智能的飞跃式发展。信息哲学开创者、旅英意大利学者、牛津大学哲学与伦理信息教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从时间、空间、身份认同、自我认知、隐私、人工智能、智能体、政策、环境和道德等核心概念为我们解析了新时代的新特性。作者试图上升到哲学层面回答我们未来的方向和命运。比起他上一本《信息哲学》以及其他多本著作来说,思考得更加深入也更加接地气一些。当然,作者的学者身份决定了这不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商业读物。
TOP5: 断点:互联网进化启示录
作者:杰夫•斯蒂贝尔(Jeff Stibel)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5年1月1日)
译者:师蓉
好书的最高标准就是开启你全新的思想空间。脑科学家杰夫•斯蒂贝尔告诉我们,神奇的互联网也难以摆脱基本的自然规律,必将经历增长、断点到平衡的三阶段。这是一本饶有趣味的书,结合了神经学、生物学与互联网技术:我们是如何通过生物学上的前车之鉴,来预测互联网的发展。本书乌鸦嘴一般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所有的网络都必经历崩溃式的断点。无论是蚁群、大脑还是互联网,核心问题是断点之后是毁灭还是重生?作者通过现象、语言与镜像神经元,解析互联网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问题。断点问题当然是天大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本期推荐人:方兴东)
TOP1《零日漏洞:震网病毒全揭秘》Countdown to Zero Day: Stuxnet and the Launch of the World's First Digital Weapon
作者:Kim Zetter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Publisher:BroadwayBooks;September1,2015
无论在网络战发展史上,还是国际关系层面,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攻击的震网事件,都是里程碑式的。震网病毒作为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已知的,以政府为背景的网络武器,利用巧妙、精心设计的机制,对伊朗核设施成功进行攻击。这个事件通过《纽约时报》2012年6月首次披露,迄今各种传说和演绎,充斥着阴谋论和想象力。Kim Zetter著作《零日漏洞》让我们重温震网事件,是目前关于震网病毒入侵伊朗核设施事件最为全面和权威的读物。全书共分为序幕和19个章节,基于广泛采访事件相关人物,多方收集一手信息,包含了大量之前从未被披露过的有关震网的信息。作为一名独立记者,Kim Zetter曾经为《连线》杂志写过100多篇文章,本书基于卡巴斯基实验室全球研究与分析团队成员的采访,精心梳理而成的一本非小说类著作。2016年,中国读者可以先欣赏基于本书完成的纪录片《零日攻击》。
TOP 2:《摧毁式力量:数字时代国家政权的危机》Disruptive Power: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Age (Oxford Studies in Digital Politics)1st on
作者: Taylor Owen(Author)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Publisher:OxfordUniversityPress;1edition(April1,2015)
一切坚固的都在烟消云散,尤其是为我们生活中提供最根本保障的那个国家机器,如今陷入危机边缘。泰勒•欧文(Taylor Owen)用3年时间完成了《破坏性力量:数字时代国家政权的危机》一书,为我们剖析了互联网与国家这对冤家的爱恨情仇,展示了数字技术和国际关系的复杂关系。本书从2012年美国联手各国情报机构针对“匿名者”的反击开篇,分析了互联网对于传统权力机构的冲击:政治、外交、经济、媒体控制、人道主义救援、战争等多个方面,这些基础性权力机构遭到削弱和破坏,使得民众以及全球秩序置身于新的危险境地。国家和传统组织机构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以适应变化,积极主动应对挑战毕竟国家和传统大型组织仍然掌控着人类社会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控制权力。
TOP3: 《黑暗领土:网络战的隐秘历史》Dark Territory: The Secret History of Cyber War
作者:Fred Kaplan(Author)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Publisher: Simon& Schuster(March1,2016)
本书可以当做美国网络战历史的深度通用读物。安全领域资深记者、Slate网站军事问题和政策评论员弗雷德• 卡普兰(Fred Kaplan)在最新著作中,深入美国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超机密网络组织、美国军方以及白宫等最神秘的内部世国网络战漫长的隐秘历史。野心勃勃地讲述了诸多有名有姓的英雄与恶棍,这些善恶难分难解的各色人等演绎的地改变了网络空间的基本格局。在安全与危险之间,在进攻与防御之间,美国政府始终扮演着最特别的角色。本书新料不少,引人入胜。
TOP 4:《网络交战:互联网军事复合体的崛起》@War: The Rise of the Military-Internet Complex Paperback
作者:Shane Harris(Author)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 Eamon Dolan/Mariner Books; Reprint edition(November3,2015)
网络安全、网络战争和互联网军事复合体的崛起是肖恩•哈里斯(Shane Harris)著作《@War》的主题,作者描述了情报机构正在努力打击网络攻击,保护美国公民。但是又试图主宰网络空间,引发了更严重的后果。作为反对全球范围大规模监控的著名记者,哈里斯曾经获得过“全美35岁以下最佳记者”等荣誉称号,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FBI与国家安全局的象征关系,称二者结合将破坏互联网的匿名性。他认为虽然国家安全局向电话和互联网公司付费创建它们的网络以便自己进入,故意降低密码标准,设法破坏洋葱网络,但FBI才是使国家安全局国内活动成为可能的机构。当媒体说国家安全局监视美国人时,他们实际是说FBI帮它做到了这一点,为其国内情报活动提供技术和法律基础设施。目前他在新美国基金会担任研究员。
TOP5:《暗网:数字地下黑社会揭秘》The Dark Net: Inside the Digital Underworld
作者:Jamie Bartlett (Author)
出版社和出版时间:Melville House; Reprint edition (May 10, 2016)
我们日常使用和熟悉的互联网其实属于“明网”,而在明网之下,隐藏着一个流淌着欲望的所在——“暗网”,依托于 暗网的匿名性,人性的黑暗在这里肆意发泄:毒品交易、军火和人口交易等。暗网作为一个全新的大陆正在迅速崛起,并且 开始挺进主流社会。《暗网》作者 Jamie Bartlett,目前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进行研究。他对暗网进行了深刻调查,了解各种非 法行为,以及更多不为人知的黑暗面。本书解释暗网的含义以及暗网的发展趋势,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暗网,预见互联网的 未来。作为 demos 互联网中心社交网络分析中心的领导者,作者最近在研究秘密机构的监察和反监察技术和科学情报服务机 构的社交网络使用。(本期推荐人:方兴东)
TOP1:《美国人事局数据泄露报告》《The OPM Data Breach: How the Government Jeopardized Our National Security for More than a Generation》
作者:美国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发布时间:2016年9月7日
2015年7月,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OPM)公开承认曾遭到两次黑客入侵攻击,造成现任和退休联邦雇员超过2210万相关个人信息和560万指纹数据泄露,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数据失窃事件,使得紧张的中美网络冲突进一步白热化。2016年9月7日,美国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公布了OPM数据泄漏案的调查报告,这份241页的报告详实地分析了整个事件过程和原因以及关键事件节点。不过与当时媒体众口铄金地归罪于中国政府的基调不同,其最可贵之处在于更多的自省。报告认为OPM领导不力,从根本上缺乏防患于未然的意识,虽然多年来一直受到信息安全警告,但却从未采取有效行动保护其存储的大量敏感数据。
TOP2:《与中国在网络空间达成共识》Getting to Yes with China in Cyberspace
作者:美国兰德公司发布时间:2016年5月
报告全文121页,功课做得非常扎实,堪称中美各方观点大汇聚,探讨了几个关键问题: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优先领域、双方的条件、可行的路径等。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当前中美双方网络空间的核心分歧在于认知差异,围绕中美网络安全关系困局,分析了美国利用协议和行为规范管控中美网络安全关系的政策选项,在避免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实施攻击或情报活动方面,有望促成一套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的达成,还提出了相关建议措施。报告最后评估,现阶段除非美国就网络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否则中方改变现状、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动力明显不足。
TOP 3:《斯诺登评估报告》Review of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s of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Contractor Edward Snowden
作者: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发布时间:2016年9月15日
就在电影《斯诺登》公映前一天,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党委员无异议通过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于16日在美媒公布。这份36页的报告详细阐述了斯诺登2013年窃取150万份敏感文件的事件。这份报告历时两年,从公开的3页报告概要看几乎毫无新意,精彩之处。报告试图为斯诺登本人盖棺论定,结论是:首先是确认斯诺登确实给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危害”。第二,斯诺登并不是揭发者。第三,美国国家安全局管理人员曾与斯诺登发生口角,斯诺登因此受到批评,随后开始大量下载机密文件。第四,斯诺登曾多次撒谎或者严重夸大事实。法新社17日称,报告的核心内容试图将斯诺登描绘成一个心怀不满的员工,经常与主管起冲突,暗示斯诺登此举是为了报复主管。斯诺登当然在第一时间给予了反驳。
TOP 4:《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作者: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技术委员会
发布时间:2016年10月13日
10月13日,美国总统办公室发布了两份重要报告:《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策略规划》。标志着人工智能领域成为这个时代新型的军备竞赛。报告结论认为,如果业界、公民社会、政府和公众共同努力,管理其风险,那么人工智能就将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驱动力。报告最主要的干货是最后的23条建议措施,类似于中国政府部门最喜欢频频发布的行动计划,看来美国政府和任期进入最后尾声的跛脚总统奥巴马也不闲着。为了配合报告发布,奥巴马还特意接受《连线》杂志采访。问到美国是否将要成为超级网络霸权的角色,奥巴马说:“我们愿意克制自己,只要你也愿意克制自己。”
TOP 5:《新加坡网络空间安全战略》Singapore's Cybersecurity Strategy
发布时间:2016年10月10日
10月10日,在为期3天的新加坡国际网络周(SICW)开幕式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正式宣布了新加坡的网络安全策略报告。网络安全是新加坡数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该策略提出了新加坡网络安全的愿景、目标和要点。这份27页的报告图文并茂,逻辑清晰,整体内容简洁明快,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建立强健的基础设施网络;创造更加安全的网络空间;发展具有活力的网络安全生态系统;加强国际合作。新加坡地理空间虽然小,但是在网络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2015年4月1日新加坡成立网络安全局,隶属总理府,整合了新加坡资讯通信科技安全局与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的部分职责,统筹各政府部门的网络安全事宜。(本期推荐人:方兴东)

G20国家包括19个独立国家和1个国家组织,分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南非、沙特阿拉伯和欧盟。

图1:G20国家分布图
G20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到全球总人口的64%,国土面积之和占到全球各国总面积的60%,网民数量占全球网民总量的70%,GDP之和占全球总和的86%,贸易总额占全球总和的80%。可以看出G20国家无论是在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以及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方面都已经可以代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是全球发展的缩影。所以,通过了解G20互联网的发展,可以对全球互联网动态有初步认识。
1、欧美国家互联网普及率高,中国仍具有增长潜力
根据Internet Live Stats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7月1日,G20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均值达到69%,与阿根廷国家69.2%的互联网普及率相持平。其中欧洲的英国互联网普及率最高,92.6%;其次为日本的91.1%。从整体上看,发达国家的普及率已经到达天花板,上升空间有限;发展中国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也面临着受人口文化水平限制带来的普及难点。对比美国和欧盟国家,都拥有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但是美国在互联网产业方面发展比欧盟国家更加具有突破性和发展性,双方之间的发展分化越来越明显。中国作为新兴互联网大国,有网民人口优势,也积累了一定的产业优势,但是走出去发展的势头和基础仍不是很充分,需要继续坚持走出去的战略,不能仅走依靠国内人口红利支撑企业发展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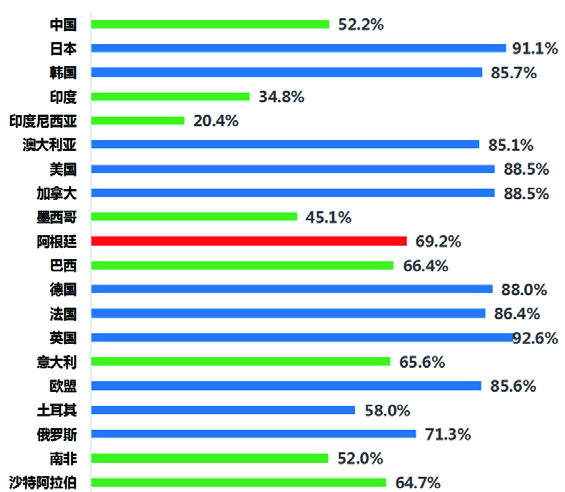
图2:G20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对比图
2、印度成网民增速最快市场,未来潜力巨大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G20国家网民增速除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土耳其之外,其他国家的增速均低于6%,多为1%-4%之间,表明全球互联网用户规模发展已经处于缓慢阶段。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后,正在面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局面,网民增长速度出现瓶颈。
印度以51.9%的增速高居榜首,显示了印度网民增长速度快,同时也有印度网民基数小的缘由,与几年前的中国发展有很强的相似性。当下印度政府正在推动互联网基础建设,会让同样具有人口优势的印度在未来几年发掘出巨大的市场潜力。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新生代网民形成的主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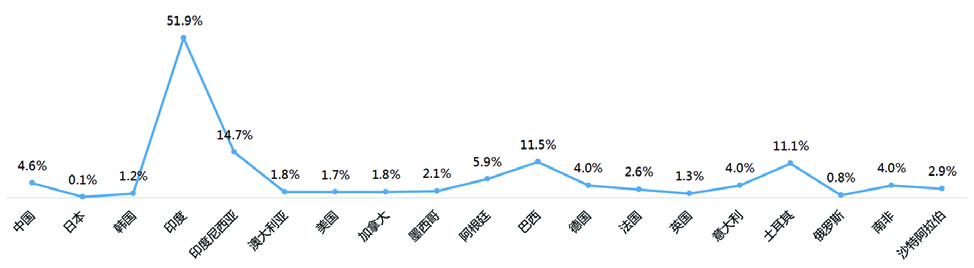
图3:2015年G20各国网民数量增速对比图
3、30亿互联网用户上半场结束,下半场30亿开始
截至2015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超过30亿,占到全球总人口的40%;其中G20国家网民用户数量达到22.4亿,普及率为50.2%,高于世界平均值。中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7亿,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普及率已经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达51.7%。纵观全球互联网用户发展的历程,从1990年互联网民用化开始到达到第一个10亿网民用了16年的时间,达到第二个10亿网民用了6年,
达到第三个10亿网民用了4年。至此,全球30亿网民的上半场已经结束,未来30亿的下半场开始。
随着用户接入互联网方式的不断变化和未上网人群的客观因素制约,第四个10亿网民的成长速度到底是会被再次缩短还是会被拉长仍未可知。
4、支持60%非上网用户发展,缩小数字鸿沟
从下图的走势情况可以看出,G20国家网民数量的增长主要有两个明显的波动,第一次是在2000年到2002年,正是互联网固网快速普及的阶段,第二次是在2009年到2011年,正是移动互联网兴起并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从总的走势图看,G20国家网民占总网民数量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未来网民的增长重点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需要支持剩下的60%未上网的潜在用户,关注他们的需求,为减小数字鸿沟作出共同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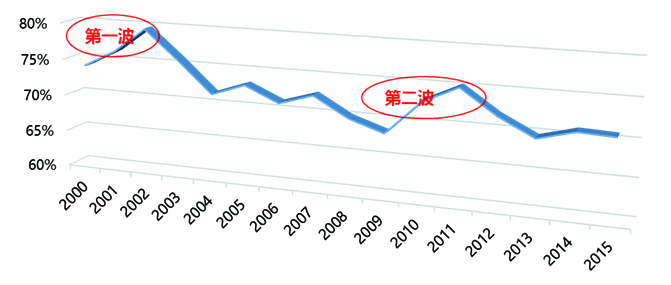
图4:G20国家网民数量占全球网民总数比例波动图
1、网络社交差异化明显,中国面临突破阻力
根据We are social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G20国家网络社交的平均水平为48%,高于31%的全球平均水平。其中,韩国的网络社交水平位居第一,达到了76%,其拥有全球最快的平均网速为网民使用社交网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印度虽然作为Facebook、Whatsapp等全球社交媒体的重要市场,但其本土社交平台的应用市场较小。中国网络社交水平高于全球但略低于G20平均水平,社交普及率已接近互联网普及率,需要突破上升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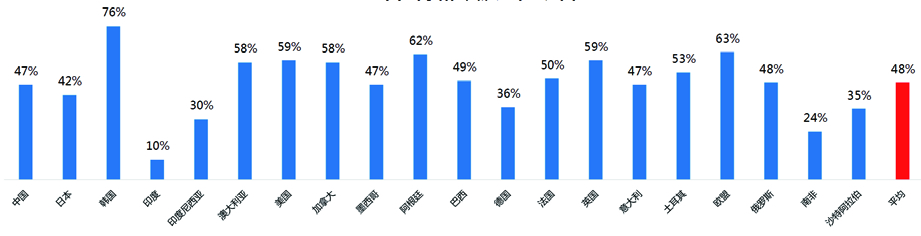
图5:G20国家网络社交渗透率对比图
2、社交平台TOP3对比,Facebook成赢家
对照G20各国社交平台的前三名,可以发现Facebook和Facebook Messenger以及Whatsapp出现的频率最高,说明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工具已经获得G20的市场优势。但其中也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现象存在,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的本土社交工具在本国占有优势地位,虽然Facebook也进入了相关市场,但并没有能够突破本土品牌的市场优势。中国社交市场的TOP3产品均为本土品牌,说明在中国市场国内品牌可以免于国外品牌的竞争,但是在国外市场的竞争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甚至中国品牌还没有走出国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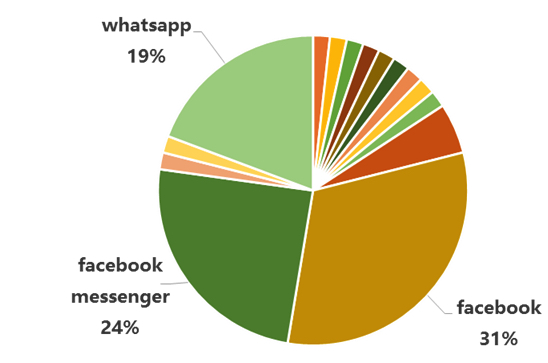
图6:G20各国前三名社交平台的占比
3、电商发展美国领先,中日竞争显著
美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以绝对优势领跑G20国家,B2B和B2C市场的交易总额达到了65830亿美元,中国和日本分别达到了27010亿美元和24940亿美元。其中,美国和日本的B2B发展明显优于中国,而中国的B2C发展则明显优于它们。
从整体上看,受各国网民用户数量、消费习惯等多因素影响,G20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分化明显;印尼、阿根廷以及沙特等国家发展水平较低,与网民消费习惯转变和对电子商务缺乏安全感有关。
4、中美在全球零售电商市场已处于两强并列
根据Internet Retailer推出的《全球1000强:全球零售电商的革新》报告,2015年全球零售电商易总额达到了1.74万亿美元,并在过去三年平均保持每年20%的增速;中美日三国的电商企业占据全球十强,总交易额达到全球的54.8%,超过一半,其中美国有5强、中国有4强、日本有1强。阿里巴巴、亚马逊和eBay的交易总额超过TOP10总额的80%,阿里巴巴领先亚马逊优势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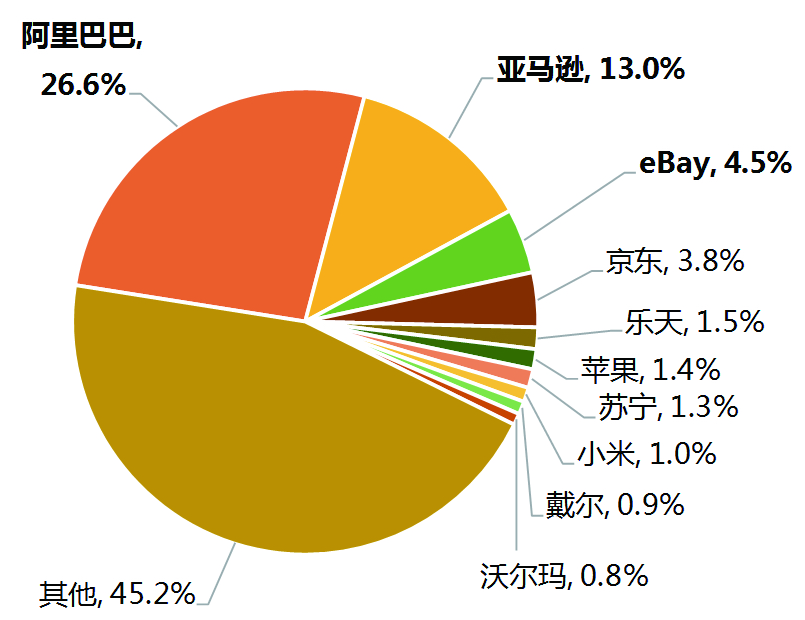
图7:2015年全球电商交易额占比排名图
5、G20互联网经济对比,中国超发达国家均线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统计数据,2016年G20国家发达市场的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为5.5%,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4.9%。其中英国的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优势最为明显,以12.4%位列第一,说明其已是一个数字商业化国家;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为6.9%,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互联网经济GDP占比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除中国外,互联网服务依赖于美国企业进口
G20各国互联网流量TOP10中,仅中美两国完全由本土企业供应服务;德国和加拿大,全部依赖于美国互联网公司,没有本土进入TOP10;韩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的本土与美国互联网企业各占据半壁江山,本土企业提供博客、新闻门户服务;除巴西新闻门户基于地缘位置辐射阿根廷与墨西哥外,G20的TOP10互联网服务几乎均依赖于美国互联网企业进口,语言对互联网应用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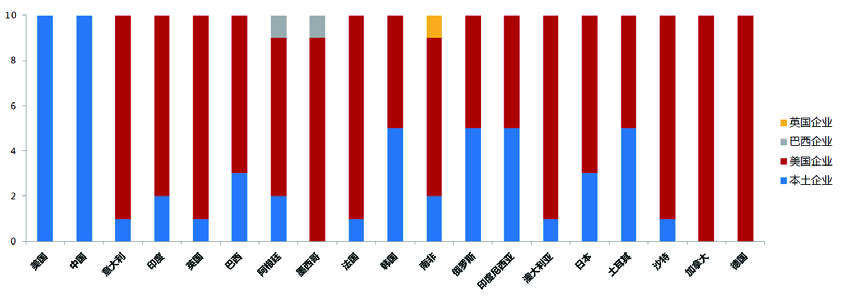
图8:四种类型的企业在G20国家中的比重
2、G20的“BAT”:集中于美国和亚洲
从统计数据看,美国互联网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公司数量明显,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领头羊形成了追赶之势;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分别紧随其后,作为第二阵营;印度和巴西作为第三阵营,具有影响力的上市企业仅各有一家。
表1:主要互联网企业国别量

3、美中互联网巨头企业市值差距正在拉大
全球TOP20互联网市值企业中,美中企业市值总和差距由2014年的2倍上升至2016年的3.4倍,中国与美国互联网巨头企业之间的市场差距明显拉大。这其中除了有中美资本市场的客观环境差异外,更体现出的是中美互联网企业在发展中确立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差异已经十分明显,投资人对企业未来成长的信心已经通过股价获得了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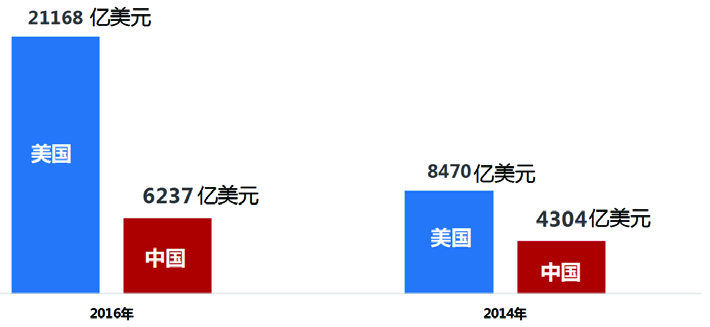
图9:中国和美国企业在2014年和2016年的市值
4、中美互联网应用创新依然是最活跃区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互联网带来了新的增长活力。许多依靠和建立在移动端发展的企业逐渐成为独角兽,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这些企业也被赋予了高估值,尤其是中国移动端市场的优势让企业的服务被看好,现在的估值总和远领先于美国。
根据中国艾瑞公司和美国Pitchbook公司对估值十亿美元以上创新公司TOP10总估值统计,美国公司的总估值超过680亿美元,中国公司的总估值超过1533亿美元,领先美国两倍之多。

图10:新兴国家互联网产业
5、移动互联网正牵引新兴国家互联网创新动能
新兴国家不仅仅是网络大国的目标市场,更会成为全球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的主动脉之一。
1、G20数字战略演进图
G20国家数字战略演进基本遵循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互联网发展与安全战略——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未来工业战略的路线图。

图11: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
2、英国—释放政府大数据红利的标杆
前面已经提到,英国的互联网经济对GDP的贡献率最大,这与英国政府力推的数据开放也有密切联系。在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互联网领域的数字开放与共享正在被发掘出新的经济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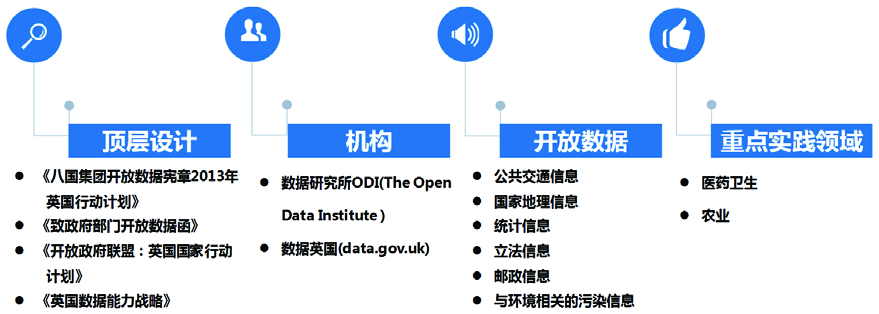
图12:英国互联网释放政府大数据红利
3、韩国—以战略推动信息安全产业全球化构筑护城河
韩国对互联网的信息安全管理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具有鲜明的韩国特色。韩国人口数量不多,但是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领先全球。基于ICT发展的已有优势,韩国欲谋求在全球信息化安全领域新的发展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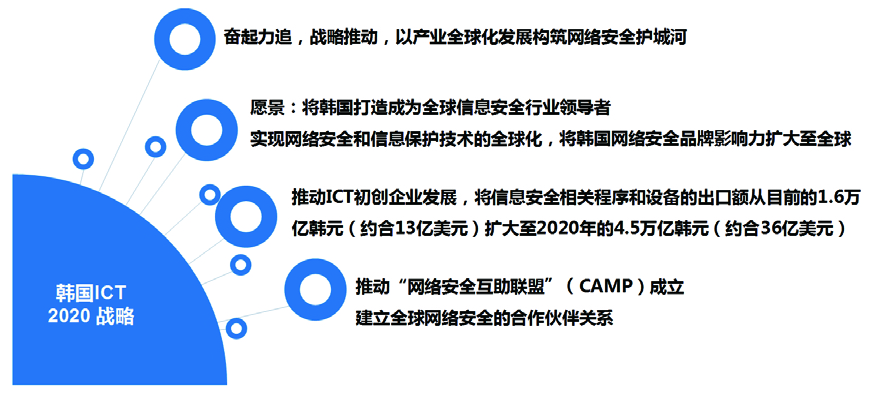
图13:韩国ICT2020战略
1、G20各国网络安全策略部署与配置
纵观G20国家在维护网络安全建设方面的举措,多具有相似性。根据各国的具体措施,我们总结了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表2:网络安全十大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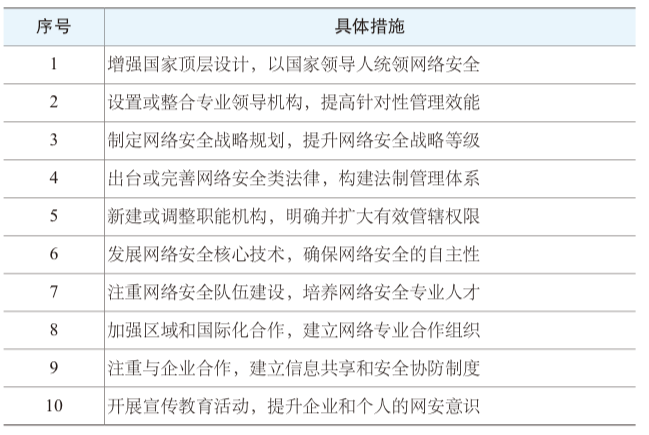
2、G20网络安全企业,美国绝对领头羊
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成就离不开数量众多的安全企业。从安全企业绝对数量上就可以看出美国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国家。更深层次的是美国通过一些机制实现了政府与安全企业的合作,让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地位越来越具有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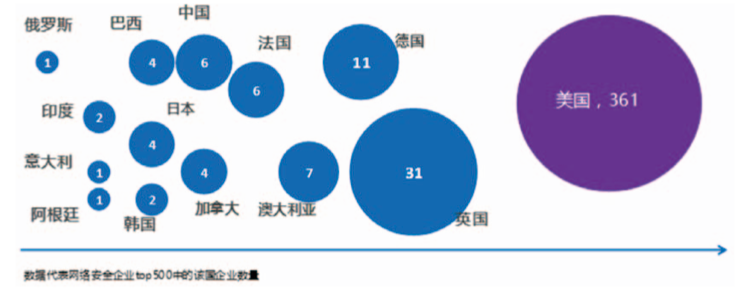
图14:G20网络安全企业数量
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与网络空间的错综复杂结合在一起,引发全球网络空间出现新的安全挑战。从国家发展程度角度划分,可以分为G20国家即全球国家都面对的挑战、G20中发达国家面临的挑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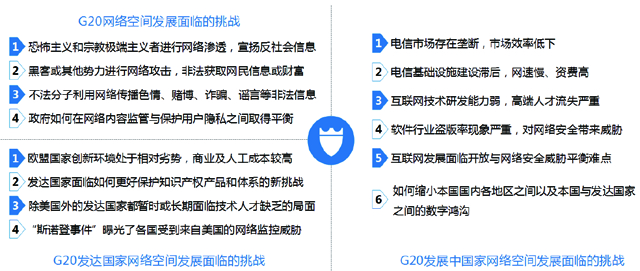
图15:G20国家网络空间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历届G20会议中,多有涉及到互联网方面的议题。说明互联网自身的影响力和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表3:提到互联网发展的G20会议

以上就是对G20互联网发展的简要总结。希望读者能够从中了解互联网发展的态势,并发现一些趋势,欢迎与我们沟通。(责任编辑:钟宇欢)
G20 Intern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Comprehensive paper
Project general manager: FANG Xing-dong,
Project lead unit: Shantou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rnet
Abstract : G20 National Confer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ction which discusses a number of issue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the world's economy. G20 Summit will be held on September 4, 2016 in Hangzhou, China. In recent years, issues about the internet always be mentioned on various types of G20 conferences. Previous G20 conferences also launched a number of documents about the stages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es. This year, China as the host country, hav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of the world, focus on Network Power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r Cyberspace is bound to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of this conference and series of forums. Under such background, G20 National Internet Development research Report, which was led by Shantou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rnet and written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is the comprehensive one. Reader can stud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status quo and the trends of the Internet of G20 nations.
Key words: G20; Internet; Cyberspace
习近平主席在“4•19”讲话中强调“核心技术受制于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早在2013年底,习近平主席就发展算机操作系统等问题作出指示:计算机操作系统等信息化核心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我们在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上受制于人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要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抓紧谋划制定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并明确时间表,大力弘扬“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经过科学评估后选准突破点,在政策、资源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扶持,集中优势力量协同攻关实现突破,从而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为确保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习近平主席的指示是中国发展关键核心技术的指导方针,我们应当认真学习、认真贯彻落实,使中国能早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展成为一个网络强国。
这使我们认识到,发展关键核心技术的基本目标是不能受制于人,它也为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受制于人,规定了一系列的方针策略。有关部门按此制定了相应的规划,作了相应的部署,现在是认真贯彻落实的问题。
不过有些人习惯于过去“招商引资”的思路,他们以“落后挨打”为由,认为自主创新太费时,也不容易产业化,主张通过“引进”或与外国“合作”来解决核心技术问题。这种思路不符合当前世界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在网信领域,与其说“落后挨打”,不如说“受制于人挨打”。大家知道,伊朗的核设施受损,显然不是因为设施不够先进,而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外国设备受到了攻击。我国信息领域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例如目前中国的桌面电脑约97%都用Windows操作系统,这些年来,中国人为此花费的钱以千亿元计。但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多的钱并没有换来或买到什么Windows的核心技术,到头来中国用户还是要被停服、被黑屏、被强制升级……一句话,还是受制于人。反倒是那些中国无法引进或无法与别人合作的技术,如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等,我们通过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终于能自己掌握,不再受制于人了。
当然,我们不拒绝任何新技术,在自主创新的同时要坚持开放创新。一般说来,发展核心技术可以采取四种途径,即:引进但必须安全可控;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同别人合作开发以及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新。究竟采取那种途径取决于实际情况,并应按照是否受制于人的原则进行衡量。
近平主席的指示向我们指明,关键核心技术只能采取自己研发的途径。因为它们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被所拥有的国家奉作“定海神针”,不能随意开放、随意买卖。所以这类技术既不可能同别人合作开发,也很难在满足安全可控的条件下引进。当然,在我们自己研发核心技术时,可以在不受制于人的前提下通过市场获取某些先进知识产权或技术;当涉及软件技术时,也可以基于开源软件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我国《国家安全法》要求“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这条法规所涉及的领域可望成为我国自主核心技术的第一个市场,而《政府采购法》也可以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撑。
我国加入WTO后,目前除了政府采购市场外,一般市场是完全开放的,我国自己研发的核心技术在初期很难进入一般市场,所以只能先在政府采购市场的支持下,使自己发展壮大起来,达到好用的水平,然后再推广到一般市场。由于我国市场广阔,即使是这一部分市场,如果运用得当,也足以支撑起自主核心技术的发展,起到突破点的作用。
至于在我国的一般市场上,企业无论是实施引进还是同别人合作,只要符合法规,都是容许的。这几年我国企业和外国同行之间在一些核心技术方面的合作有增多的迹象。这可能是随着我国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外国放宽了某些出口限制,有利于企业间国际合作的扩展。另外,我国广阔的市场也吸引着外国企业扩展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一般说这种合作是市场行为,企业可以自行决策。只有当合作涉及到国家安全或者有可能造成市场垄断时,需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
据报道,近来有企业同微软合作要推“Win10政府版”。本来企业间的合作如果是面向一般市场那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它要面向政府市场,这自然要受到相应法规的制约。众所周知,政府出于安全的考虑完全可以决定是否采用某个特定产品或服务,这与我国在WTO的地位也没有任何矛盾。早在2006年微软发布“视窗Vista”时,当时有关部门根据专家评估,确认其架构会使用户电脑被微软高度掌控,其结果是“Vista”未列入政府采购目录。后来微软发布了“Win8”,有关部门根据专家评估,确认“Win8”和“Vista”是同类架构,且其不可控程度更高,因此“Win8”也未列入政府采购目录之中。此后,微软以空前的速度将“Win8”升到“Win9”、最后升到了“Win10”,有人评论微软此举有刻意绕过中国政府采购对Win8的禁令之嫌。
2015年,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本着为国家安全负责的态度,委托一些权威测评机构就“Win8”和“Win10”的相似度进行了测评,他们证明,“Win8”与“Win10”内核基本一致,并不存在较大幅度的变化,而版本号的大幅度升级更多是为了商业宣传的需要。据此,建议在政府采购中,对“Win10”和“Win8”予以同等对待。由此可见,现在“Win10”未列入政府采购目录并不是什么新规定,只是过去政府采购对“Vista”禁令的延续而已。
一些评论认为,以“Win10”的规模,中国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在有限时间里掌握它的数千万行源代码,何况根据以微软与中国方面实行“源代码备案”的经验,中国方面并不能看到100%的源代码。而微软Windows和设备集团副总Yusuf Mehdi也表示,“微软将保留所有关于Windows10的技术知识产权”。这些情况都表明谁与微软合作推“Win10”的定制版都不可能使“Win10”发生什么实质改变,如果是面向一般市场,关系倒不大,但如果要面向政府市场,须满足安全可控的要求,那就难如登天了。
今天,我们重温习近平主席的指示,更坚定了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信念,只要我们遵照《指示》的精神,贯彻落实按照《指示》制定的相应规划和部署,那么中国一定能突破包括计算机操作系统在内的关键核心技术,为确保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责任编辑:李晓晖)
作者简介
倪光南: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院士。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 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中科院计算所公司 (联想前身)和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 2011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和中国计算机学会终身成就奖。
当今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义盛行,网络安全问题丛生。何进行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及建公平正义的国际规则,各界一直存在颇多争议,实质上反映了国家、国民和国际三大网络空间行为体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各行为体从自身利益发,从而形成了目前各执一词、难以调和的局面。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建立需要从三大行为体的视角审视全貌。“三视角”理论是从国家、国际、国民“三点”出发,引出三个边界条件,在稳定的三角形共视区内将网络空间分成“三层”——基础层、应用层、核心层。不同层面区别对待,求同存异,从而跳出单点迷思和二元对立,站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维度,以俯瞰的视角,科学把握排他性与让渡性的对立统一。
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挑战,正在上升为主权国家第一层级的安全威胁。世界各国针对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展开热议,网络主权不可回避地成为争议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得到“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的较大认同,但在国际社会,仍对网络主权存在深层分歧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将网络主权与互联网精神对立起来。有观点认为主权的排他性有悖于互联网精神的互联互通,认为强调网络主权会人为制造新的问题,导致互联网碎片化。例如,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FrontierFoundation)发起人巴洛(JohnPerryBarlow)发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认为,网络空间生来自由,民间力量自会明辨是非,形成网络空间新的社会契约,解决冲突和争议,认为中、美、俄、法、德等各国政府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均不拥有网络空间的主权。
二是将网络主权与人权对立起来。有观点认为互联网应该支持言论自由,主权的介入阻碍了信息自由流动,这一舆论矛头集中在中国设立防火墙上。例如,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AmnestyInternational)认为,中国的网络主权主张侵害了言论自由,并以此为由号召苹果、谷歌、脸书、领英等科技公司抵制中国。
三是将网络主权与多利益攸关方对立起来。有观点认为,网络主权引发互联网治理模式之争,政府主导的多边治理可能会挑战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例如,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施特里克林(LawrenceStrickling)表示对中国的立场感到困惑,认为中国一方面表示支持多利益攸关方,另一方面却在乌镇峰会提倡网络主权。
由此可见,网络主权问题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成为诸多问题树的树根,其他问题由此衍生。在这一问题上理清分歧、达成共识,才有国际合作的基础。“大道至简”,再复杂的问题回归到最简单的“道”上,道通则理明。如何才能让传统主权这个概念在网络空间全球化时代以更加科学的内涵和表达获得最大公约数和认同度?借助在“中美”、“中俄”、“中欧”国际二轨对话交流中得到的一些启发,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框架,阐释一种整体的、互动的、分层的网络主权观,以便更客观、更辩证的理清问题、解决矛盾。
深入剖析上述三个主要矛盾,实质上反映的是国家、国民和国际三大网络空间行为体之间的利益诉求。这三大行为体各自从自身视角出发,对另外两大行为体普遍忽视,从而形成了目前各执一词,难以调和的局面。
网络主权和互联网精神这对矛盾,其背后行为体是国家与国际;网络主权和人权这对矛盾,其背后行为体是国家与国民;而网络主权与多利益攸关方这一对矛盾,其背后又涉及国家、国际和国民三个行为体。
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或为僵局,或是一方胜利,但皆付出巨大代价。如今国际社会的舆论质疑,大多出自单一视角、单向思维、单边逻辑。站在一个点看问题,对另外两点普遍忽视,要么绝对,要么过激,结论是无解的,需要跳出单点迷思和二元对立,站在更高的全息维度,引入三个视角。
认清网络空间的三大行为体,如同混沌空间点亮的三盏灯,一盏灯只能看到一个点,两盏灯能看到一个面,而三盏灯可以让我们看清一个整体。从三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网络空间,其中各行为体的角色与诉求,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影响,形成多元矛盾的对立统一。
数学当中解多元方程总要设边界条件,(n>x>0),在一个定义域里求解,变量既不是无穷大,也不是无穷小。三视角的意义就在于,由这三个行为体的视角出发,就能画出三个边界条件,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和共视区,可以进行有效对话,求同存异,更具包容性,避免单点思维。
传统的、实体空间的国家主权,存在天然的排他性。对内强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对外强调不可侵犯的独立性。当人类进入了网络社会,由于开放性、全球性特点,使另外两个行为体的体量增长,作用凸显。这个时候谈国家主权,一定要拓展国际和国民两个视角。
国民视角:国民社群(网民及公民、国民)追求自由,具有更多的横向拓展的特征。当今全球网民达32亿,中国网民高达7.1亿,这是了不起的数字。网民就是公民、国民。国民社群内部具有家族、邻里、语言等方面的相似性,栖身于同一社会与文化语境当中,受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但同时,在网络时代,国民社群更多地走出血缘和物理社区的绑定,实现横向水平拓展,以价值观认同为基础,追求温和渐进的社会变革。各国都市化人群的生活方式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并且因女权、人权、环保、反战、反全球化等共同价值观走到一起。1999年民间团体作为反全球化的力量在反WTO示威中崛起,并在新世纪作一个崭新的利益攸关方成为络空间政策的参与者。
国民社群虽然有追求自的天性,也存在紊乱、松散甚至产生冲突;既拥有美好价值观,也可能诉诸极端主理念和民粹主义。例如:ISIS等伊斯兰极端组织通过网络招募战士,世界各地竟有年轻人趋之若鹜。在无序的环境下,完全靠网民治网,自律效果并不好,自由也无法得到保障。要维护每一个网民的自由,就必须要有秩序来平衡,这就注定网络不能是法外之地。秩序的建立和形成需要外力,需要国家、政府层面制定规则,依法治网,保障网民的合法权益。技术不是万能的,技术本身不会提供秩序和安全,需要主权来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
国家视角:国家追求安全与发展,具有更多的纵向垂直的特征。国家拥有征税的权力,还拥有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按照等级鲜明的命令体系运作,这是17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的特征。讨论网络空间的国家视角,需要将国家分成两类:发达的、强势的上游国家和发展中的、弱势的中下游国家。网络主权对于后一类国家具有特殊意义。
对于发达国家、强势国家来说,它们既可能利用自身所处的上游地位,引领建设和平美好创新的网络空间,也可能诉诸单边主义,肆无忌惮地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监控全世界,至将网络空间军事化、政治化。在这些国家,最坏的趋势是网络空间对外政策上的好战主义。在国家和国民这条双边系上,挪威和平学者加尔通(JohanGaltung)研究的结论西方发达国家越民主越好战。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认为,在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中,最珍贵的是驯服了统治者,将他们关进了笼子里,并号称自己站在笼子里向人们讲话。殊不知,在美国,可能真正做到了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仍然站在笼子以外。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最要紧的事情是建立隔离带,不要将传统空间对外政策方面的好战主义延伸到网络空间。
对于发展中国家、弱势国家来说,国家既可能以主权为国际法中唯一认可的法律武器来抵制霸权主义和好战主义,也可能滥用网络主权概念来隔绝自己国民的信息渠道。这些国家既要保安全又要谋发展,既要管网也要用网,利用网络空间建设符合自身国情的民主体系,避免失去与国民的联系和共鸣。国家与国民这条双边关系应是相互依赖和依存的关系。习近平主席在“4•19”重要讲话中指出:“网络以人民为中心。”要让互联网更好的造福人民。在网上倾听民声,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引导民主,更能体现执政党的智慧。这样互联网的自由活力也会给国家发展带来繁荣生机。
国际视角:国际社会追求开放与包容。国际互联网代表技术创新的主流,人类文明生活的大势。国际社会要追求开放与包容,因为这里既有大国关系的角逐,又有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还需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国际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反经济全球化力量的全球化。按照德赫尔兰(MajidTehranian)的观点,中国、印度以及一些东盟国家属于“北京全球化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中国是最典型的国家。中国经历了长达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和消费,拥有五千万海外华人的联系,因而成为全球化过程的重要受益者。与此相反,伊朗、朝鲜、古巴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分国家,则游离于全球化体系之外。
“达沃斯全球化模式”属于另一种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向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既普及了创新和技术,也造就了消费主义的泛滥。世界经济论坛是该模式的代表,该论坛每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代表几千家全球公司及其政治盟友的利益。与此相反,反对达沃斯模式的劳工、人权以及环保力量也实现了全球化,试图纠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上是国民、国家以及国际三个视角的特征、逻辑、以及优缺点。从国家视角看,国家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正确看待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可以将互联网为我所用,趋利避害。国家主权通过一定的让渡,融入国际体系,可以让国际间的开放互通为国家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促进文化交流、经济合作以及安全上携手应对。国家与国际之间有相互依赖、包容、让渡的关系,达成对立统一。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
国际视角看,互联网在技术上实现了全球互联互通,但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无视国界和国家主权。要防止过度追求开放,越过底线,网络强国更应主动协助填平数字鸿沟,积极让渡和共享网络资源和治理经验,克制使用不对称手段谋取短期利益的冲动。在全球一网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利益契合点,让世界各国都能够取得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安全保障,这才与“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互联网精神本质相契合。最近,中国《反恐法》删除了原本草案中规定的数据本地存储、提供接口等国际社会反映强烈的条款。这说明中国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正在做出必要的让渡。
国家追求安全与发展时,需要向国际开放;国民在追求自由时,需要国家提供秩序保障;国际追求开放时,需要包容不同国家的多元文化。这些多边关系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看似矛盾,却相互依存。每个行为体不能总是一味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绝对化,而是需要一定的相互“让渡”,在三边所限定的共视区内达成最佳的平衡,也就是要在网络空间的地球村、一条船上,寻求守望相助。
综上所述,发展与安全、自由与秩序、开放与包容之间都是一组动与静的统一,阴和阳的平衡。其实这三个行为体本身的诉求并不是绝对冲突和对立,只不过放到不同范畴,而表现出一定对立关系,但最终我们追求的是大格局下的整体平衡,有让有合,对立统一。很多时候,通过观念的转变,视角的转化,就可将一些矛盾化解。
虽然传统主权天然排他,但在全球化时代的网络主权需要考虑合理让渡。具体什么时候排,什么时候让,让到什么份儿上,要有度。基于三视角模型,再进一步分析和把握这个度。
过去习惯把网络主权的争论焦点放在网络空间到底应不应该有主权,也就是放在主权的“演进性”或“延伸性”上,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无须争论的事实。认为网络空间没有边界,认为网络空间不适用国家主权,这种观点已被现实所否定。网络空间早就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疆域,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讲话中早就把它视为一个作战域,并组建了133支网络战部队。
各国不管在网络主权的提法上如何各执己见,在实践层面却无一例外对本国网络加以管治,防止受到外部干涉和侵害。这些都是对承认网络主权的实践明证。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认同网络主权,而在于主权覆盖哪些区域,通俗的说,就是“脖子”以上还是以下的部分。这个问题反映了不同国家对网络安全的痛点是不一样的。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和理解各国的不同关切。
因此,我们认为研究的关键,要用分层的方法来具体分析网络主权的可分性,进而找到主权“排他性”与“让渡性”的适用域。
底层:物理层,包含网络基础设施。这一层的关键是追求标准化,全球一网、互联互通。互联网,是继粮食、水以及电之后,成为各国发展的必备基础设施和先决条件。这一层里,需要各国做出集体让渡,强势方更要向弱势方主动让渡,发达国家把成果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以填平数字鸿沟。在2005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成立了全球数字团结基金,致力于弥补全球数字鸿沟,就属于这个范畴的事情。
中层:应用层,包含了互联网平台在现实中的广泛应用。互联网载体融入了人类在科技、文化、经济、贸易及日常等方面的各种活动。新的世纪,技术的崛起延续了工业时代的势头,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大英百科全书相对于维基百科,新华书店相对于亚马逊,中国移动相对于Skype,中国工商银行相对于余额宝,希尔顿酒店相对于民宿Airbnb,百货大楼相对于阿里巴巴,传统的出租车相对于滴滴优步。后者都具一个相同的特点,建立在网或移动应用平台之上,更容跨越主权国家的范畴。
网络主权在这一层次的响应该因地制宜,动态平衡多边与多方共治,自由与秩平衡。在ICANN所管辖的名体系中,各国都认可“.cn”(中国)、“.de”(德国)、“.ru”(俄罗斯)、“.jp”(日本)等国家代码顶级域的主权属性。同时,顶级域名的注册已经向省份和城市开放,“.Helsinki”(赫尔辛基)、“.London”(伦敦)、“.NYC”(纽约)等城市名称也都成为顶级域名,获得跟“.fi”(芬兰)、“.uk”(英国)、“.us”(美国)等国家级域名同样的待遇。它们都属于各国行政区划内的城市,完整携带主权属性。
同时,关于WHOIS域名注册信息查询,也可以较大程度上包容各国隐私法的差异。WHOIS是“Whois”(谁是)这两个单词的合并形式。“谁是这个域名的负责人?”WHOIS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通过使用WHOIS数据库(https://whois.icann.org/en),任何人都可以查询某个网站的注册信息,涉及包括域名所有人、注册商、注册地、创建和更新日期、联系电话、传真、邮箱等将近60行标准格式的信息。但是具体到各个国家层面,所公布的内容亦可根据本国隐私法的内容决定公开内容的完整程度。所以,从ICANN机制本身来看,虽然奉行的是多方原则,但是从更广的实践层面来看,ICANN却是多边和多方融合绽放的万花筒。
顶层:核心层,包含政权、法律、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涉及执政根基,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容挑战。因各国的国情、宗教、文化背景差异,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的生存常态,不能用一种文化强行格式化这个世界的所有文化,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于一个国家,你可以不认同它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是必须尊重它的存在,包容它的差异,理解它的国情。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土壤即是各国所处的历史、文化、文明语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认为“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希望“在承认文化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发展文化间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认为“尽管受到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积极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挑战,但也为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进行新的对话创造了条件”。
网络空间应该避免重复各国在传统空间所走的弯路,不应以网络安全为借口复制传统空间中格格不入的敌我势力划分,做到各文明、文化、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对文明、文化、以及宗教的基本观点,恰能回应当下全球网络空间领域存在的核心分歧。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的最大障碍。”
可见,在三角形的中层和底层,网络主权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合理让渡,让更多的利益攸关方能够参与治理,形成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而顶层重在体现政府的主导作用,“互联网的公共政策制定权是一国的主权,每个国家对境内信息基础设施承载的信息拥有天然的管辖权”,这是联合国专家组已经达成的共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和网络治理模式,是让各国政府承担国家责任、开展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
综合这三个分层,可以进一步厘清多边与多方的分歧。两种模式其实并不冲突,而是在网络空间的不同区域、不同层级有不同的适用性。涉及意识形态、政策、法律、制度和政权安全问题肯定要充分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体现多边治理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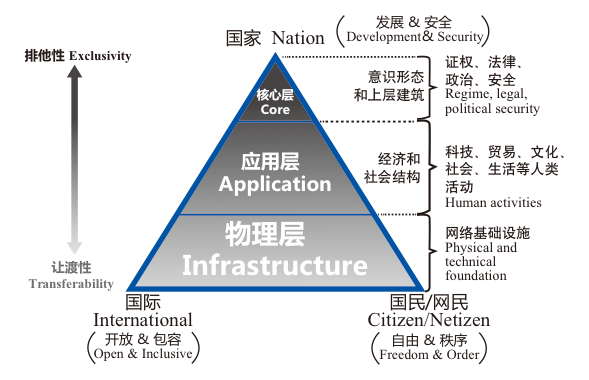
图1:三视角下的网络主权三层特征
基于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回答前文提出的对网络主权的三个质疑:
第一,关于网络主权违背互联网精神的质疑。坚持网络主权绝不排斥互联网精神。“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不容置疑。承认“网络主权”是基础,是为了各国能够平等参与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不仅实现互联互通,而且还要共享共治。
第二,关于网络主权与网络自由的分歧。以防火墙为例,防火墙对中国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面对网络空间日益恶化的安全态势、“颜色革命”的严峻挑战、上游强势资本的冲刷,网络对抗能力还不够强大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对政权和国家的安危无动于衷。就像让一个整日面对恐怖袭击威胁的国家,放下反恐的戒备,解散反恐的武装,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反对网络强国动用国力支持穿越他国防火墙的行为。但是随着安全的好转,互信的加深,民主的成熟和技术的发展,我们也会更加精准、高效地封堵有害信息,将防火墙收窄。顶层所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是面积很小的,过度扩大顶层区域的面积,不利于各方在网络主权上达成共识,这也是中国一直在努力研究、不断改进的内容。
第三,关于多边与多方对立的疑虑。提倡网络主权并非要取代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各国政府也是多利益攸关方的一员,既要发挥政府在多方中的作用,同时也应当尊重、鼓励企业、社群、专家、智库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参与治理。但要防止以多利益攸关方排斥政府的参与和关键问题的主导。在核心层和应用层,涉及意识形态、政策、法律、制度和金融安全问题,必然要充分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体现多边治理的优势。
例如,美国和欧洲今年发布《欧美隐私盾协议》,最终取代了此前由于斯诺登泄密事件而废止的《安全港协议》。新协议较为妥善地协调了国民、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由于欧盟是跨大西洋数据流通中相对弱势的一方,新的框架协议明确规定美国安全部门不可以大规模、毫无鉴别地搜集欧洲用户的信息。欧洲公民在自身隐私受到侵害的时候,既可以向本国政府部门申诉,也可以越过本国政府直接向美国公司申诉。新协议从实质上体现了网络空间的主权含义,也是政府主导下维护网络主权的法律实践,值得研究借鉴。政府在国际和国内重大事件当中是举足轻重的定盘星,这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时刻,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当放则放,当管必管,不容回避,也必须担当。
通过上述分析,三视角下看网络主权的对立统一,可概括为:在全球化向深度发展的网络时代,网络主权具有可分性。第一,核心层具有不可侵犯的排他性;第二,物理层、应用层具有开放共享的让渡性。既不允许滥用互联网的联通性来挑战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也不能以传统主权的排他性动摇全球一网的基础平台。让渡与排他的比重具有弹性,因其网络主权能否得到国际规则的尊重而互动。
第一,网络主权植根于现代国际法,是国家权利和责任的综合体现。任何一个负责任、有良知的国家政府都不会漠视新空间的发展与安全,也不应排斥、阻挠其他国家的主权申张和全球共治的合理诉求。尊重“网络主权”是开展国际作的前提,是构建良好秩序基础。
第二,网络时代和全球背景下的“网络主权观”,要突破实体空间的局限和二对立的误区,站在网络空间运共同体的维度,以俯瞰全的视角,科学把握排他性与让渡性的对立统一。中国坚持网络主权,也在合理让渡主权,中国重视国家安全,也在推进国际合作与开放发展。
第三,中国从不反对多方治理模式,但必须防止以此排斥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的作用和责任。多边与多方是互补而不是互斥。政府和多利益攸关方可以在网络空间的不同层面发挥不同主导作用。
第四,在网络时代,丛林法则应让渡于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画地为牢应让渡于开放共享;唯我独尊应让渡于共生共荣;以价值观划线应让渡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交流互鉴。(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郝叶力: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ISC“观潮”洲际论坛主席。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强弱,“网”强则国强、“网”弱则国弱。
以色列,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种类稀缺、饱受战乱纷争的中东国家。其凭借深谋远虑的发展思路和独具匠心的管理政策,弥补了自然劣势与先天不足,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将自身打造成网络治理领域的强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典范样本。从1995年至今的20年间,以色列网络安全政策大致经历了起步、发展、成形和完善四个阶段,其政策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世界网络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深入研判以色列网络安全政策的发展演变,不仅有利于加深对网络治理规律的把握,还将为我国“网络强国”建设提供认识和实践上的借鉴。
与众多西方国家一样,以色列的信息化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富于忧患意识的以色列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变革的特殊意义。据研究,以色列信息安全政策的起步得益于以下三方面因素:首先,政务、民生、国防等领域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需求不断增长,病毒入侵、黑客攻击等安全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其次,1997年IBM“深蓝”计算机战胜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的事件使得以色列的精英阶层感受到了技术变革的强大力量;第三,国防部门的有识之士敏锐地察觉到IT变革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安全风险和未知挑战,提出应及时将计算机安全纳入政府监管。在起步阶段,以色列网络安全管理举措主要有:
(一)组建国家层面的审查咨询委员会、研究制定安全标准
1995年4月,以色列政府专门研究“敏感领域”的信息安全管理与防护问题。随后,正式成立了名为“计算机系统和信息安全审查顾问委员会”的职能机构,组织以国防部门职业军人为主的专业队伍,为政府研究设计信息安全领域的管理标准,承担IT系统的安全审计,并就计算机敏感领域的安全管理提供对策性建议。审查顾问委员会的建立不仅为“计算机安全”的管理提供专业化的智力支持,而且,为咨询专家在网络安全政策形成和优化过程中的支撑作用奠定了良好治理基础。
(二)在财政部设立“计算机处”、统筹管理IT预算
除制定安全标准以外,以色列政府还积极统筹IT建设。1996年,在财政部会计总署办公室成立了“计算机处”,主要职责是规划政府在IT领域的计划开支和预算重点,直接落实政府在信息化领域的建设,引导社会的信息化发展进程,为早期振兴国内IT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引导电子政务建设、维护信息系统安全
1997年,以色列政府建立了一个名为“Tehila”(互联网时代政府基础设施)的应用项目,旨在为政府各部门提供IT领域的技术支持,并为建立统一的电子政务提供基础设施和安全服务方面的相关保障。“Tehila”项目涉及政府门户网站、电子税务支付、企业资源管理和公民数字身份识别等多个方面,几乎涵盖了电子政务服务的关键基础领域。同时,确保信息系统安全是“Tehila”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项核心职责,随着电子政务的不断扩展和网络连接的延伸扩大,计算机安全的防范任务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充和提升。
(四)推动社会信息化发展、尝试提供共性化服务
电子政务作为一项新兴事物,一直获得以色列政府的大力支持,以政府希望通过电子政务工程为政府管理的信息化转型和计算机安全提供“共性化服务”。在提升政务服务效率、抵御DDoS攻击、防范网络入侵行径等方面,“Tehila”确实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传统管理与电子政务这两个新旧事务在相互融合的初期往往存在矛盾摩擦。当时,大多数政府机构并不完全依赖“Tehila”的专业服务就能实现自身的预定目标;并且,在安全治理问题上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也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联动。以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网络安全问题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它是集合了政治、安全、战略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治理问题,需要统筹规划、全局考虑,才能实现安全到位、治理得当的发展目标。
不难看出,以色列国家网络安全政策的起步阶段,虽然在Web服务、电子政务以及计算机安全保障等领域做到了提前部署,但安全治理的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究其主要原因:第一,在计算机安全问题上,社会普遍存在认知盲点,仅靠国防领域的少数专家和个人来推动,难免力量单薄、效果不佳;第二,在安全治理上,以色列政府更多的是采取“地方试点、局部实验”的方式,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或者是全局上整体铺开,网络安全的治理工作未能形成统一格局,致使安全政策的实施效果收效不大;第三,IT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普及率仍然较低,政府的内部协调工作又并不是很到位,致使众多利益相关方不愿参加政府的行动计划,许多安全政策因而未能有效地开展或落地践行。
2002年以后,以色列的内外安全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在国内安全环境上,以色列民众和关键基础设施日益遭受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袭击,并且出现了利用移动电话、互联网络等IT技术组织、协调恐怖行动的苗头;另一方面,在国际安全环境上,针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初现端倪,特别是2007-2008年所发生的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网络被攻事件给以色列政府敲响了警钟;第三,由军队部门负责信息安全防御任务的治理方式已不再适应当时的发展需求,若将社会和民生领域的网络安全系统全部交由军方机构来监管,势必会产生道德和法律问题,进而冲击以色列现行的民主体制。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以色列政府开始将“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和“网络监管专职机构的设置”列为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网络安全的治理工作也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颁布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安全政策
在以色列政府的授意要求下,以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于2002年12月11日出台了名为《以色列信息化系统保护职责》的“B/84号特别决议”,这是以色列正式公布的首例网络安全政策。该政策与美国2002年所颁布的《关键基础设施信息保护法》(CIIP)几乎处于同一时期,这使得以色列迅速跻身成为全球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先驱国家行列。
在“B/84号特别决议”中,以色列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概念进行清晰地定义,并明确了未来网络安全政策的实施手段和建设目标,同时还表示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工作需由使用者和监管者来共同承担,实施义务上的分摊协作、发挥监管组织上的专项职责。为落实该项决议的制度安排,以色列对《1998年公共机构安全监管法》进行了重新修订,将私营企业所属的关键基础设施也纳入到新法的监管范围内;同时,还明确提出要对关键基础设施内的数据信息进行安全防护,确保数据安全。
(二)设立“国家信息安全局(NISA)”、专司网络安全职责
早期,承担以色列国内网络安全防护职责的机构主要有国防军(IDF)、国家安全部门“辛贝特”(ISA)等单位。在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这一问题上,以政府曾考虑将国防军设为主要监管单位,但考虑到以色列现有的法律,仅授予“辛贝特”和警察部门有管理国内民众安全事务的权力。在涉及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信息安全问题上,“辛贝特”有着成熟的经验和专业的人才队伍。在经过多轮的分析论证后,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将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监管职责赋予“辛贝特”,即在该安全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国家信息安全局(NISA)”,以色列安全机构的防御职责由此获得了扩展延伸。
根据2002年《以色列信息化系统保护职责》的相关授权,NISA的审查人员可依法对被监管单位在网络安全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上的防护措施以及内容信息等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和系统的安全审查,被监管单位须密切配合监管部门的执法行为、及时分享有用的数据信息,否则将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制裁。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问题上,隶属于强力部门的NISA很好地发挥出了监管机构的优势职能,为以色列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指导和支持。
(三)化解金融领域的安全监管矛盾
在网络安全治理问题上,监管机构的履职行为往往不会一帆风顺,它会面临来自不同领域的压力和阻力,NISA的立威履职也莫能外。
2006年,根据“以色列信息化系统保护最高指导委员会”的决议,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TASE)需纳入到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监管范围内。证交所方面对此决定表示严重不满和坚决抗议,其具体反对理由为:第一,证交所及其管理高层在信息安全领域有着多年的经验积累和丰富的能力储备;内部建有完备的信息安全保障部门,能够按照全球最先进的安全理念开展工作,并能遵照以色列信息安全标准的各项要求;在无需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就能独立地承担好自身信息安全的防护职责;第二,若将信息系统置于安全情报部门的监管体系下,势必会极大地损害以色列金融市场的良好声誉和国际地位,投资者们会担心其交易信息被以色列政府监控,进而有可能引发国际资本的大范围逃离,危及以色列国家的经济利益。第三,证交所方面认为,有关将其纳入到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监管保护清单的任何提案决议都将是一项冒险激进、后患无穷的非明智政策,片面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用来提升网络安全的治理水平,只会带来事与愿违的效果。
虽然,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利用政府公关、媒体宣传等多种反馈渠道向政府表达抗议和不满,但经过监管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多轮博弈后,证交所最终还是被以色列政府划入到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监管范畴内,接受相应的安全监管和执法监督。此次冲突事件的顺利化解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政府的网络安全治理措施实施得当,并正确处理好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利益纠葛和合作关系,就不会引发所谓的灾难性后果。
(四)扩充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工作体系
自2008年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被确立为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以来,国家信息安全局(NISA)又先后将商用移动电话、互联网服务运营商等不同领域的8家单位也纳入到国家监管的范围视野当中。尽管政府的监管成本有所增加,但事实上这些增加的预算最终被证实用到了促进政府机构、监管部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所有者和运营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与互信合作关系上。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工作由此构筑起了比较完备的治理体系,并实现了阶段性的政策目标。
在2002-2010这一阶段,以色列政府为适应时代的需求、顺应社会的呼声,对其网络安全政策进行了及时调整。具体特点有:第一,强化了重点领域和重点设施的网络安全保护措施,出台并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政策;第二,在治理工作上,实行义务分摊、强调专职专责,以色列政府合理地设计了军队机构、安全部门和网络企业等在安全治理体系中的职能角色和功能定位,突出了“辛贝特”所属国家信息安全局(NISA)在国内网络安全监管事务中的专项职责,确保了网络安全领域的相关部门都能各显神通、各尽其责;第三,注重技术发展和网络政策的兼顾平衡,以色列在制定这一阶段政策时考虑到了技术变革、安全成本和市场效率等要素的重要性,将敏感数据和隐私信息的监管保护也纳入到治理政策的统筹范围之内,进而拓宽了监管工作的视野,提升了网络治理的水平。
最近五年来,以色列信息化进程和安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一,从网络发展的数据报告来看,2010年以色列已成为全球宽带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犹太居民的家庭宽带普及率已达到68.79%,居全球第六,远高于第20名的英国和第25名的美国;并且,以色列网民每月平均上网的时间达到37.4小时,位居全球第二;随着互联网络在以色列境内的迅速普及,网络安全的威胁挑战与网络事件的频频爆发成为一种常态。第二,从政策的成效性与适用性来看,以色列原有的针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制度安排已无法有效满足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需要,NISA的监管工作也存在诸多执行不到位的地方,网络安全的新形势亟待安全治理的新模式。第三,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变化趋势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治理力度,2009年奥巴马政府更是完成了对美国网络安全状况的整体评估,指出来自网络空间的威胁已成为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和军事安全威胁之一,加强对网络基础设施的保护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根据内外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和美国等战略盟友的政策启发,以色列积极着手制定更加符合国情、更加有力、更为高效的网络安全政策,安全治理的整体水平变得日趋完善、日益成熟。
(一)仿效美国启动网络安全政策评估
2010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参照美国发布《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的方式,要求以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对国家现有网络安全的整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NSC迅速组建了一个由8名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评估小组,这些专家分别来自军事国防、学术科研、国家安全、经济金融和科学技术等相关领域,评估小组由7个小组委员会外加1个机密委员会共同构成。他们用6个月的时间对以色列网络空间的风险挑战和未来机遇进行了系统性的调研评估,启动此次评估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摸清以色列网络政策的实施效果、预判网络安全的风险挑战,进而为下一阶段以色列网络空间优势能力的提升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承前启后的《国家网络计划》报告
2011年,评估小组正式向以色列总理提交了《国家网络计划》评估报告。在调研结论中,评估小组指出,外部敌对势力和黑客分子可通过网络空间对以色列的国内安全进行渗透破坏,专业的网络攻击行为和敏感的网络安全事件会使以色列的网络安全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同时,2002年信息化系统保护政策B/84决议的涵盖范围太小,仅针对特定的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其它与网络安全紧密相关的商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大众却被置于法律监管的保护范围之外,这不仅影响社会民生的健康发展、危及中小企业的成长环境,更不利于维护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和总体安全;并且,评估小组在对以色列网络安全产业以及商业化建设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调研后还发现,以色列现有制度法规上的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技领域优势潜能的充分开发。例如,以色列的贸易政策就限制与密码技术相关的产品出口到海外,而在国内与密码学相关的科研攻关又利润微薄、难以吸引投资,政策的限制阻碍了潜力的发掘。因此,评估小组在最终结论中告诫以色列政府需对原有的网络安全政策进行革新升级,以满足网络空间发展的安全需要。
评估小组从教育、研发、安全和机遇等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充分挖掘商业部门和IT产业在网络创新和科技研发等领域的潜能优势,利用协同优势打造能力优势;第二,积极鼓励高等院校开展网络安全技术攻关,成立科研卓越中心,并为网络空间的发展培养优秀人才;第三,尽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政策法规修订,减少利益团体间的矛盾冲突,利用合力优势打造治理优势;第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投身国际舞台,参与对外交流合作,使以色列成为网络安全世界强国。
《国家网络计划》评估报告是以色列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所做出的一项整体性、宏观性的战略统筹。它不仅考虑了网络安全防护、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细节性问题,同时还从战略角度出发,统筹规划未来网络空间发展的努力目标和方向路径,发挥了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指导作用。
(三)落地践行的“2011国家网络战略”
经过“国家网络计划”的评估诊断后,以色列政府于2011年8月7日正式公布了关于推动国家网络空间能力的“3611决议”,即《2011以色列国家网络战略》。该战略采用了“国家网络计划”中的多项政策建议,提出要强化以色列国内各领域网络安全设施的防护水平,鼓励政府部门、学术界、工商界和企业界等单位协同攻关、通力合作,推动以色列网络空间能力建设,改进国家网络安全治理水平,进而确保以色列全球五大网络强国的优势地位。自“2011国家网络战略”实施以来,以色列的网络空间治理水平很快处于世界的领先行列,其经济、民生、外交等各领域的安全发展也因此广泛受益。
(四)成立总理直属的“国家网络空间局(INCB)”,统一管理网络发展与安全工作
2011年8月,以色列在总理办公室下新设立了一个统筹网络安全治理、负责网络战略实施的综合协调机构“以色列国家网络空间局(INCB)”。该局作为国家战略的执行者和总理身边的参谋顾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中枢神经作用,其具体职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负责网络战略的研究制定与落地践行。国家网络空间局(INCB)的首要职责是为以色列总理和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网络安全发展与治理方面的指导说明和对策建议,进而协助政府完成网络空间的战略研究,并负责后续政策的跟进实施与落地践行。
第二,负责政府部门机构之间的统筹协调与综合指挥。国家网络空间局能够参与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指挥工作,通过调动政府部门、国防部门、学术机构、商业机构以及企业团体等单位的优势力量,进行实现网络治理的优势互补、安全发展的协调联动。
第三,负责网络空间的态势感知与安全演习。作为网络安全治理的监管机构,国家网络空间局需收集整理网络安全的情报信息、分析研判网络态势的总体状况、及时发布网络威胁的预警信息,并为网络突发事件的解决提供应急预案;同时,为确保以色列网络空间的优势能力,国家网络空间局需定期参与组织国内外的网络安全演习训练,进而提升安全治理的整体实力。
第四,负责网络技术的研发管理与资金扶持。国家网络空间局(INCB)每年会花费大约5亿新谢克尔用于网络技术的创新研发和资金扶持,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云计算等前沿科技都是INCB所重点关注的核心技术领域;在INCB成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内,高校与企业中的各类技术研发中心就如雨后春笋般在以色列境内发展壮大,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技术公司也由原来的50多个增长到220多个;根据Gartner的报告显示,2013年以色列用于网络安全创新研发的资金投入就占到了全球总投入的13%,这一惊人数字的背后得益于INCB对以色列网络安全事业的全力支持与巨大贡献。总之,国家网络空间局(INCB)在以色列网络安全治理领域扮演着“参谋长”和“协调官”的角色,其核心作用异常突出。
在经历了起步和发展阶段的经验积累后,以色列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开始变得更加系统和全面,其迈向成熟阶段的三个重要事件表明以色列的安全治理工作已日臻完善。第一,成立专业化的评估小组,开展国家级的安全态势评估,摸清了自身网络安全的“家底情况”,实现了“看病诊脉”的就医效果;第二,成立高级别的治理机构,将网络发展和信息安全统筹管理。INCB的成立宣告了以色列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有了重要的中枢神经,它能在国防、安全、学术、产业等各领域发挥统一协调和政策引导作用,在推动以色列成为全球网络强国的战略进程中,其突出贡献功不可没;第三,“2011国家网络战略”的正式颁布表明以色列在安全治理问题上有了系统完整的成熟经验,在随后的数年中,该战略一直发挥着提纲挈领、强而有力的指挥作用,以色列的安全治理水平因此有了长足的进步,综合国力的发展也获得了稳步地提升。
2015年以后,以色列网络安全的治理工作面临着新的使命任务。首先,网络空间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人类第五大新领域,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出台面向网络空间的国家战略,这一领域中的网络安全问题可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据国际电联的统计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网民数为31.74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46.4%;以色列互联网协会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以色列的网络使用率在全球排名第20位,87%的以色列网民会定期使用互联网。这些数据显示出网络空间正加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网络安全的复杂化致使风险挑战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强化网络安全的态势感知、推动威胁情报的信息共享、深化安全合作的军民融合成为这一时期以色列政府安全治理改革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其次,国家网络空间局
(INCB)需要一个全新的协调部门,以辅助它完成在网络安全领域日益繁重的组织协调和监管治理任务。网络空间的复杂化致使网络防御的任务细化到不同的分支领域,关联性、准确性和时效性的共享信息将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态势感知能力,成立一个专职的部门既是客观发展的需求,也是治理工作的需要。第三,政府在对以色列网络安全现状进行再评估后发现治理工作需进一步完善。过去国家信息安全局(NISA)和国家网络空间局(INCB)在获取信息共享方面的强制性手段已明显不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并且机构的重叠致使职能交叉,政府需要对现行网络安全治理模式进行再评估,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014年任命新的评估小组,来自国家安全委员、“辛贝特”、国家网络空间局、国防军情报公司以及摩萨德等部门的专家学者最后提出了一个评估结论,即为“国家网络空间局(INCB)”成立一个同级机构,主责网络空间安全的管理,包括信息作战、态势感知和信息共享等工作,利用开源信息的共享丰富秘密情报的搜集,逐步形成对抗网络安全威胁的新体制。
(一)成立“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管理局(NCSA)”,与INCB并驾齐驱
根据2014年评估专家组的政策建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心为政府成立一个新的网络空间安全管理部门,进而强化对态势感知、信息共享和民生安全等领域的安全治理工作。2015年2月,“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管理局(NCSA)”正式组建成立,它成为与“国家网络空间局(INCB)”并驾齐驱、分工协作的重要治理机构。在这一新机构中,国家网络事件应急小组(CERT-IL)成为管理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强化信息安全态势感知的核心部门。新组建的NCSA将使以色列国内不同的网络安全组织实现高效联动与协调互动,减轻了部门与利益之间的条块分割,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安全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以色列网络安全领域的态势感知和信息共享工作打开了崭新的格局。
(二)颁布出台“2015以色列网络安全新战略”
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安全威胁,国家网络空间局(INCB)于2015年11月颁布实施新的《以色列网络安全战略》。该战略首先明确了未来网络安全发展三个层级领域的指导原则:一是稳固性,即不断强化政府的网络安全风险管控与综合治理能力,提升核心部门、重要领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水平,确保网络安全保护的坚实可靠、有力抵御网络威胁的恶意攻击;二是灵活性,即重视灾备恢复能力的建设,当网络安全保护不能做到绝对的万无一失时,应确保核心部门、重要领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运行设备在遭受网络攻击后能及时平稳恢复,进而将网络攻击的危害降至最低;三是预警性,即加强以色列在网络安全态势情报感知和威胁信息共享等领域的能力建设,对敏感事件和敏感人物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防备,进而确保安全预警的及时、准确和高效。同时,2015新战略中还进一步提出,要在以色列境内构筑国家网络空间治理的安全“生态圈”,利用“技术创新能力”、“安全产业能力”、“学术科研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所形成的优势合集,全力打造网络安全的防护屏障。战略中明确表示,今后以色列政府每年将投入专项资金对国内的250多家网络安全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在国内的知名高等院校内建立至少5个网络安全科研卓越中心;同时,政府还将积极鼓励年轻一代参与国家的网络安全事业,挖掘青年人的优势潜能,进而为网络安全的治理提供强而有力的智力支持。
(三)致力巩固网络安全世界强国的优势地位
在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上,以色列提出要在2015年乃至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巩固其作为世界网络空间五大强国的优势地位。在顶层设计上,以色列提出将继续推动立法工作的跟进,确保网空治理领域的立法设计与技术发展能实现协调统一;在人才教育培养上,以色列明确提出要全面提升社会民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网络安全教育,坚持“网络安全全民皆兵”的原则,从小学阶段就设立网络安全常识课,让网络安全教育惠及大众;在技术研发创新上,政府将积极鼓励国内的高等院校开展网络安全领域的跨学科建设,鼓励公司企业和社会组织组建技术攻关的协同创新中心;在发展机遇上,以色列坚信用好并把握好网络空间领域的发展良机必将给未来以色列的国家创新能力、科研教育水平、人才素质拓展以及国际政治舞台地位的提升带来潜力无限的优势活力。
(四)积极拓展国际网络空间交流与合作
以色列政府积极顺应网络时代的发展趋势,不断拓展国际舞台上的交流渠道;同时,还积极深化同世界主要区域国家间的互信合作,努力将自身融入到国际舞台,全力让世界感知以色列的网络成就。在国际战略上,以色列积极将“对外交流”打造成自身发展的一张优势名片,每年利用“网络安全技术大会”、“网络安全周”、“网络技术交流会”等交流平台,向世界充分展示以色列在物联网安全、网络金融安全、移动通信安全、新兴社交媒体安全以及网络安全调查等方面的技术成果和优势实力。在国际合作上,以色列坚持用好对外交流这张名片,利用合作渠道的深化拓展来巩固提升自身的网络强国优势地位。
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以色列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完善阶段”,以色列安全治理工作的总体特征归结起来有三点:第一,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在经历了并合分转的探索阶段后,最终被以色列政府纳入到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高度进行全局统筹;第二,以色列的政策实践表明,网络安全的治理并非简单的技术应对,它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国家战略工作,只有将政治、经济、民生、安全等各领域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全局统筹和平衡发展,才能确保网络安全政策的实施取得应有的成效;第三,重视战略的与时俱进、强化经验的国际交流是以色列网络安全治理进程中所反映出的一个突出特征,网络空间瞬息万变、安全挑战复杂多样,只有让政策跟上发展的步伐,让战略适应形势的变化,才能在网络安全的治理工作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本质上来说,网络安全的治理工作不仅是一项艰巨的技术挑战,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政治任务。“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作为身处夹缝中的中东小国,以色列能够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将自身打造成国际网络舞台上的优势强国,靠的就是其在网络安全治理领域的高瞻远瞩和战略优势。以色列在安全治理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经验对我们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一)政府首脑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是网络安全治理体制的关键
“一张好的蓝图,成就一番事业”。纵观以色列网络安全治理体系的发展脉络,我们可清晰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总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在规划网络安全治理蓝图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职能角色,发挥了“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的核心作用。凡涉及国家战略的起草、安全风险的评估以及专业机构的设置等重大治理事项时,以色列总理都会亲力亲为、亲自督办,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很好地服务于总理,充当顶层设计者的角色,进而协调和规划网络安全治理领域重要政策事务的落实与执行。网络治理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性、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复杂工作,需要国家领导人从战略角度进行全局统筹,更需要国安委这样“一子落而满盘活”的顶层设计机构来承担规划者的职能角色,只有这样,安全治理工作才是抓住了“牛鼻子”,网络发展事业才算把好了“总开关”。
(二)“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以色列网络安全政策演进过程中所反映出的突出特征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以色列网络安全政策从起步发展到成熟完善,其各个阶段都高度重视战略的调整与政策的适配。在网络空间领域,没有一成不变的安全政策,“变”是适应网络安全发展的永恒规律。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与时俱进”就是“主动作为”、就是“改革创新”,当网络安全治理工作从“浅水滩”步入到“深水港”的时候,需要拿出真抓实干的拼劲、坚忍不拔的韧劲和开拓创新的闯劲,来干事业、来谋发展、来保安全。只有明确“改革关头勇者胜、危机来时备者安”的勇气目标,才能在网空治理的道路征程中充当“常胜军”和“大赢家”,才能在建设网络强国的奋进目标中蹄疾步稳、后劲十足。
(三)坚持开放合作、统筹协作是以色列网络安全治理的根本方针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开放合作与锐意进取方面,以色列积极将美国作为网络安全治理的“参照标杆”,学习它的政策标准、借鉴它的优势经验、努力开拓合作视野,进而实现了“最佳实践引进来,开放合作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同时,在统筹协调与联动互动方面,以色列网络安全管理机构ISA、NISA、INCB和NCSA等在不同时期所承担的推进、引导、规划和协调职能,反映出以色列真正地在求实、务实与落实上用了“真功夫”、下了“大力气”。重视对外交往的开放合作,注重产学研用的协调联动,突出各司其职、风险共担的治理模式已成为以色列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四)重视技术创新、强化科研攻关是以色列网络安全治理的重要抓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在夹缝中生存的家,以色列没有得天独厚的源优势,没有高枕无忧的发优势,更没有与生俱来的环优势,其唯一拥有的只是生不息的拼搏精神和实实在在创新意志,因此,重视技术新、强调人才培养、注重科攻关是以色列兴国安邦的“立身之本”、强国兴国的“生存之道”。在网络安全治理问题上,只有握住了技术创新和科研攻关的“核心命门”,才能在今后的发展治理中有“强身板”、有“硬底气”,才能卯足实力在国际网空治理的博弈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上述研究是基于实地调研考察和文献研究分析后得出的一些阶段性成果。同时,由于研究水平和材料掌握数量的限制,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业界专家批评指正。(责任编辑:钟宇欢)
作者简介
吴世忠博士,研究员,《中国信息安全》杂志社总编辑。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公开发表文章百余篇,著有《信息系统的互连与互通》、《C3I系统的安全与保密》等专著和《应用密码学》等译著。
随着互联网管理职能移交尘埃落定,这场淹没在大众视野里的互联网大戏有惊无险地暂告一段。此时距阿帕网正式开通已过了半个多世纪,美国一直独家掌控着互联网的命根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肯定是互联网发展史上重大的里程碑事件之一,也是全球网络治理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从全球范围看,这场移交的最大蕴涵在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即多方模式)从此正式成为全球网络治理的主流模式,与我们熟悉的政府主导的传统国际治理模式(即多边模式),至少形成并驾齐驱、分庭抗衡之势。也就是说,新的游戏开始了!
全球网络治理的多方模式重在平等共识,类似我们的围棋,但博弈更加复杂,也更多奥妙。它的崛起,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起码迄今为止尚且行之有效。现实的因素是,这种理念贴近时代趋势,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在实践中,多方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力”的弊端,所以适用性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既不是我们熟悉的一国一票和一人一票,也不是简单资本说话的一元一票;既不是简单的私有化,也不是我们熟悉的公有化和国家化,甚至不是我们熟悉的传统国际化。那么它究竟是美国政府自己绕晕自己的灵丹妙药,还是忽悠了中国、俄罗斯等期望与美国分权的各国政府的迷魂汤?总之,这是新的游戏规则,在简单或主观结论之前,必须深入了解其中的各种奥妙和玄机,才不致于陷入战略被动。
多方模式与多边模式,两者并不是“或”的关系,而是“与”的关系。对美国政府而言,这种“以退为进”的战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际社会对其独霸互联网控制权的诟病,也意在收复斯诺登事件失去的道德高地,但同时并未削弱美国在各个层面对互联网实质性的掌控,美国的先发优势,依然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和控制。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的新起点,必须正视挑战,开拓视野,以高超的智慧参与规则设置和利益博弈,除了我们熟悉和擅长的政府参与形式以外,两手共抓,全面开辟“多方模式”的第二战线,才能逐步获得与我们网络空间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也有自己的“特朗普”们,习惯于封闭式的孤立主义和斗争思维。排除这种高级黑的干扰,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和防范的。当然,亚投行的成功也告诉我们,面对美国利用先发优势的布局和设局,中国也不是只有一味追随的选择。在重大新技术变革和以发展中国家网民为主体的后网络时代,我们完全有能力展开新的议程设置、规则完善和形式补充。但是,无论如何,从此之后,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国内的民间智库、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学术机构以及个人,都将更多地走向前台,积极主动、锐意进取地参与到全球网络治理的大潮之中。